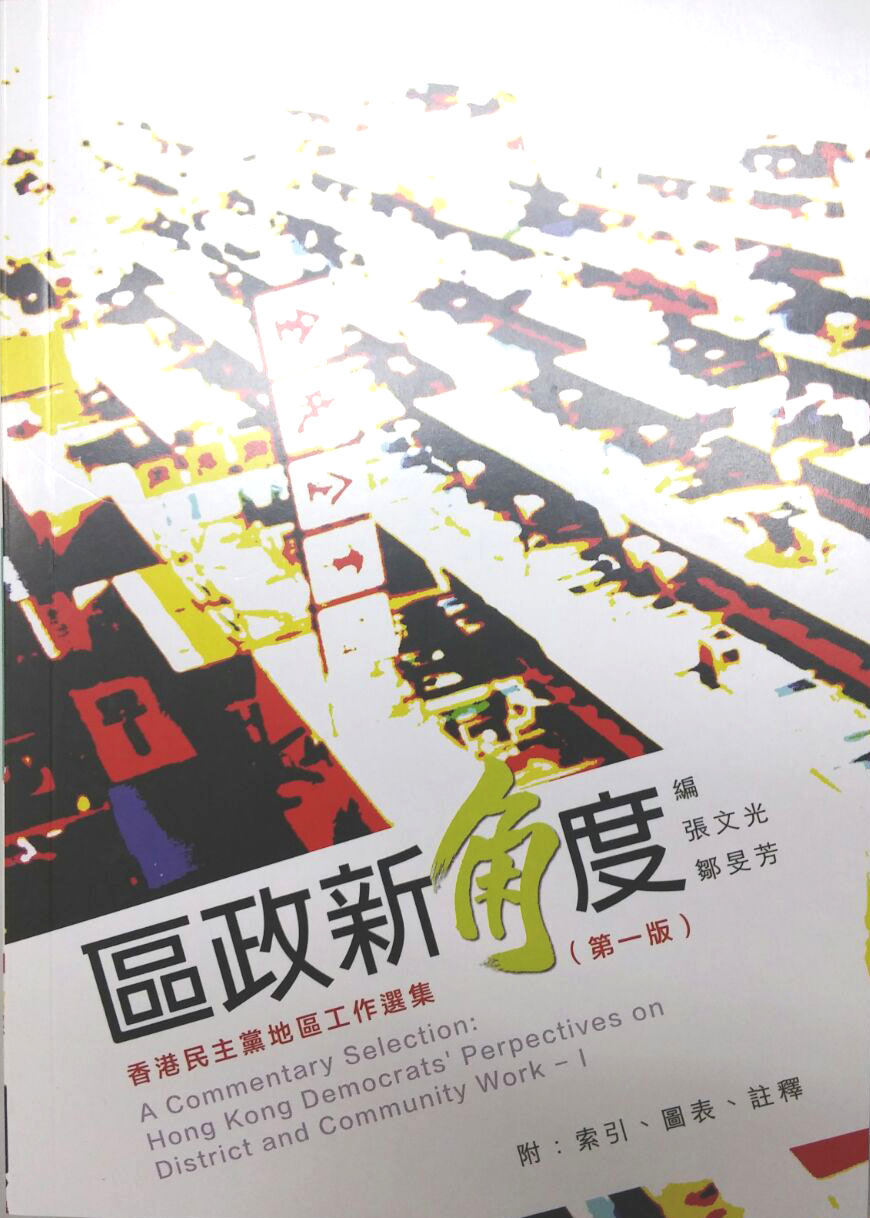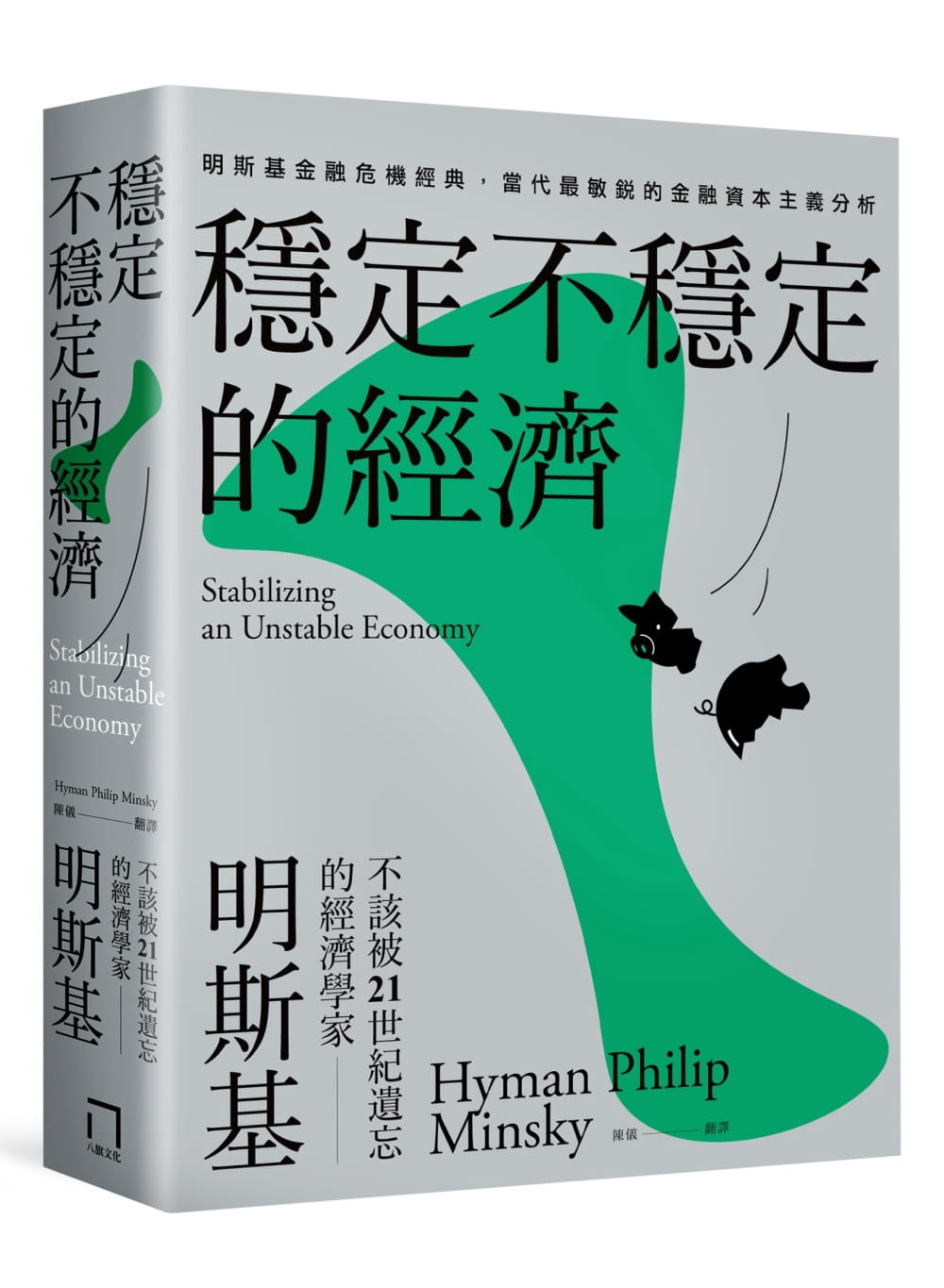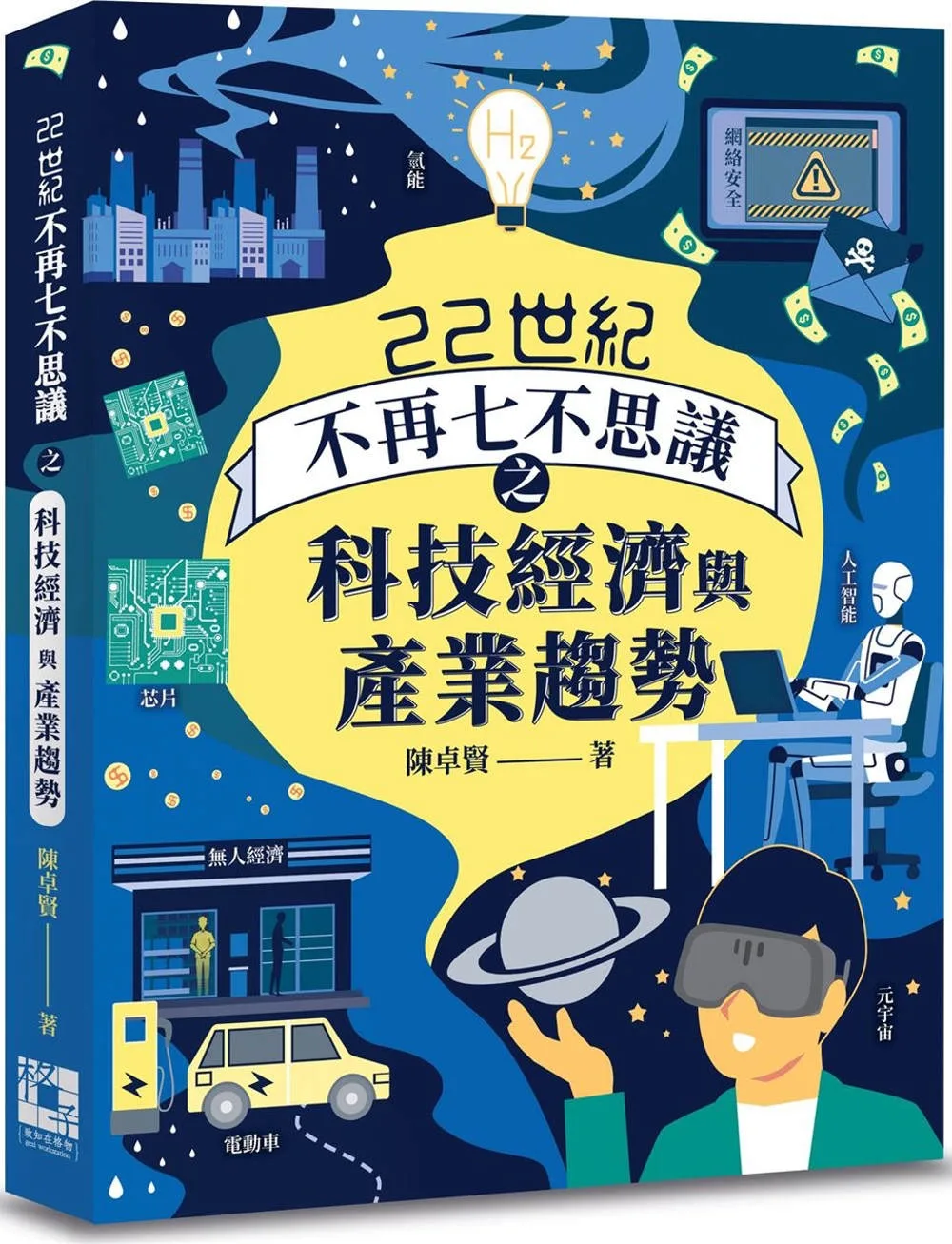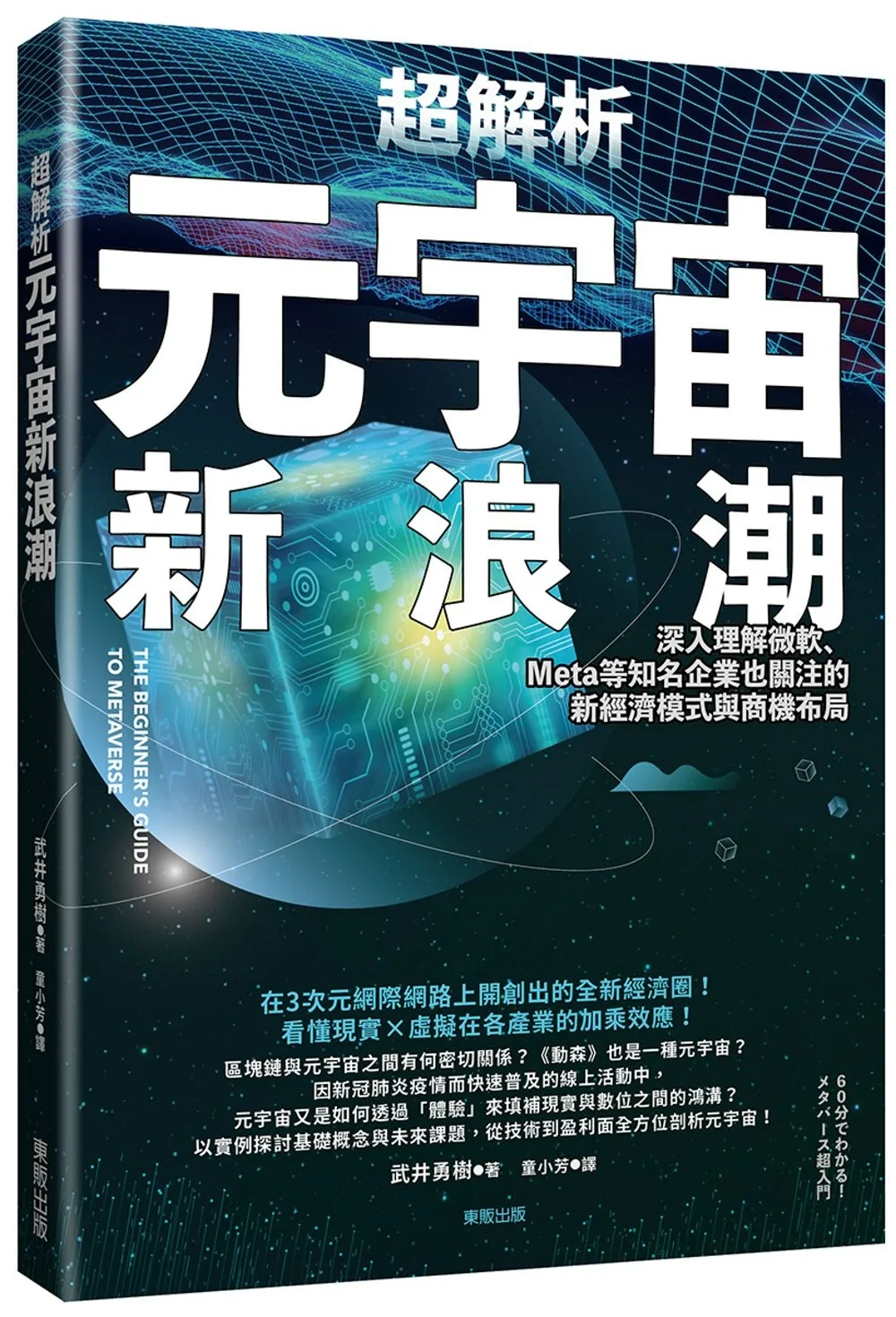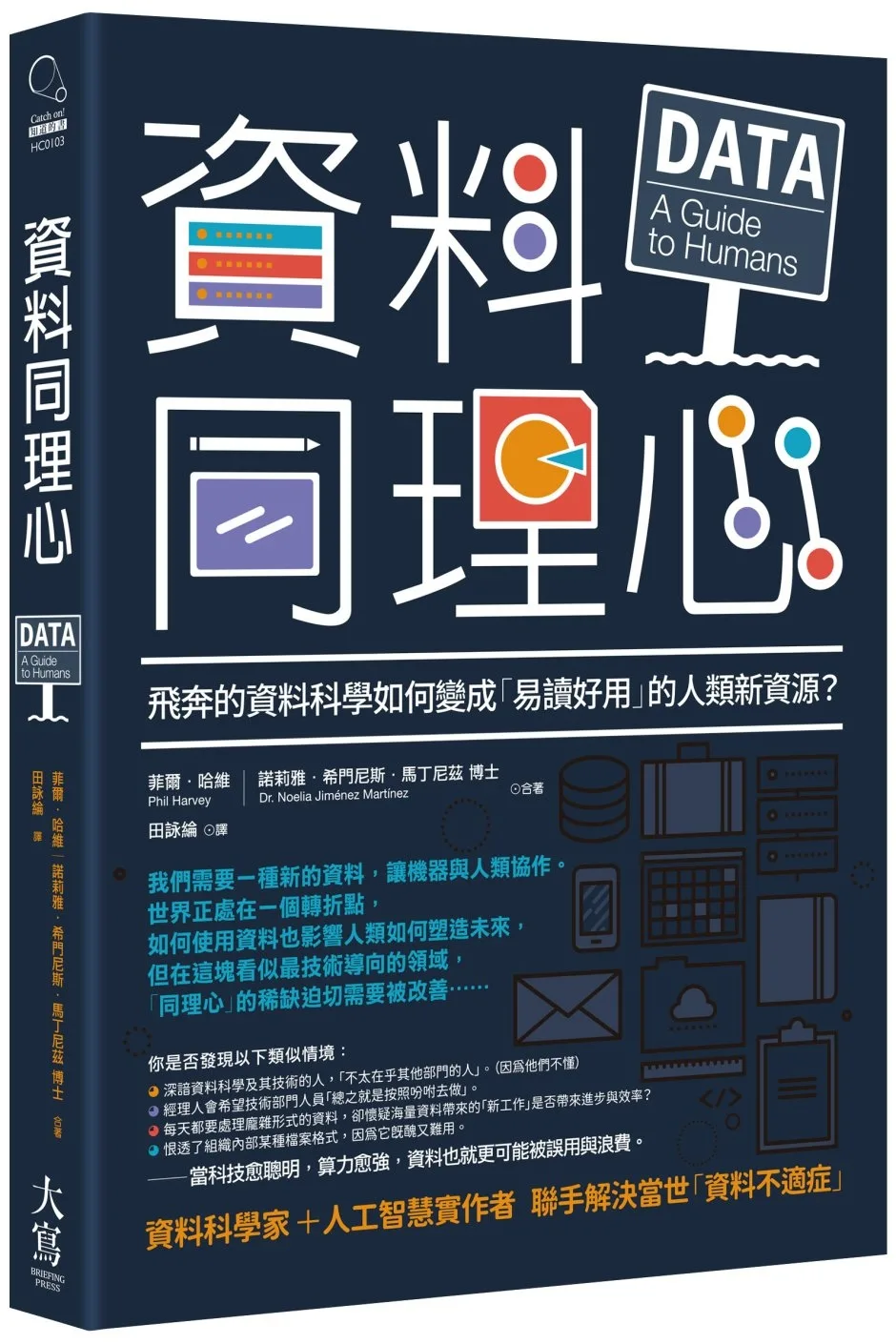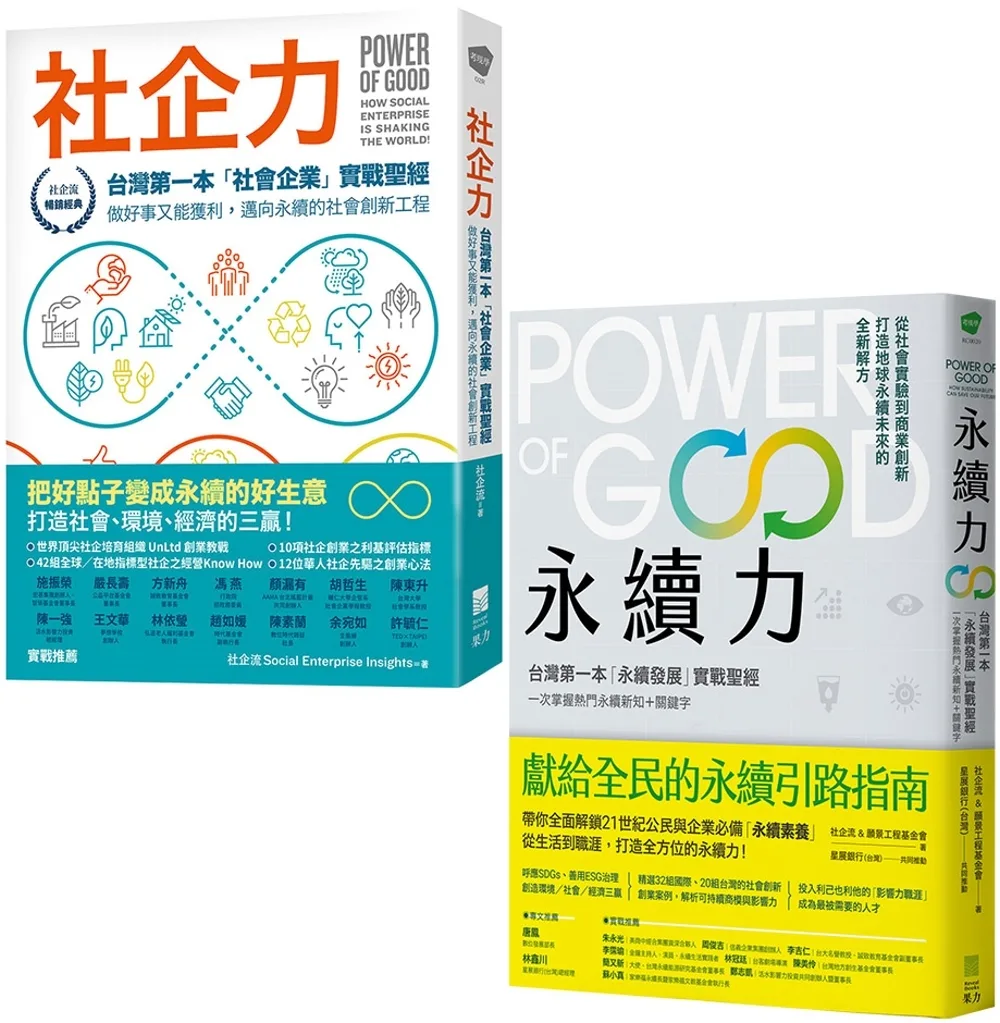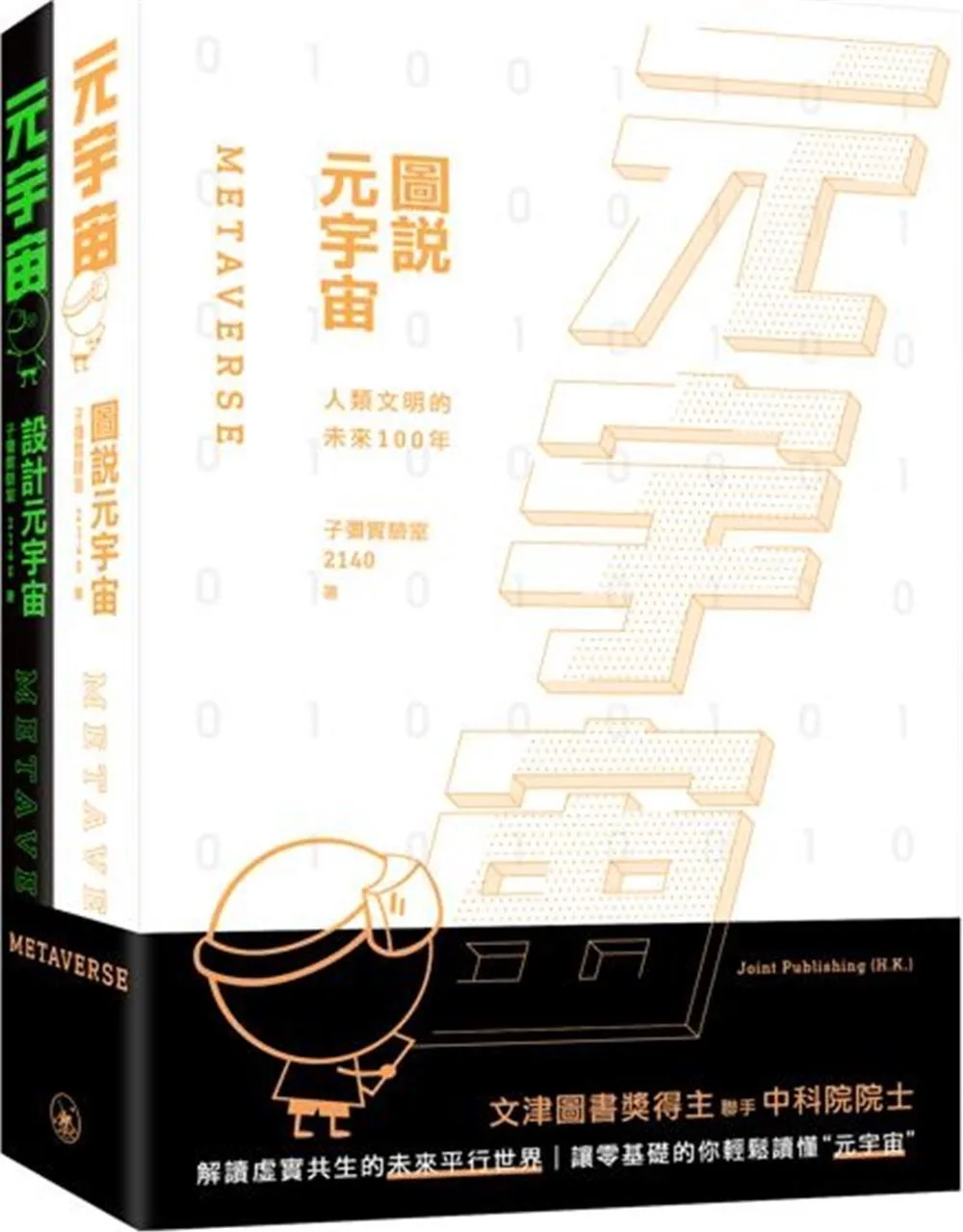推薦序
走在時代尖端的經典
海曼•明斯基的《穩定不穩定的經濟》在1986年首度出版時,絕對稱得上是走在時代尖端的著作。經濟思想家經常如此,像約瑟夫•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目前的影響力就比在世時更大一些,約翰•梅納德•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開創性概念在出版之後才得到廣泛的影響力。個性一向剛毅不屈的明斯基也一樣。在1970年代與1980年代,明斯基固然已堪稱擁有一股不容小覷的影響力,但當年他的概念從沒有像今日一般受到矚目。如果明斯基迄今依然健在,他絕對可以對過去幾十年間密切關注經濟學與金融學的人說一句:「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因此,這時正是重新發行明斯基這本經典名著的最佳時機。
與凱因斯(明斯基在1975年初版一本凱因斯傳記)和熊彼得一樣,明斯基也特別重視商業週期(business cycle)。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蔚為主流的凱因斯主義主要只聚焦在凱因斯著作中較受政治圈青睞的幾個特點,鮮少人記得凱因斯建議在採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前,宜先採取相關的貨幣政策措施,也鮮少人記得他建議應在經濟成長時期設法維持預算盈餘(biudget surplus);太多政策制訂者認為,凱因斯主義意味著赤字開支(deficit spending)是一種既輕鬆、又可自動矯正經濟問題的手段。愈來愈多人以為凱因斯主義已經征服商業週期,由「軟著陸」(soft landing)與「中期修正」(mid-course correction)之類的專有名詞便可見一斑。
但海曼•明斯基與凱因斯有種截然不同而重要的聯繫。明斯基特別著重在投資活動的反覆無常,他指出,來自投資活動的現金流量隱含根本的不確定性,這會對企業的資產負債表產生強大的後座力。這個真知灼見值得我們更加重視。
1970年代末期與1980年代,凱因斯主義因貨幣主義(monetarism)的興起而逐漸式微,明斯基的真知灼見當然不可能獲得應有的重視。但即使是貨幣主義在1980年代初期達到鼎盛之際,也無法有效應對金融體系不斷改變的結構;相較之下,明斯基以其廣博的分析方法和流暢的辯才做出解釋。但在此同時,眾多經濟學家與財務分析師則幾乎全部成為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s)的虔誠信徒。不過,海曼•明斯基的分析並未受那些統計模型所局限。他睿智的察覺到,數學方程式無法對重大的關鍵結構性變遷或經濟與金融行為模式的變化做出適當的解釋。
我投入金融市場之後不久,便深受海曼•明斯基的研究吸引。在從事研究工作時,也愈來愈重視債務的成長速度為何會持續高於名目國民所得(gross national product)。我將這個不健康的發展現象歸因於金融資產快速證券化、金融市場的全球化,以及因資訊科技的長足進展而得以量化風險承擔程度等眾多實務。由於官方政策制訂者未能設置適當的防範措施,導致金融機構不再那麼重視信託責任(fiduciary responsibilities)與企業家創業動力(entrepreneurial drive)之間的平衡,這促使隱含在債務激增現象裡的固有風險進一步升高。
海曼•明斯基的真知灼見幫助我們理解近幾十年重要的金融發展。世界上沒有幾個人比明斯基更了解投機型企業融資(speculative corporate finance)、債務品質日益降低,以及經濟波動性等自我強化的動態,這樣的動態已成為當代的特徵。他將以償債為目的的企業貸款行為稱為「投機性融資」(speculative finance),這種融資將進而驅使投資活動增加與資產價格上升。他解釋,當就業、投資活動和獲利趨勢看漲,企業領袖與銀行業者的內心往往會更堅定相信,最終將導致波動性與令人難以接受的風險增加的這種不當方法是健康的。明斯基以生動的用語告誡世人不該從事「資產負債表冒險」(balance-sheet adventuring,這個精闢的用語堪稱恩隆時代﹝Age of Enron﹞的標誌)。
明斯基身為本書的作者,想必不會訝異在本書初版發行之後發生的種種事件,像是1980年代末期至1990年代初期的儲貸機構危機與銀行危機、墨西哥與韓國債務困境、俄羅斯債務違約,以及1990年代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的超額槓桿行為在各地市場造成的巨大損失,乃至西元2000年的高科技泡沫破滅等。
此時此刻(2008年),我們正遭逢次級房貸危機(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的考驗。有些人將諸如此類的情境稱為「明斯基時刻」(Minsky moment),但這樣的評論實在太小看明斯基研究成果的廣度及深度了。值此關鍵時刻,我們必須痛定思痛,開始嚴肅看待海曼•明斯基的真知灼見,並以他的開創性研究成果作為起點,設法鞏固美國金融體系的根基。
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
華爾街資深分析師、被譽為「末日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