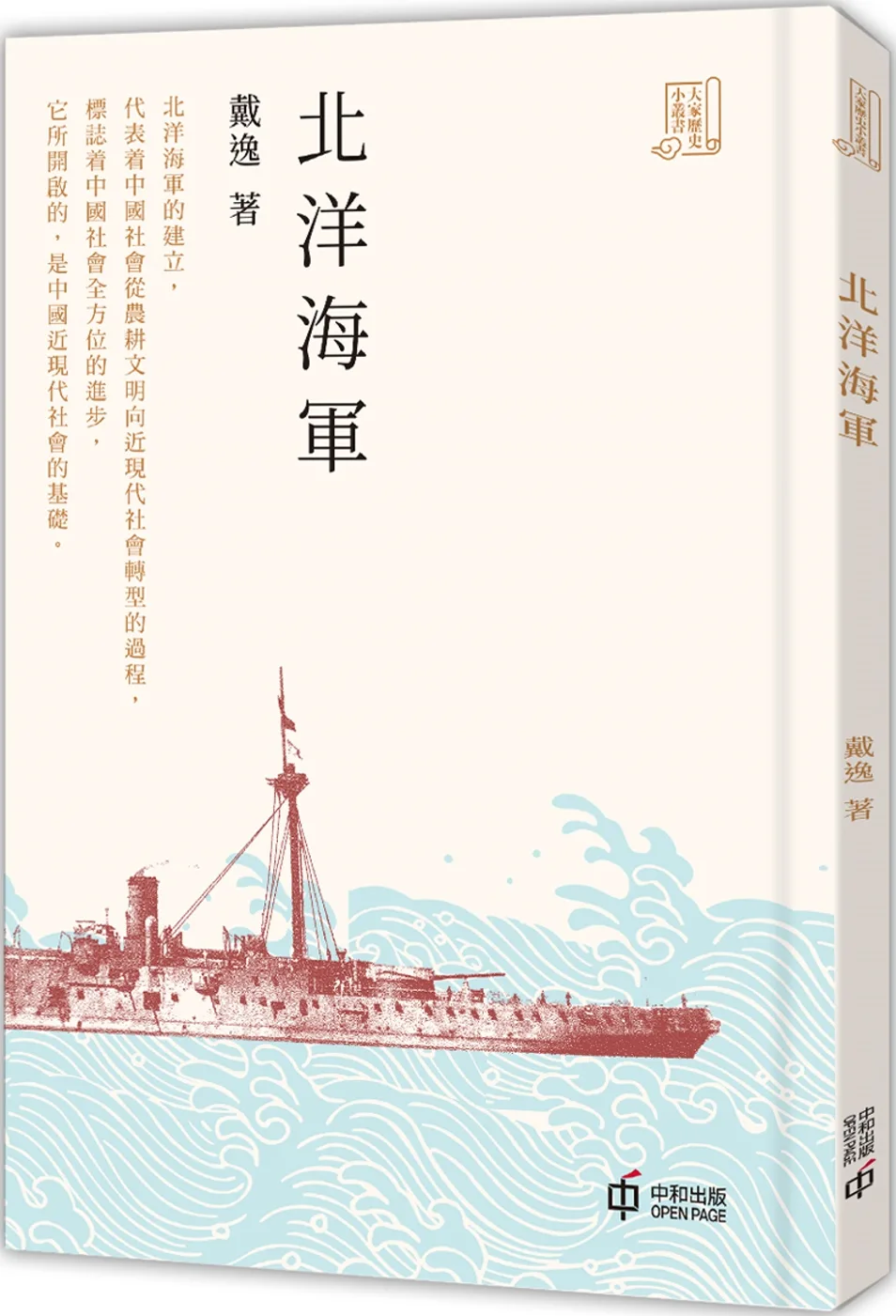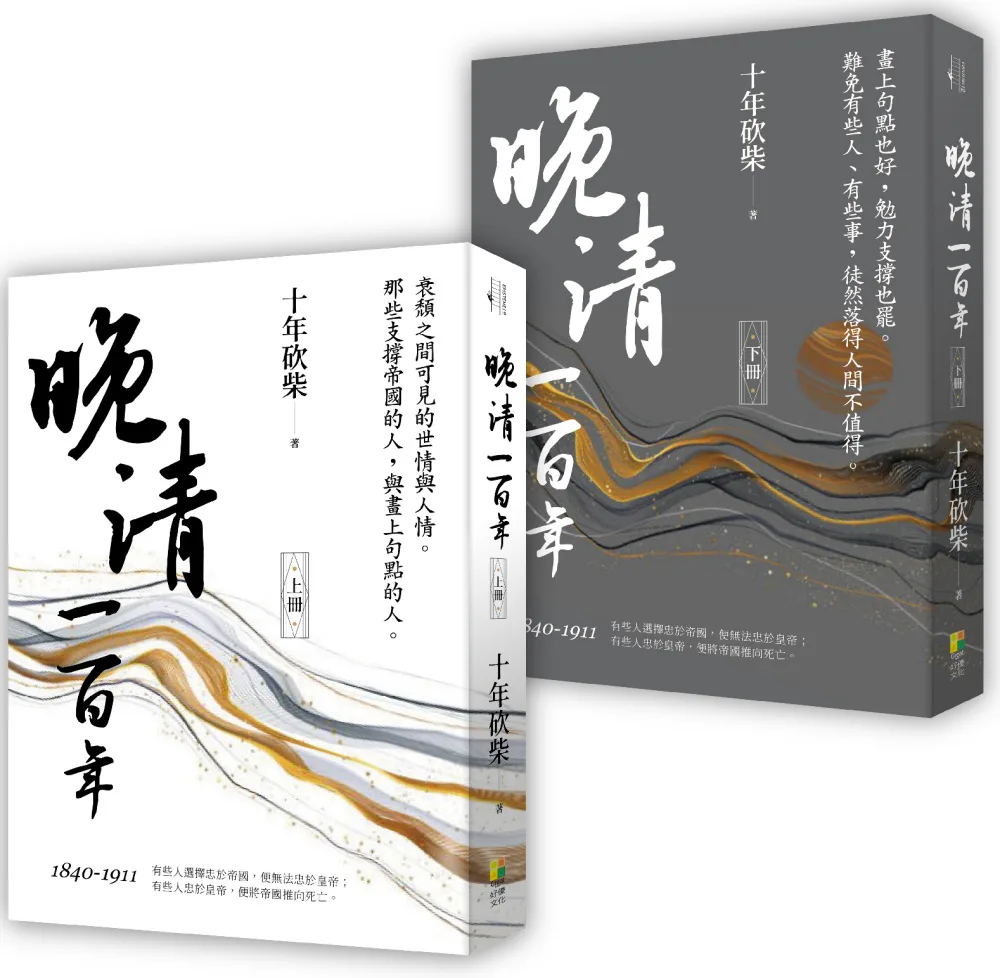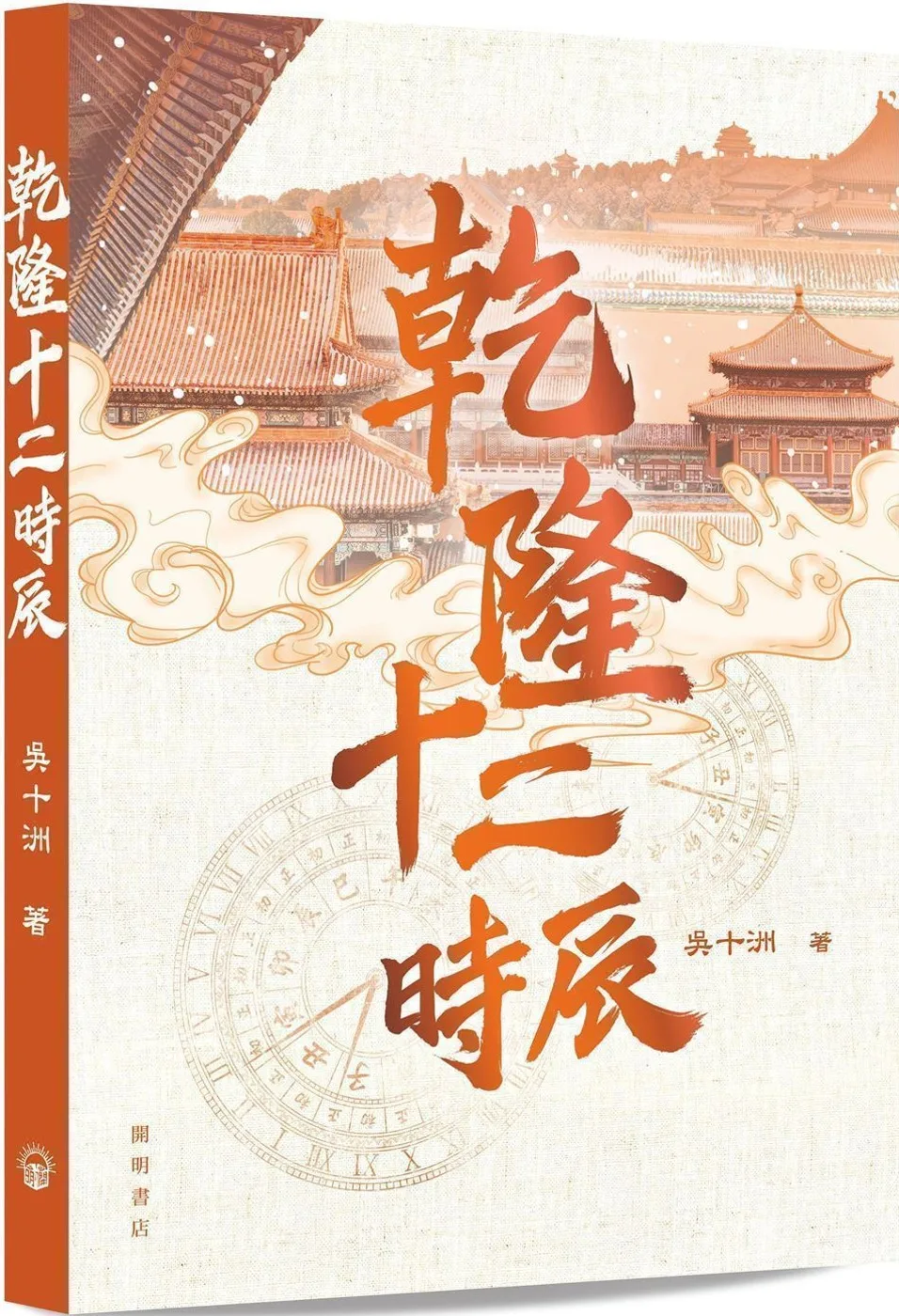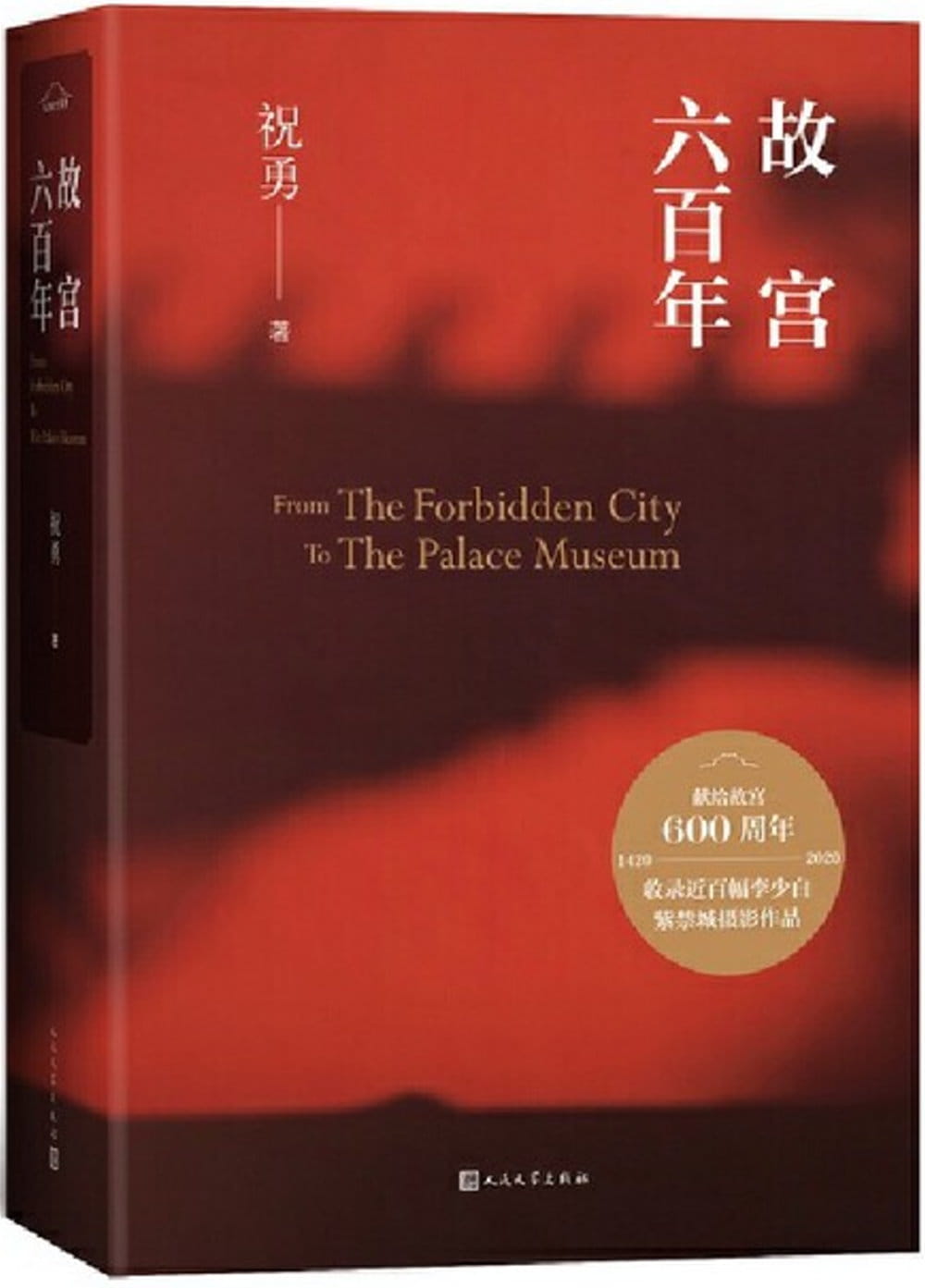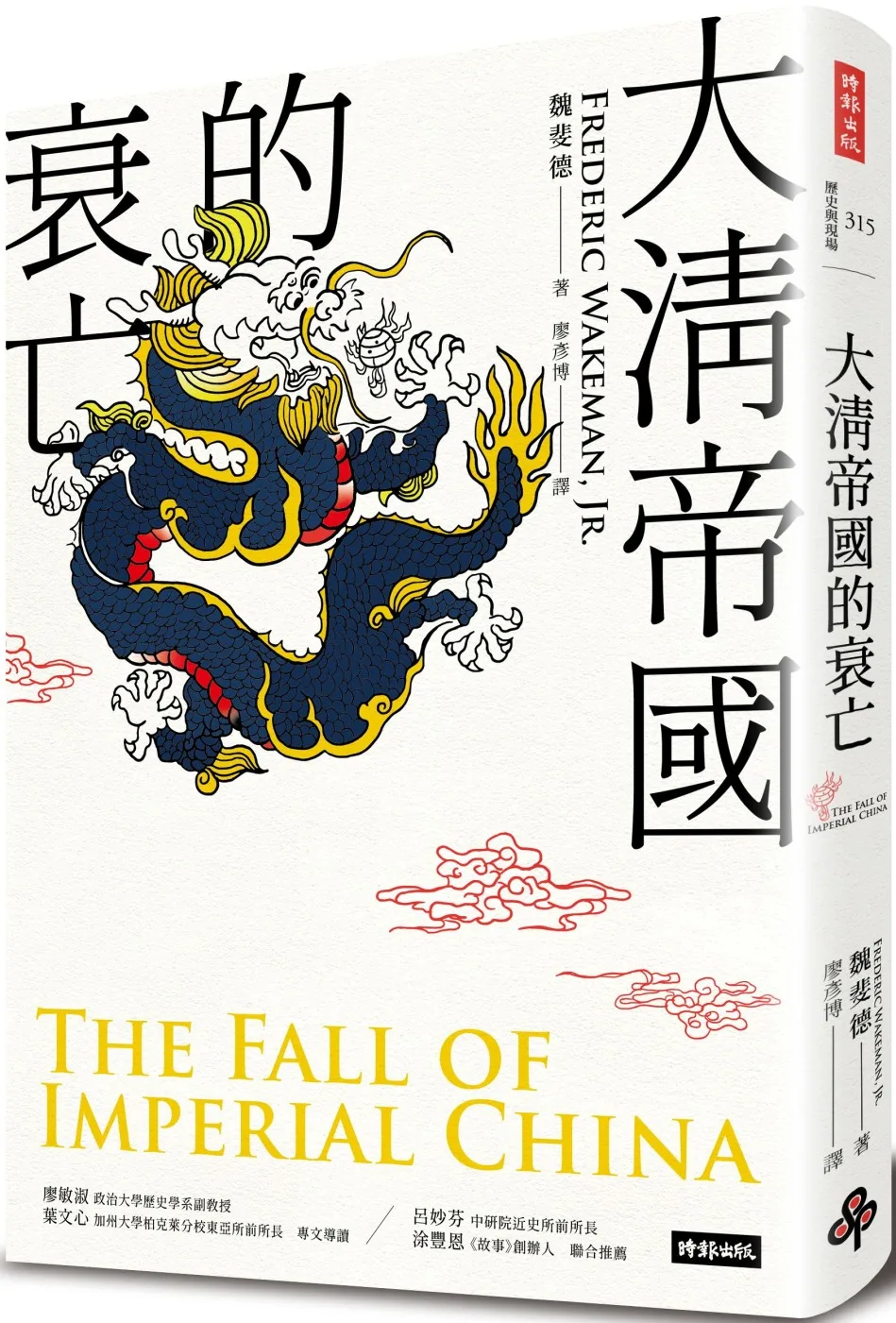自序
中年讀史,如飲濃茶
十年砍柴
這是一本我無意中寫出來的書。
在過去的十年裡,父親和母親先後患重病,數次住院治療,且在不到三年之內,相繼謝世。父母在世,我從未意識到自己已不再年輕,因為心中尚有一份童真氣;父母俱亡,我一下子就覺得自己不再是以前的我了,歲月如流、馬齒徒長的中年心態日益濃烈。
因為父親和母親多年患病並接踵而逝,所以我在過去的十年內必須一次次返鄉。得益於中國交通條件極大改善──特別是北京到湖南的高鐵開通,我的返鄉較之以前變得更便捷。從二○一○年春天父親患病住院,到二○一五年四月父親去世,再到二○一八年一月母親去世,這些年中我每年要回湖南六七次。從十八歲負笈北上,離鄉三十年間,近些年和故鄉的關係最為緊密,因此我便有意識地留意鄉邦文獻,關注湖湘近世人物,撰寫一些解讀湖湘人物和湖湘文化的文章。
在寫這類文字時,我認識到,近世湖湘人才輩出、蔚為大觀,必須放在整個中國社會數千年之大變局的歷史背景下來考察。也就是說,僅囿於湖南一隅,是看不清廬山真面目的,只能感歎其事功之大、際遇之好或性格之堅韌、才華之突出。此類觀感,直如鄉下小孩看戲,喜歡其情節曲折、場面熱鬧和人物個性鮮明。
湖南從一處三面環山、北當大湖的閉塞、落後之地理單元,近世成為對整個中國乃至世界發生深刻影響的省份,舉世矚目的政治、軍事、文化人物如井噴泉湧,於大寂靜中應時而出。這當然有其時代之因緣,如俗話所言「時勢造英雄」,他們搭上了歷史的便車。人們所共知的這趟歷史的便車是太平天國起事。洪、楊大軍離開廣西,向北逐鹿,湖南首當其衝。太平軍入湘,給湖南士人帶來了巨大的危機和機遇。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太平軍和清廷的長沙攻防戰,就如敲響了大戲開場的鑼鼓,一個個湘籍人物聞聲而魚貫上臺。
但是,在同樣的歷史機遇面前,為什麼有人脫穎而出,有人寂寂無名,有人半道折翼,除了才華、能力的差別以及說不清、道不明的運氣因素外,我以為一個人能否將自己的人際關係轉化為助力至關重要。
一個人不可能憑空長大,也不可能平白無故成功,他是在自己所處的人際網路中一點點前行,尋求突破。「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的這個著名論斷,用在中國社會尤為精准。中國古代是以血緣、宗族為核心的家國同構社會,單個的人結成一個群體做事,很自然地以血緣、姻親和地域為紐帶。所以,我們能看到,在歷史巨變中,左右歷史進程的人物總是以某地為基礎成集群地出現,如漢代的豐沛舊友,隋唐的關隴集團,明初的淮左老兄弟。
讀史或者看以歷史故事為底色的小說或戲曲,重要人物的結識和訂交總會被濃墨重彩地書寫,如《三國演義》中的「桃園三結義」和「隆中對」,《水滸傳》中的李逵初見宋江。這其實就是一個人在人生重要關頭,其人際資源獲得了提升和重組。
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在閱讀晚清湖湘人物的史料時,喜歡以人際關係為切入點去觀察、分析,進而從湖湘旁及其他地區的人物,挖掘和梳理他們的一輩子從家族到江湖,從本土到外地,對其影響最大的社會關係是什麼。譬如曾國藩,影響其一生重要的人際關係,首先是他通過科考成為進士,並選為翰林庶起士,進入清帝國最精英的社交圈子裡——他的座師是道光朝政壇第一大佬穆彰阿,他在詩酒征逐中結識的都是大清官場的重量級人物或「潛力股」;而在與太平軍交戰處於焦灼期時他苦苦支撐中,其九弟曾國荃出山募兵,急兄弟之難,曾國荃的「吉字營」成為他後來最為倚仗的嫡系力量。
再如李鴻章,他能考中進士、入翰林院是他人生極為重要的起點;而因為他父親與曾國藩是會試同年,他得以拜曾國藩為師,為後來的功業埋下重要的伏筆;當他遭遇人生低谷、彷徨苦悶時,已經為曾國藩的湘軍辦理幾年後勤的大哥李瀚章及時點撥,為其指明道路。
人總是活在人情世故之中,無論是帝王將相,還是升鬥小民。只要是有血有肉的人,對別人總會有分別心,會分親疏遠近,會有好惡之感,因此我頗能理解太后和皇帝為什麼習慣用佞臣,大官喜歡用同鄉和門生,這是普遍的人性使然。
傑出的人物或者位高權重者,他們不僅僅活在世情之中,其行為對國家、對社會、對時代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不管是正向的還是反向的。他們的言行,與家國之禍福大有關係,他們中間的許多人,身上有著濃厚的家國情懷。譚嗣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胡林翼、彭玉麟、劉坤一、劉錦棠、劉銘傳這類人物自不必說,即使在高層政治角逐中因為私情而做出了頗受非議舉動的大僚,如身為帝師的翁同龢,其基本底色是大清的忠臣,主觀上希望國家強盛,擺脫內憂外患。包括一些觸發「庚子之禍」的守舊派大臣,
如徐桐、剛毅、趙舒翹、毓賢等人,他們的下場很慘,他們的認知和行為現在看來很可笑、可恨,而在當時他們何嘗不自認是為了江山社稷那樣做,內心充滿著道義優越感。他們處在高位,昧於大勢、顢頇糊塗的「家國情懷」反而害了家與國。
以「家國」和「世情」兩個維度去品評晚清大變局中的人與事,我斷斷續續寫了一些讀後感,發在微信個人公眾號(「文史砍柴」)上與朋友分享。
我不是在寫歷史類專業文章,所以不關心自己那些想法有無學術價值;也不想迎合眼下自媒體讀史「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風潮,以此來吸引粉絲。我的這些寫作,確切地說是一個中年文史愛好者的內心自我觀照。人年少時多喜歡讀詩歌和小說,因為詩是情感最直觀的表達方式,小說的情節曲折生動,而讀史是需要有一定人生閱歷的。同樣的一位歷史人物和一個歷史事件,少年時和中年時去看,感受是很不一樣的。年少時愛恨分明,喜歡對歷史人物進行簡單的褒貶。到中年後,有著較為豐富的人生經歷,見過許多事,結識過形形色色的人,對歷史人物和事件方才有一份從容與冷靜的態度,才能理解一個歷史人物所處時代的種種複雜性,如品一杯茶,幾道沖泡,其濃淡與悠遠,需要細細品味。
如品茶一樣去讀歷史,我自己似乎回到了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我常反躬自問,如果我是他,我會怎麼做?我和某公,若在一百多年前相遇,我們怎麼交談?有可能結交為朋友嗎?對某一件事,若換作我,能處理得更好嗎?
左宗棠所言「讀破千卷,神交古人」的人生狀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對於那些歷史人物,若放到當下,我當然會有情感層面的直接判斷,可敬、可愛、可怕或可憐。我喜歡可敬又可愛的人物,這樣的人能在家國與世情兩端達到平衡。若無對世情的體察和尊重,一味強調家國情懷、社會責任那樣的大詞,則面目可憎,不近人情;若一味地屈從世情,圓融處事,將家國情懷與社會責任當作不合時宜的累贅,則不可能從流俗中卓然崛起,即使其社會地位再高,其人格也是猥瑣的,不值得尊重。
這些文章在我的公眾號上引起不少朋友的肯定與讚揚,他們鼓勵我繼續寫下去,也在留言中常不留情面地指出文中的錯訛處,或就一些觀點與我辯論。感謝這些絕大多數未曾謀面的朋友,在與他們的互動中,我獲益良多,也有了繼續閱讀和寫作的動力。因文章是在不同的時間有感而作,其篇幅長短不一,我也沒想過要結集出版。謝惠是一位勤奮而專業的編輯和出版人,她和我曾同事幾年。她讀了這些文章後,建議整理出版,讓更多的人看到。承蒙其不棄,我想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也許我的孔見能博得讀者茶餘飯後一哂,便答應下來。這本書的選題、編排、整理,謝惠費心力頗多。同時,特別感謝雷頤先生撥冗為本書作序。雷先生是湖湘籍前輩學人,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之成就,海內公認。我定居北京後,有幸識荊,時常向雷先生請教,他有問必答,言無不盡。雷先生在大序中誇我解
讀歷史有「貫通感」,實在是過獎了,我就當作前輩學人對後輩的勉勵吧,且愧且受之。
今年是農曆庚子歲,新春伊始,新冠病毒大疫荼毒全球,我禁足於北京一個社區內整理書稿,看窗外的樹木由枯枝變枝葉嫩綠,進而深綠,院內的各種花兒也循時序吐蕾、綻放,再凋謝。心有所感,口占一絕,權當描寫中年讀史的心境吧:
早歲讀詩如飲酒,中年閱史似喫茶。
倚窗忽見三春盡,空負滿庭桃李花。
十年砍柴
二○二○年四月庚子季春於北京定福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