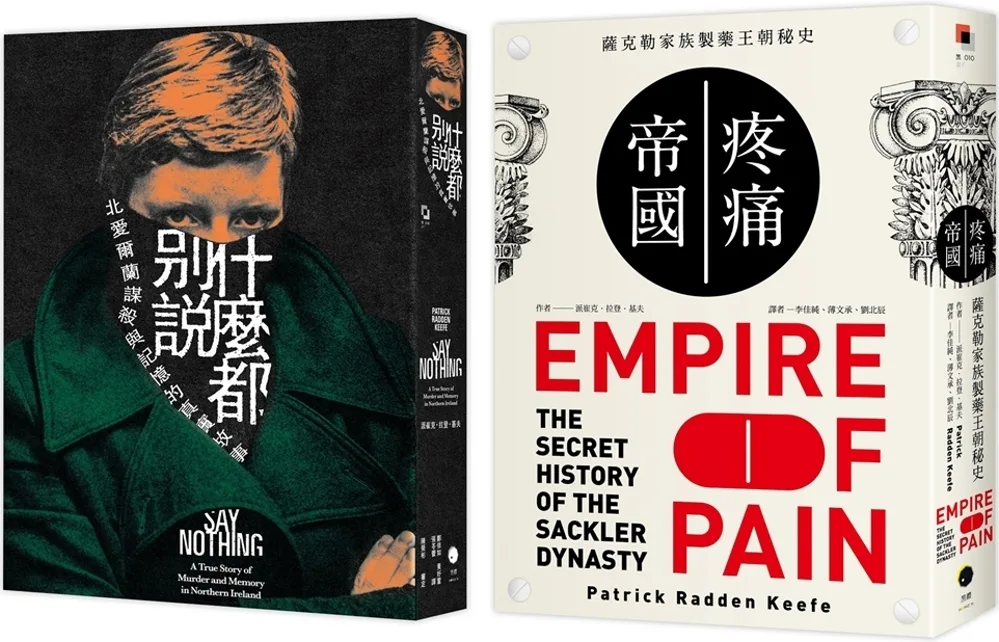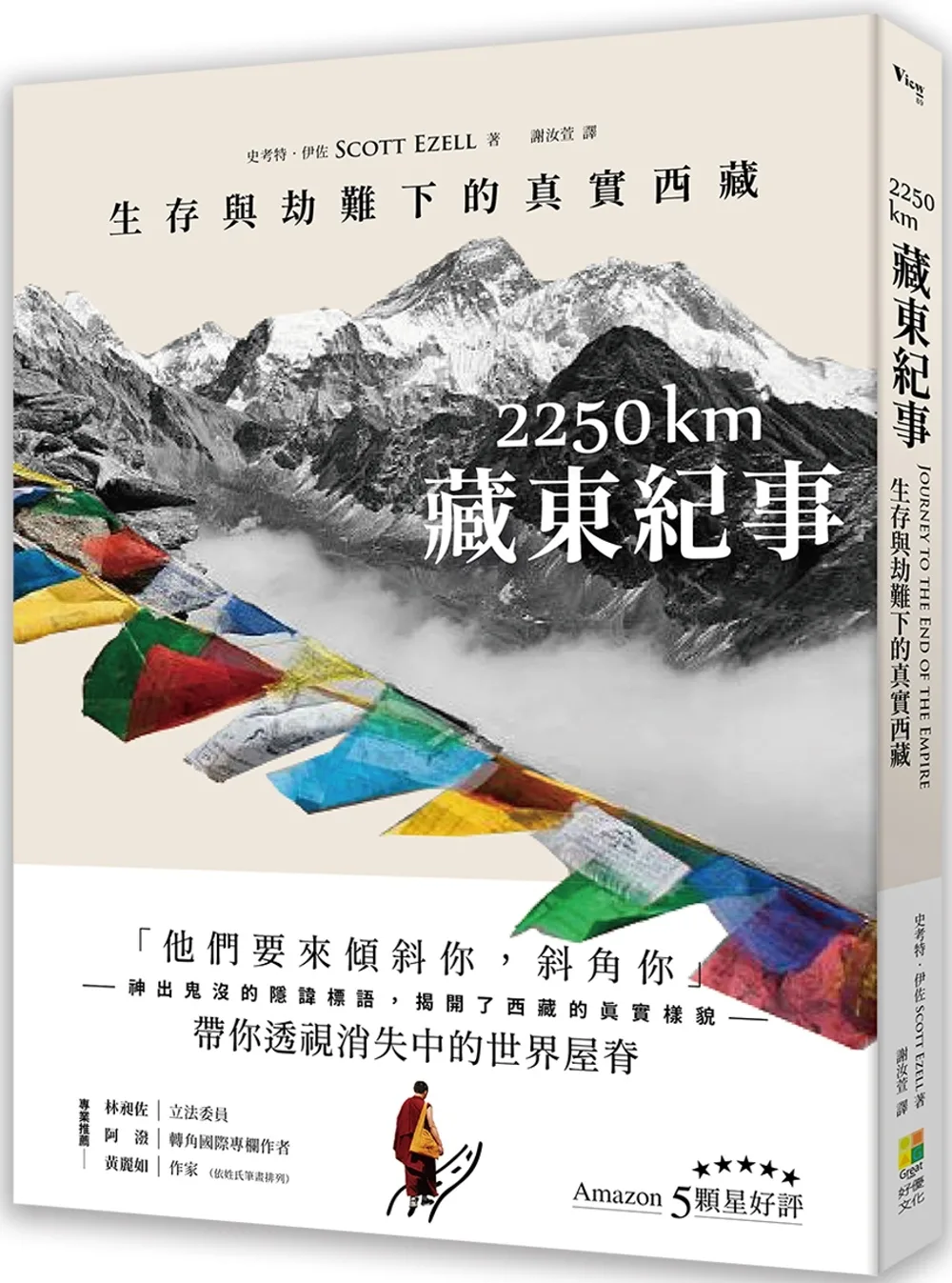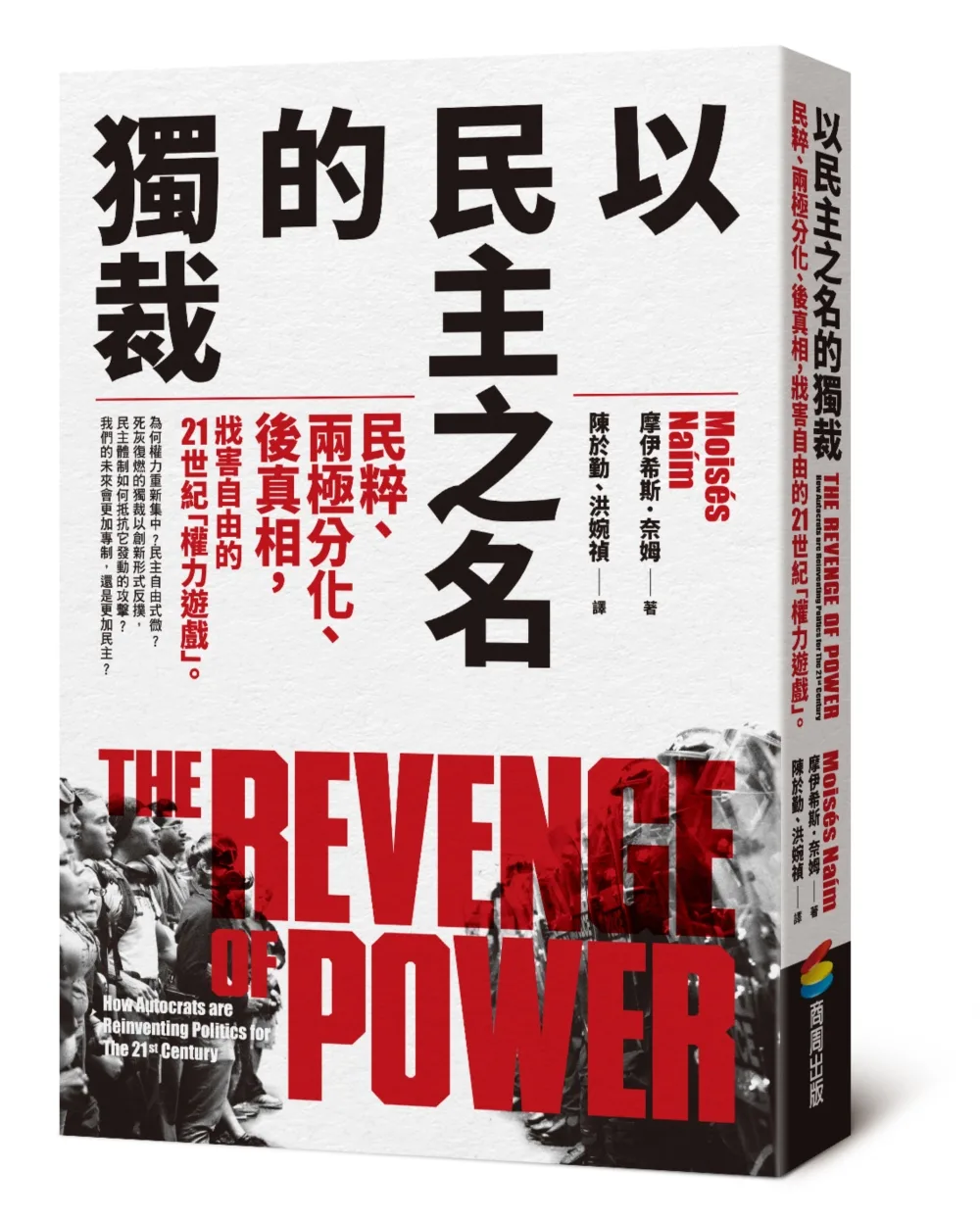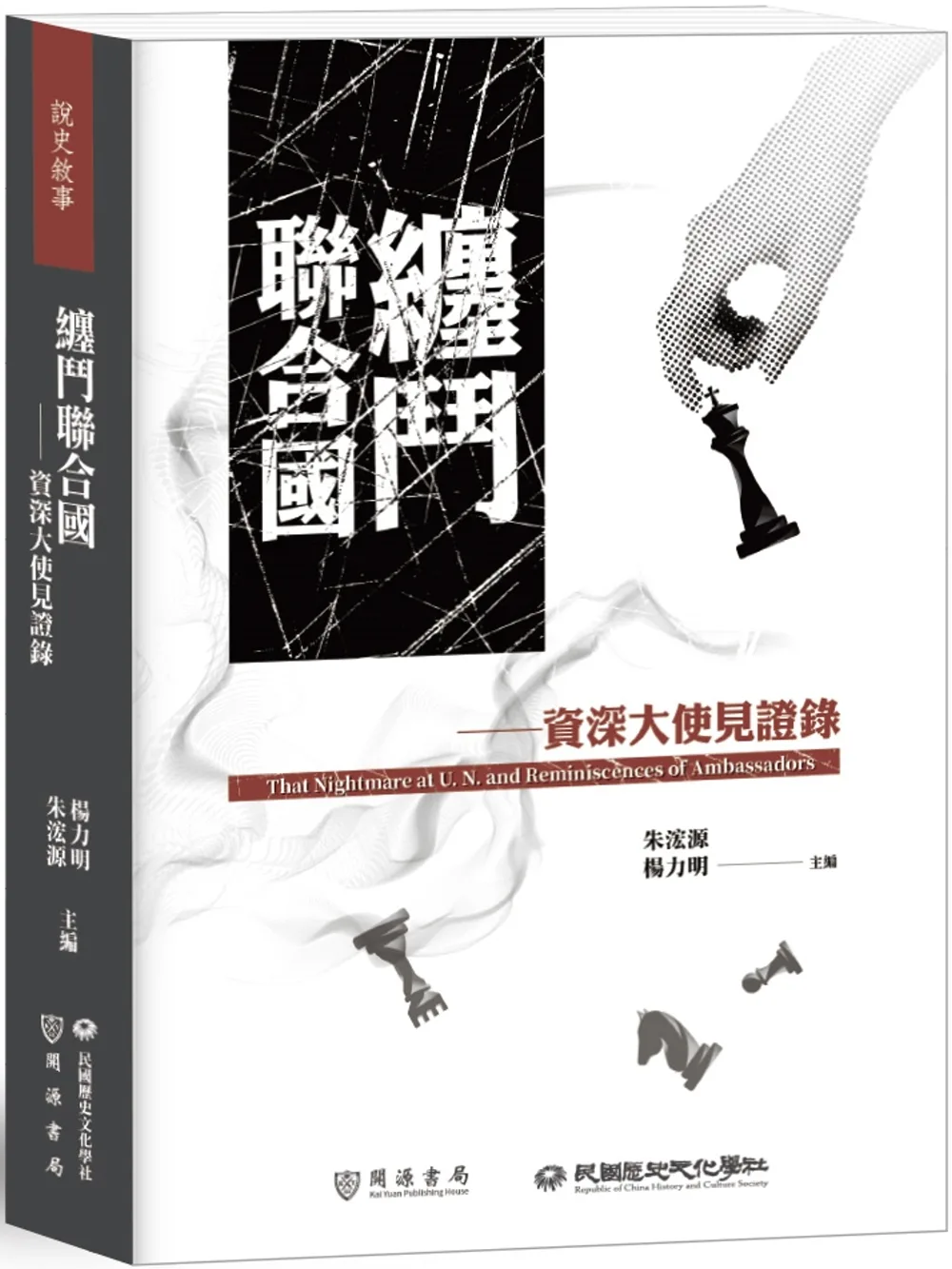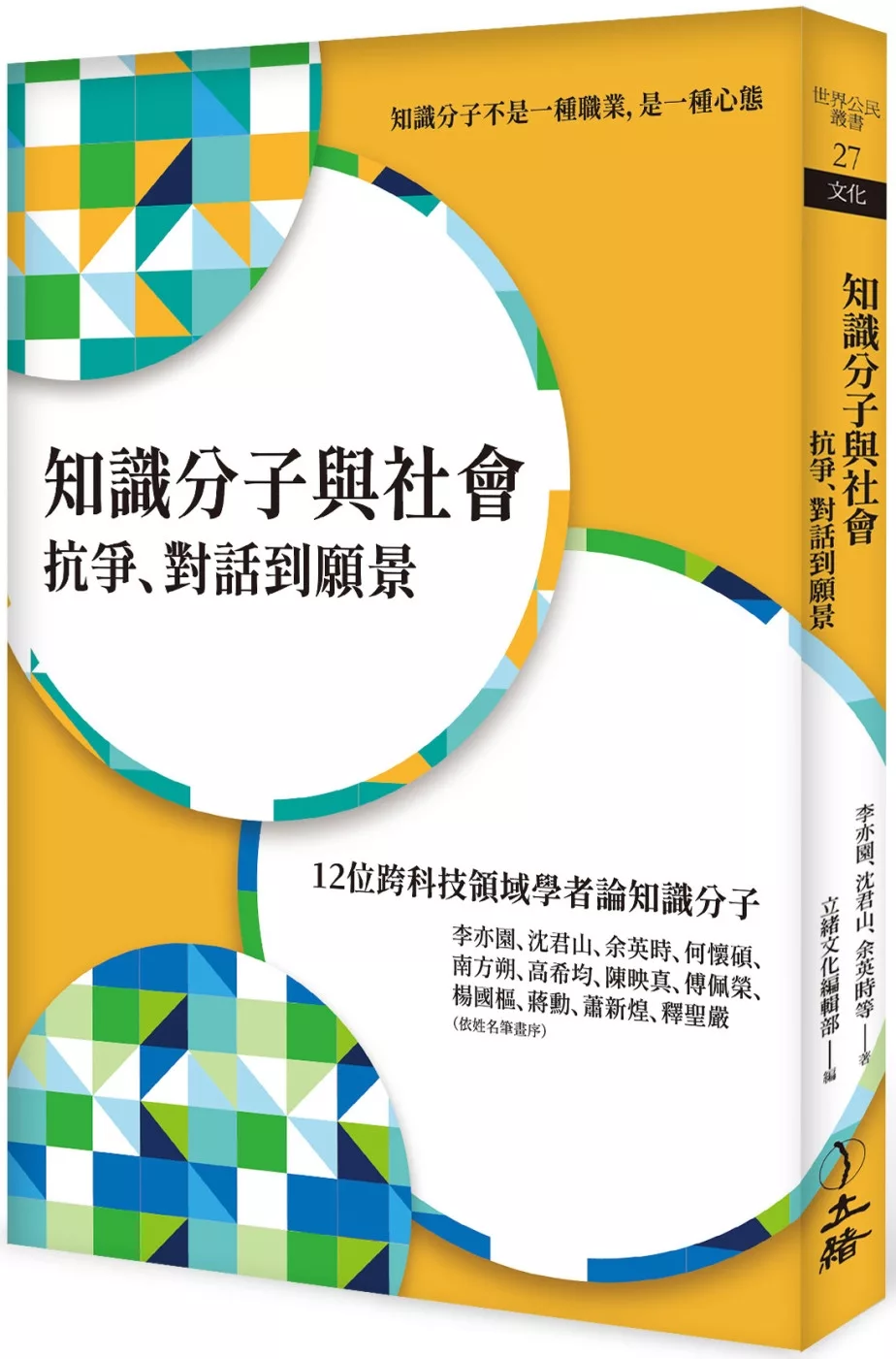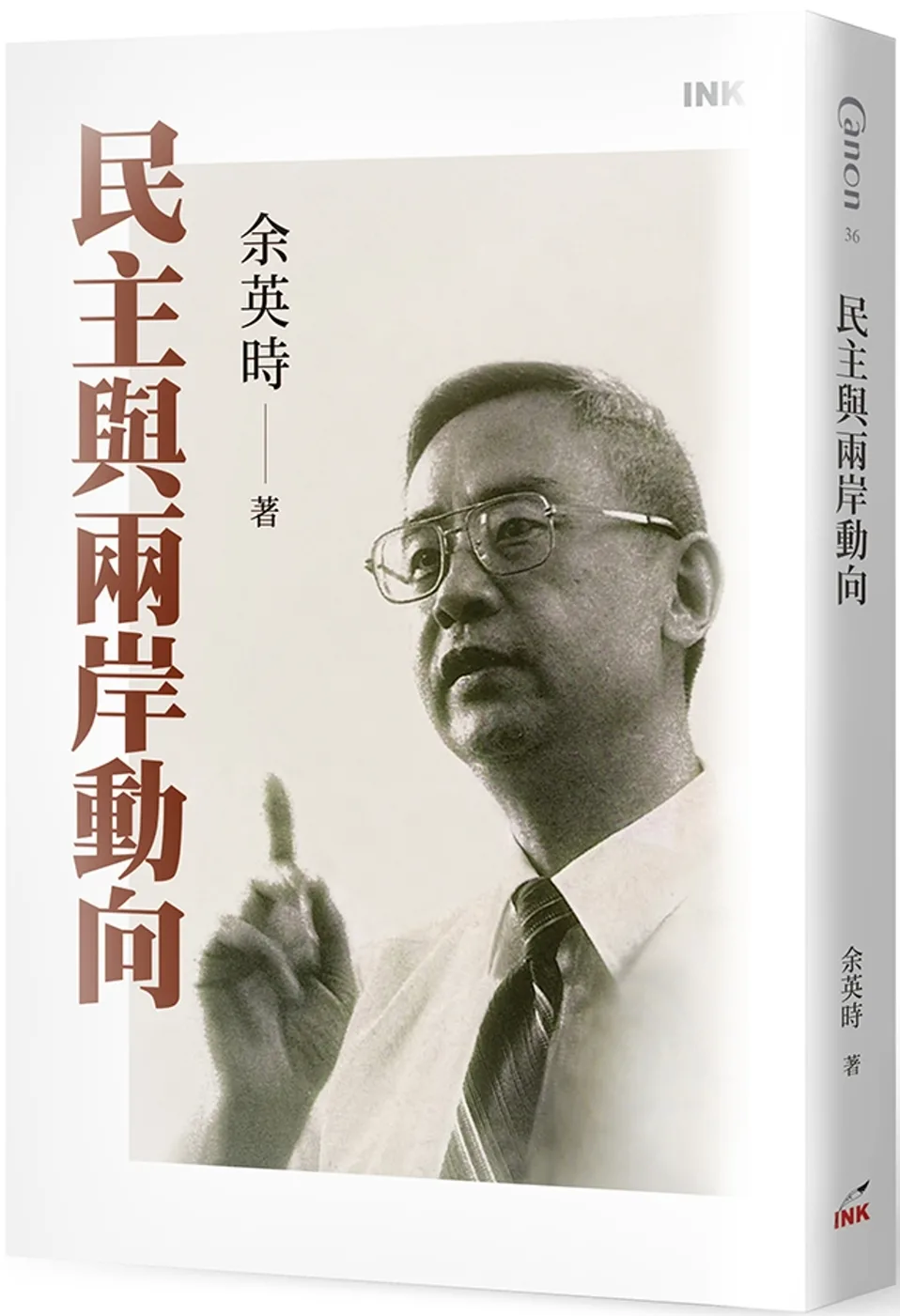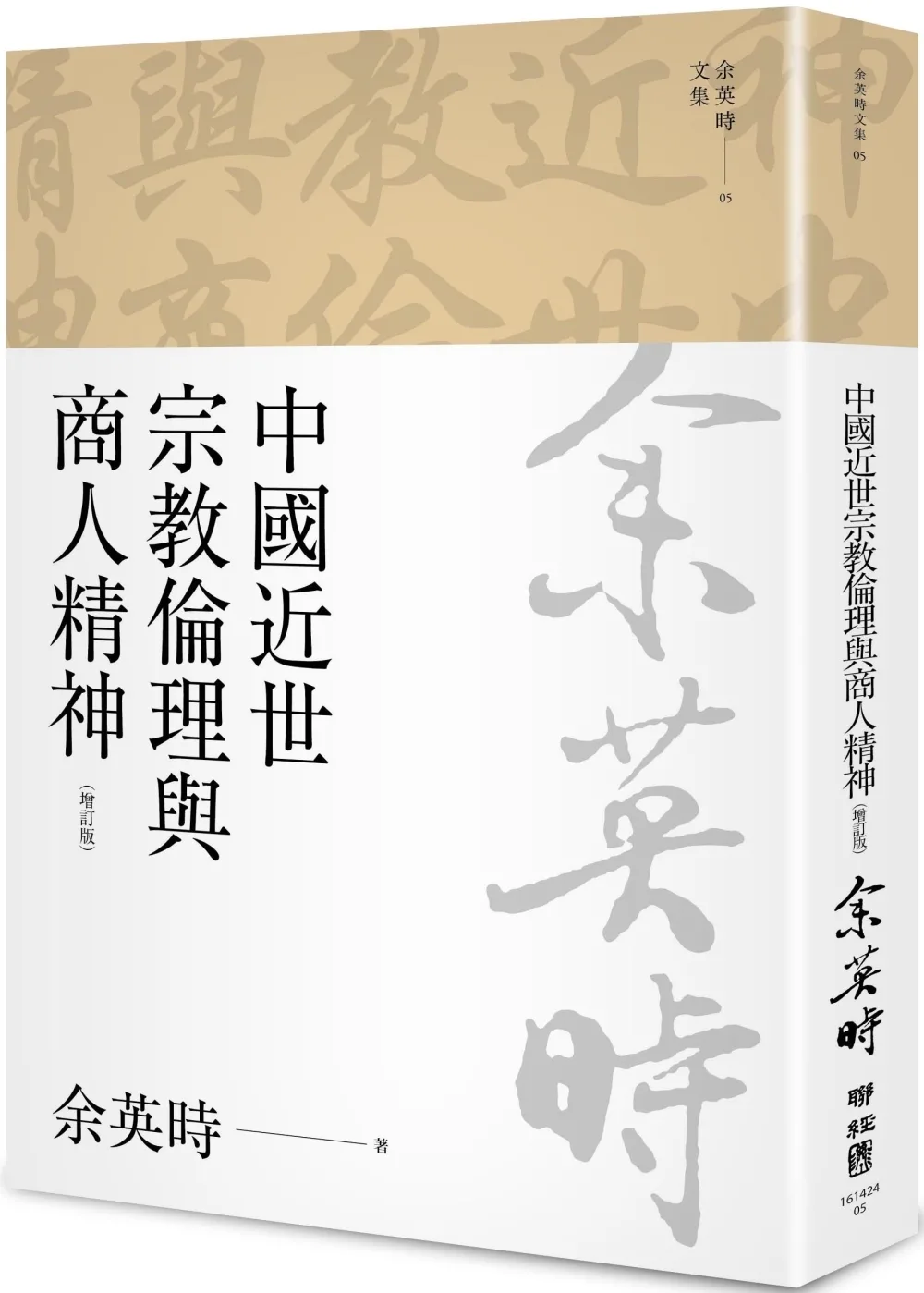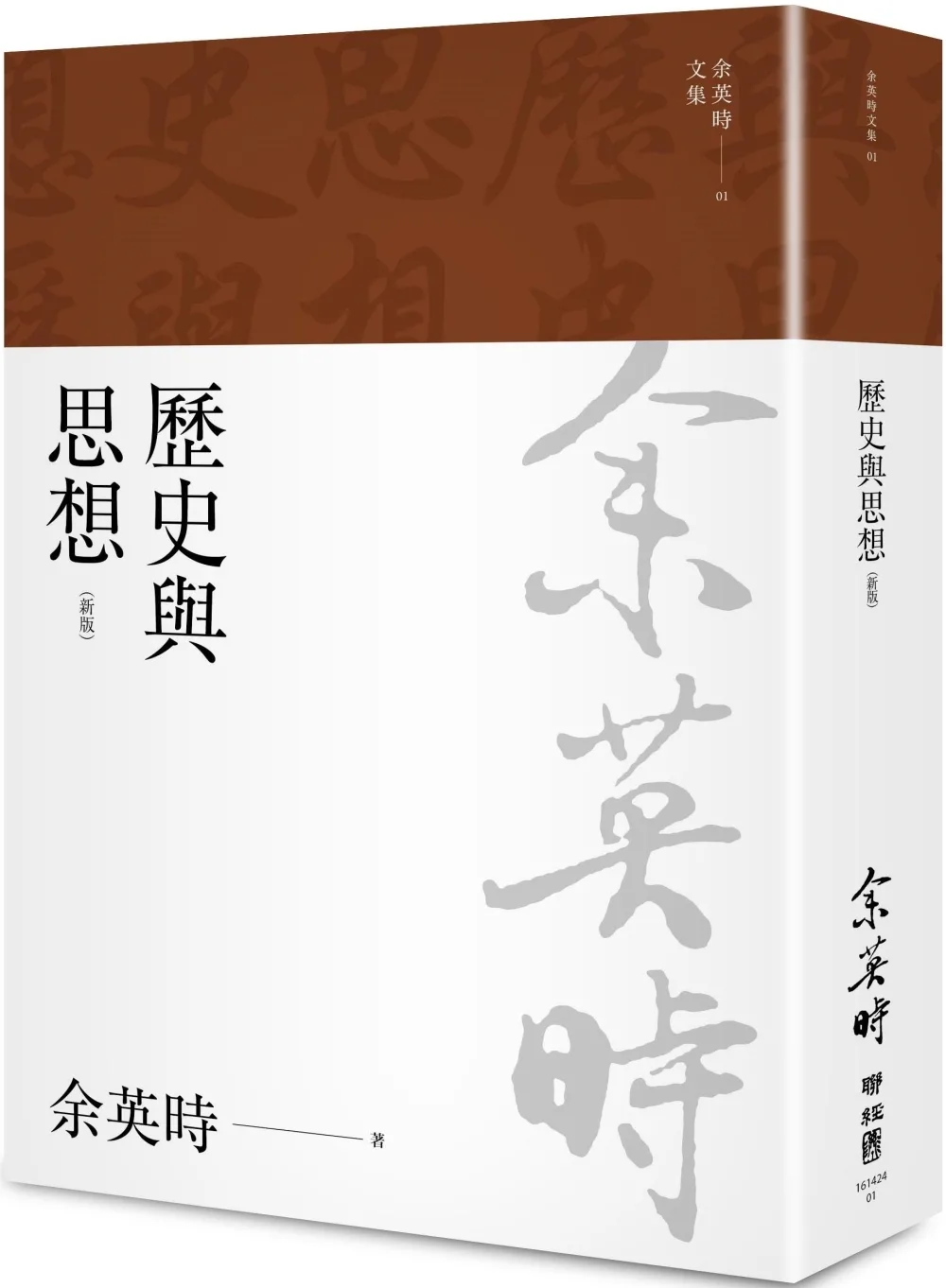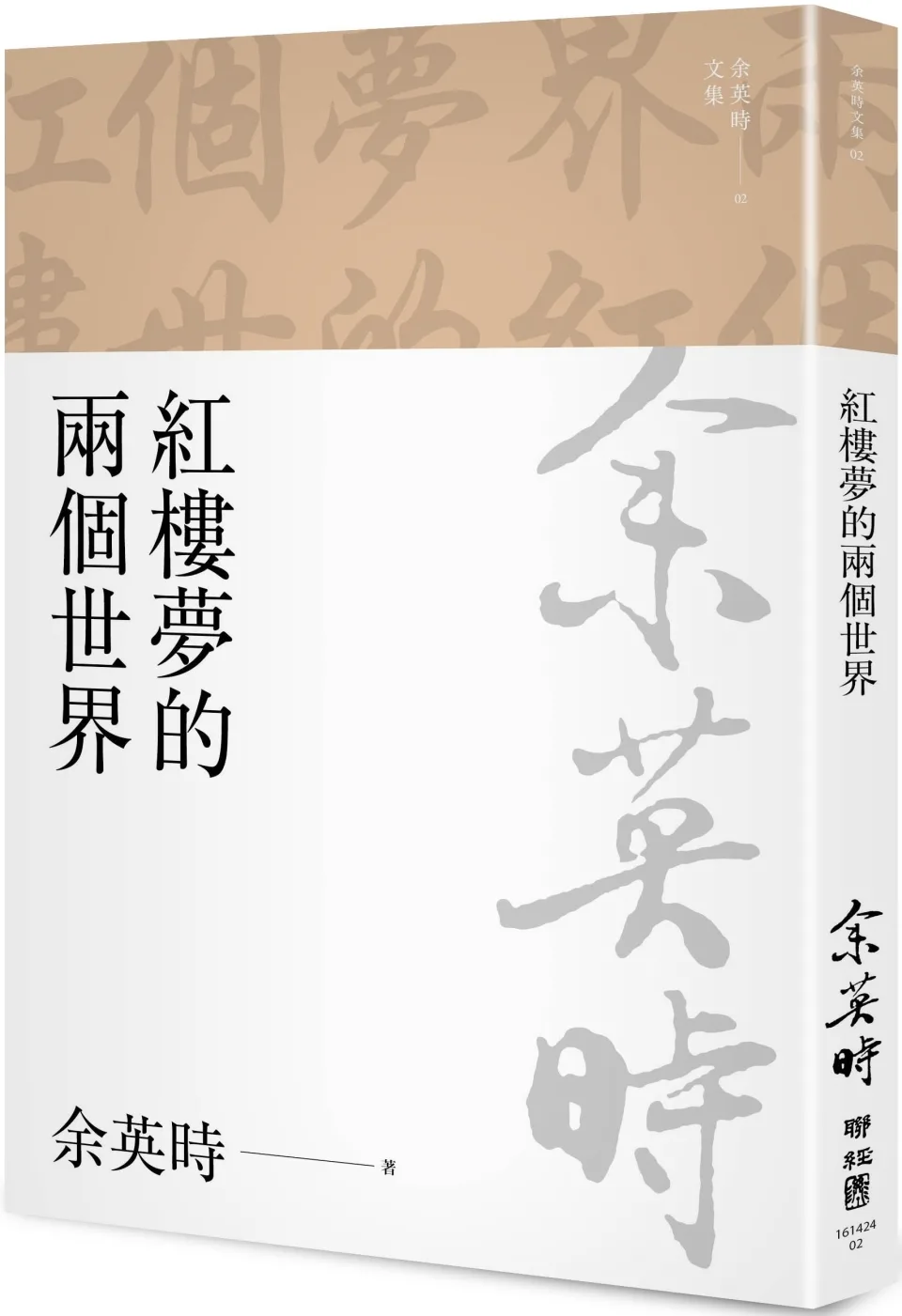序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自序
我近兩年來思想的興趣集中在兩大問題上:一是文化哲學(philosophy of civilization),一是社會哲學(social philosophy)。前一方面曾寫成了若干篇論文,最近擬收為《文明論衡》第一集,由高原出版社印行;後一方面首先提出了自由與平等兩個概念及其關係加以討論,於是遂有本書之作。本書計分六章:首二章專論自由,三、四兩章專論平等,後兩章則綜論自由與平等的一般關係及其文化基礎。其中一、三、五三章曾分別發表於《自由中國》、《民主評論》、《人生》諸雜誌而略有修正。〈羅素論自由〉一文係介紹羅素於一九五○年發表的〈自由是什麼?〉之長文,我自己又復加添了一些註釋,載於《自由陣線》週刊,因此文可以與本書相互啟發之處甚多,故一併附錄於後。前年我曾為人人出版社譯過一本英人湯姆遜(David Thomson)所著之《平等》(Equality),亦與促成我對於自由與平等的研究興趣有關,甚望本書讀者能同時參閱。
社會哲學原與文化哲學一脈相通,而後者則是對當前人類問題更高、更深一層的探索。因此本書雖屬於前一方面,而頗有涉及文化範疇之處,最後一章更企圖對二者加以理論上的溝通。我在此學無所成的階段妄談這些大問題,實在有點過於不自量力。好在我並沒有「創建理論體系」的妄念,並且在相當程度上我是做著整理與接受前人思想遺產的工作。百餘年來中國人民的苦難以及知識分子所應有的良知時時在激發著我,使我不能自已地考慮到當前社會文化的種種問題。儘管我的知識淺陋、見解幼稚,但是自信總還有一點「不忍之心」。何況現實問題的解決也並不完全是知識所能為力的,思想的現實性更不必然與知識的高低成比例;任何人祇要肯本其良知在這些問題上用心都可有其一得之見—當然一得之見並不就是理論,更不能算做學術,但卻不能不承認它也是一種思想的結晶。古今中外的第一流思想家與哲人們的學術思想究竟影響人類實際社會行為的有多少?這也是很值得人疑問的。中國的孔子、西方近代的盧梭與馬克思大概要算是少數例外了。可是孔子並未能及身見其道之行,盧梭、馬克思的真正影響也發生在身後。而後兩人在西方學術思想史上的地位及其知識上的真成就亦不能令人無疑。要講知識的真實性,自然科學遠較社會為可靠,可是一部自然科學史上仍然充滿了錯誤的知識。社會是不斷變動的,人與人的關係不可能是完全穩定的,因此人們關於社會規範方面的知識便很難有永恆的「真」可言,而祇能在一定的空間與時間的交叉點上採用「適」作衡量其價值的標準。
基於這種認識,我雖自知缺乏足夠的知識,還是大致地寫了不少有關社會文化之類大問題的文章。我相信把學問視為一己之私的「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至少也快要過去了!我個人一方面固然對純學術研究有更大的興趣,一方面實深感此時此地殊不容我「兩年不聞窗外事,一心祇讀聖賢書」。縱使我今天能寫出斯威登堡(Emanuel Swedenborg)那樣艱深博大的形上學體系的著作,如果祇能賣出四本的話,我還是不屑寫的。我所寫的千言萬語儘可以一無價值,但祇要它與苦難時代的苦難中國有關,而且真是我的良知要我如此寫的,則無論它是否在學術上有貢獻,我都是一樣心安理得的。因此我希望讀者不要用嚴肅的眼光來看本書所收集幾篇文字。這樣才可以減輕一點我個人的心理負擔。
?
余英時一九五五年「五四」紀念日於香港新亞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