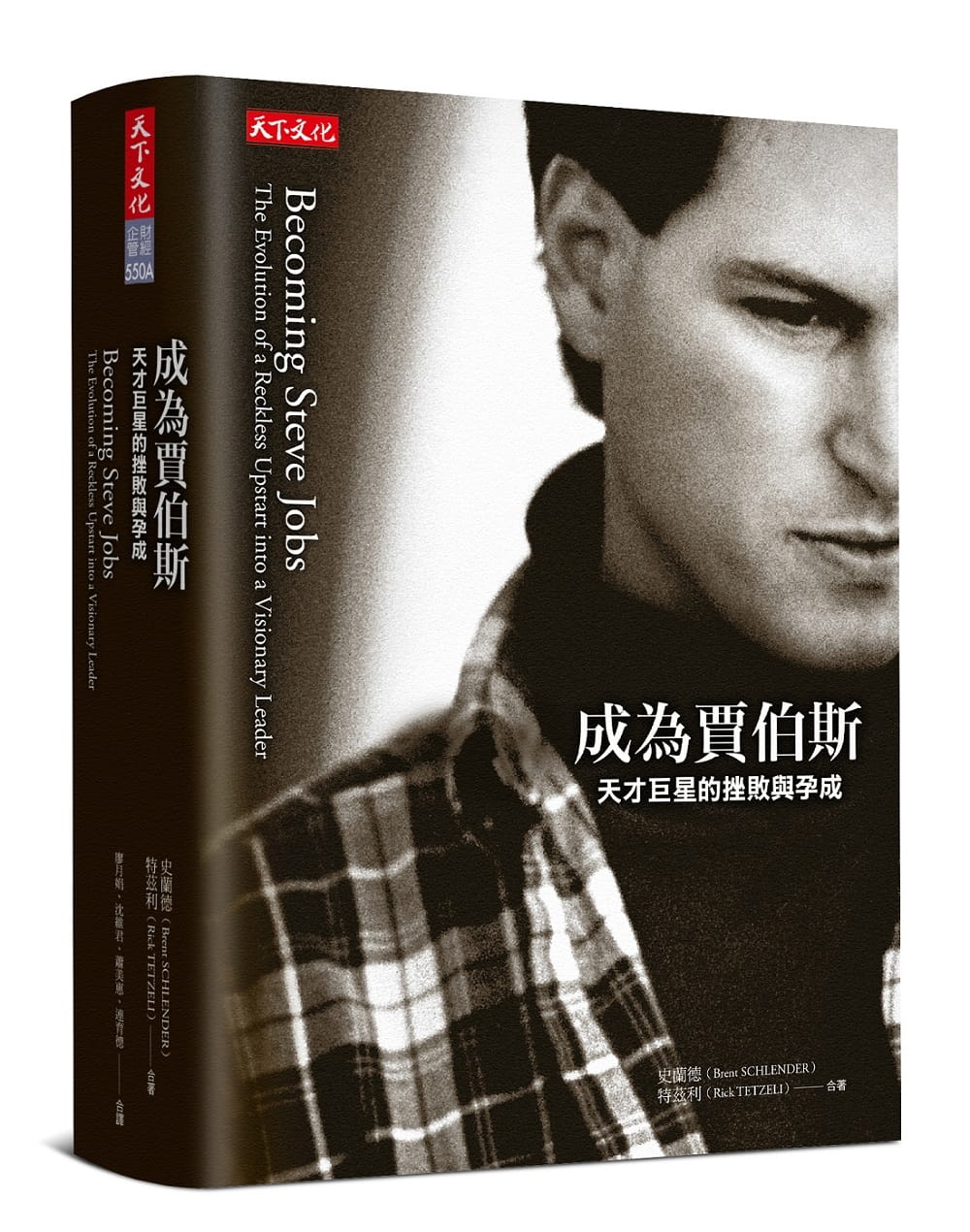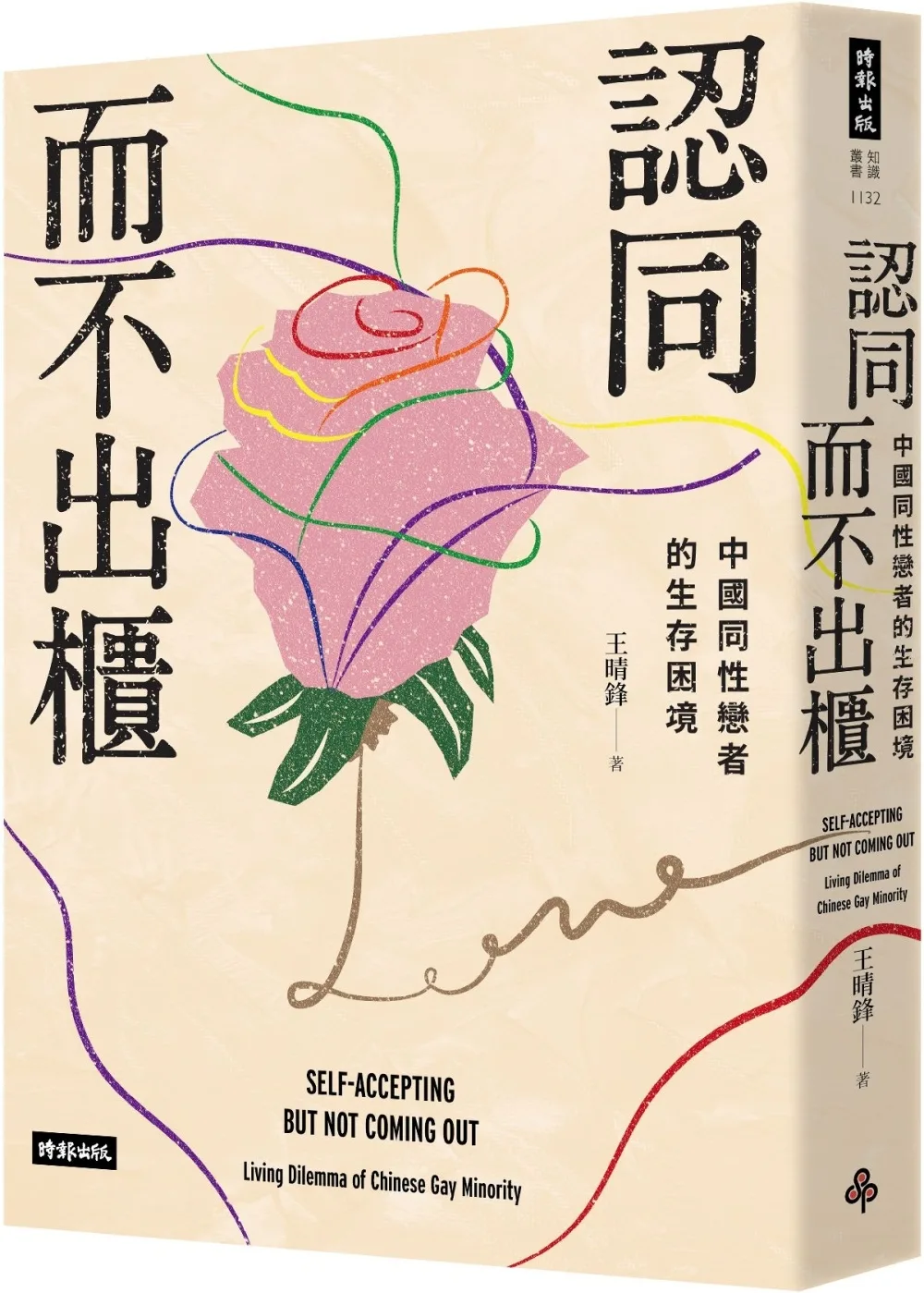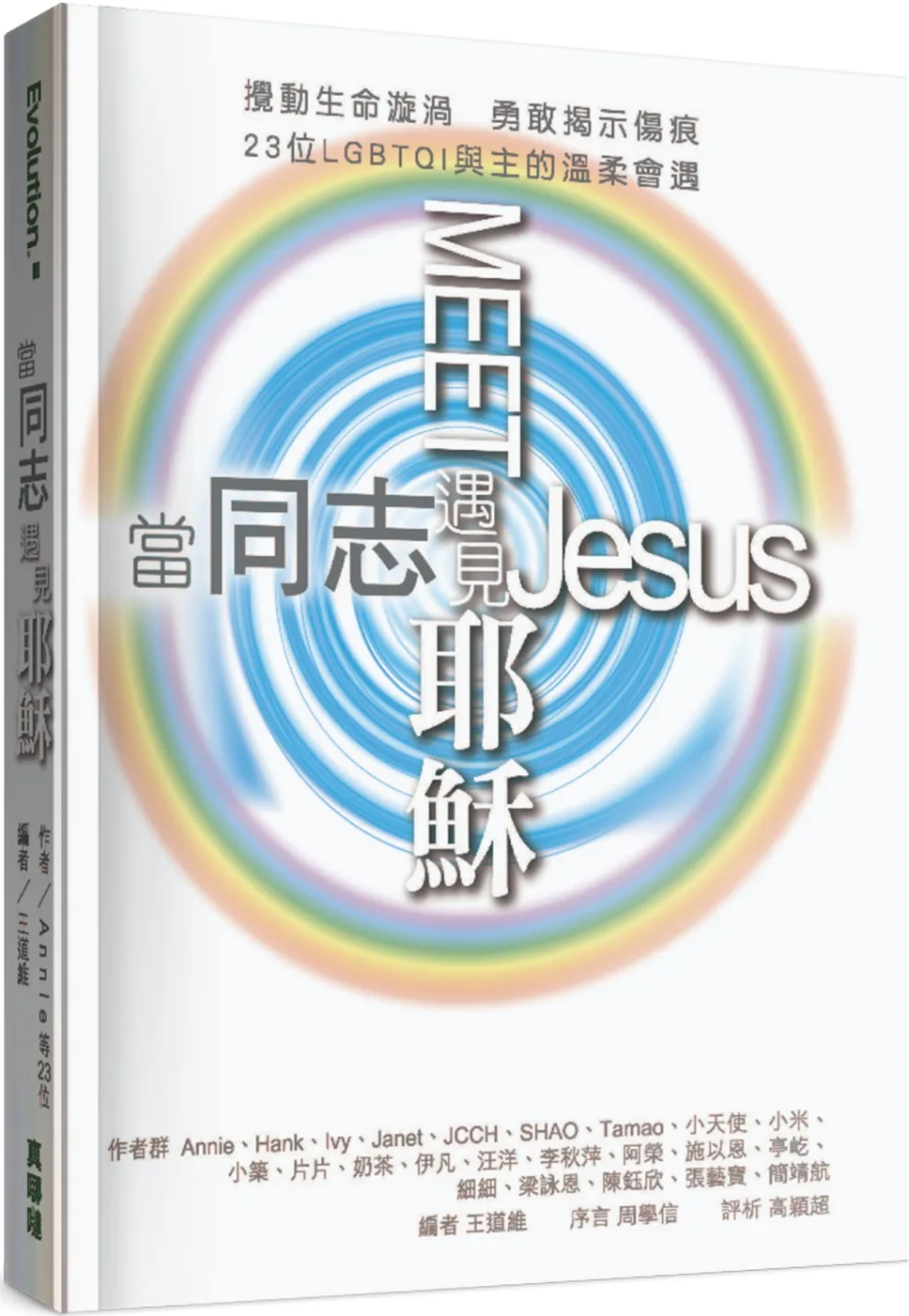當前中國社會的同性戀者處於何種生存狀態?
他�她們浮出歷史與現實的地表了嗎?
他�她們又面臨了哪些集體困境?
他�她們浮出歷史與現實的地表了嗎?
他�她們又面臨了哪些集體困境?
身分認同�出櫃是連結個人與社會的關係紐帶。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社會歷經同性戀「非罪化」與「非病理化」的過程,但對許多同性戀者而言,出櫃仍然不僅是個人的「私事」,也是重要「家事」。在制度忽視、文化缺失、社會氛圍以及傳統觀念的壓力下,向家庭成員出櫃是一項沉重的議題,常使同性戀者深陷同性情感與家庭責任的衝突之中。
深描當代中國同性戀者的生活及話語
反思根深蒂固的文化偏見和社會問題
《認同而不出櫃》懸置各種先入之見的污名、標籤和想像,結合文獻資料、參與觀察和訪談等研究方法,從個體、家庭和國家三個層面探討當前同性戀者的生存狀態。微觀層面涉及同性戀個體的情與性;中觀層面論述同性戀婚姻(同直婚與形式婚)、家庭出櫃的代際矛盾與文化衝突;宏觀層面則討論同性戀運動的各種形式。王晴鋒試圖在同性戀身分認同的基礎上關注家庭出櫃問題,並解析中國同性戀社群為什麼傾向於「認同而不出櫃」。
名人推薦
專文推薦
李銀河(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共同推薦
王增勇(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教授)
杜思誠(社團法人台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祕書長)
洪凌(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
桑梓蘭(密西根州立大學教授、《浮現中的女同性戀:現代中國的女同性愛欲》作者)
(依姓名筆畫排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