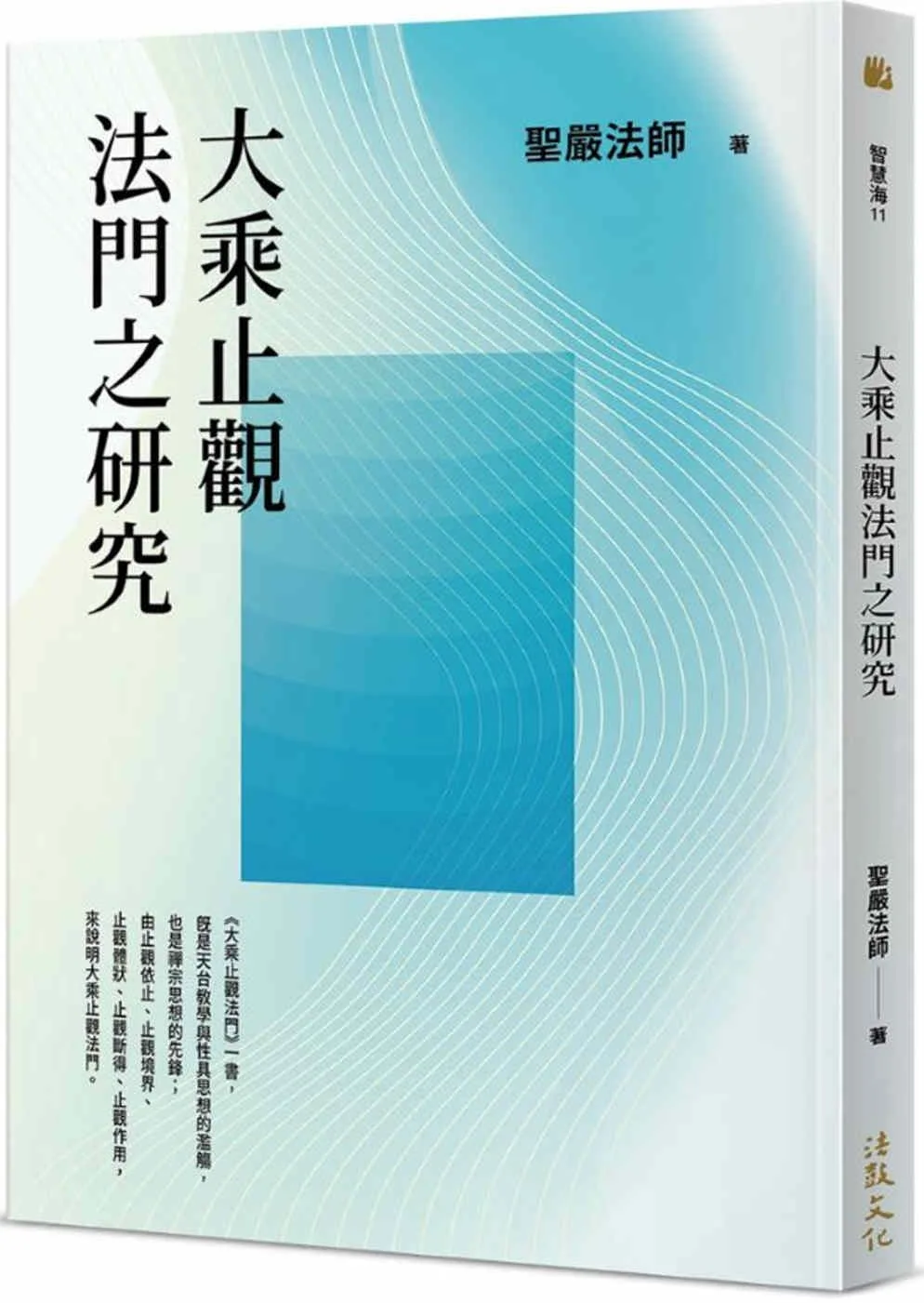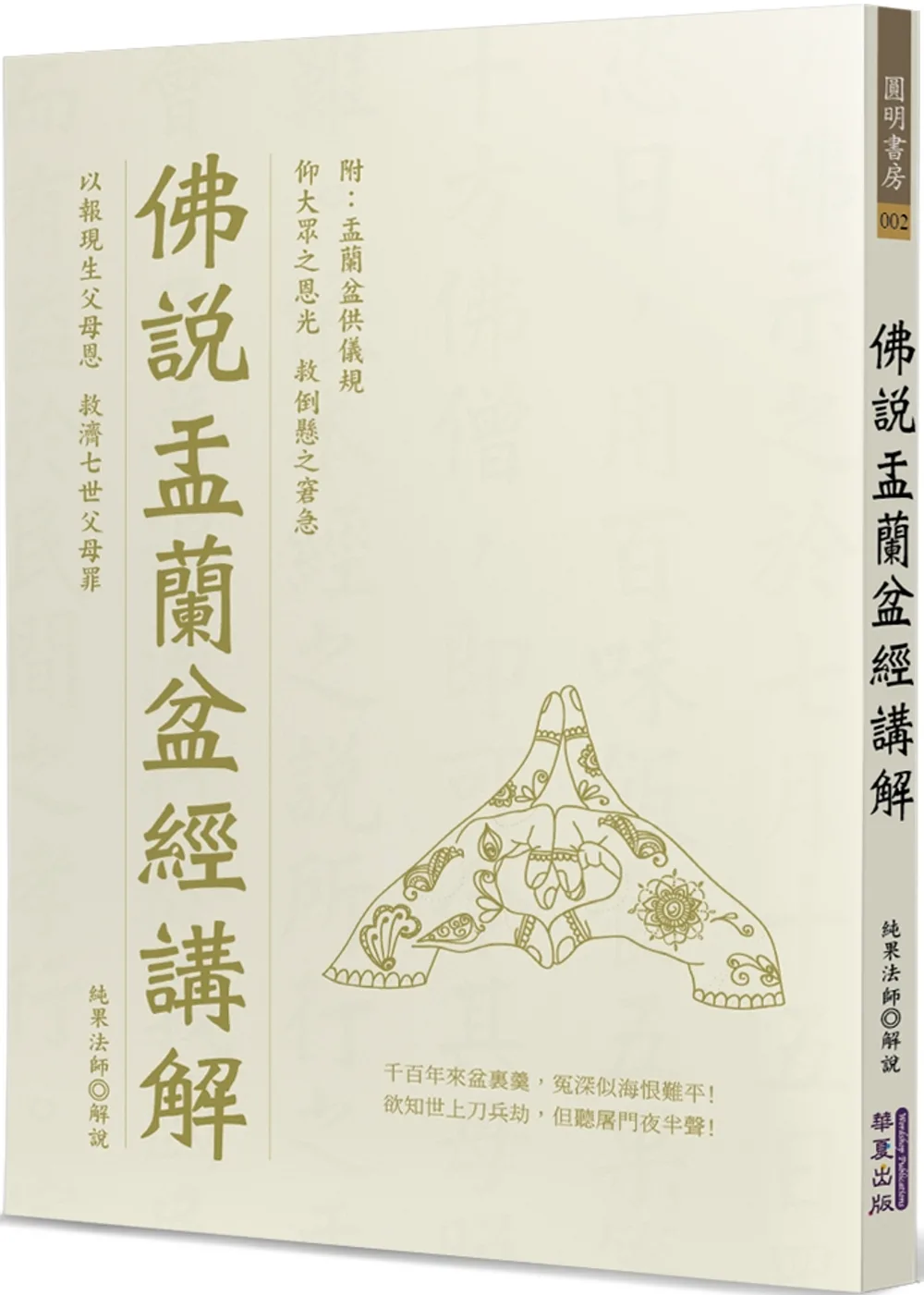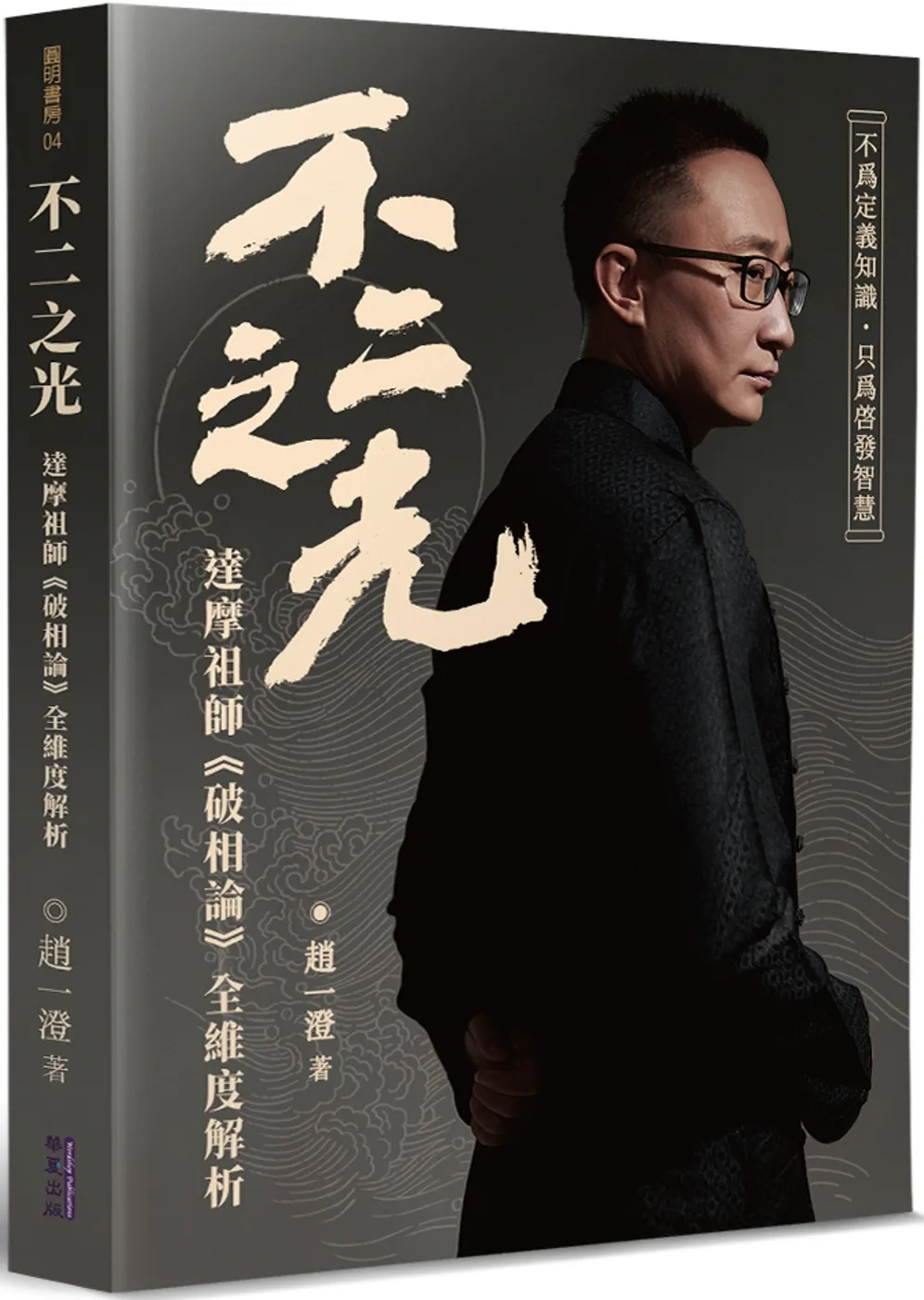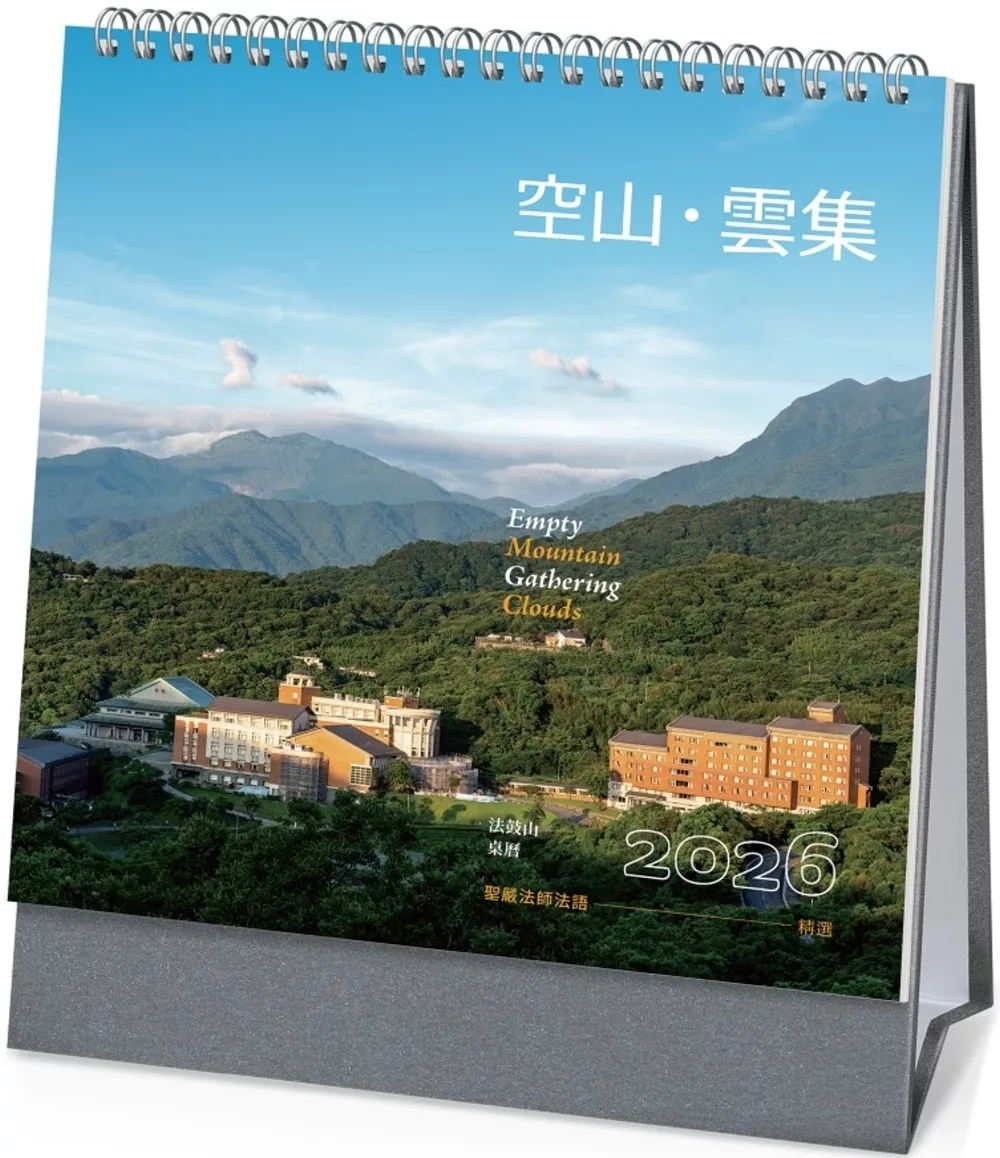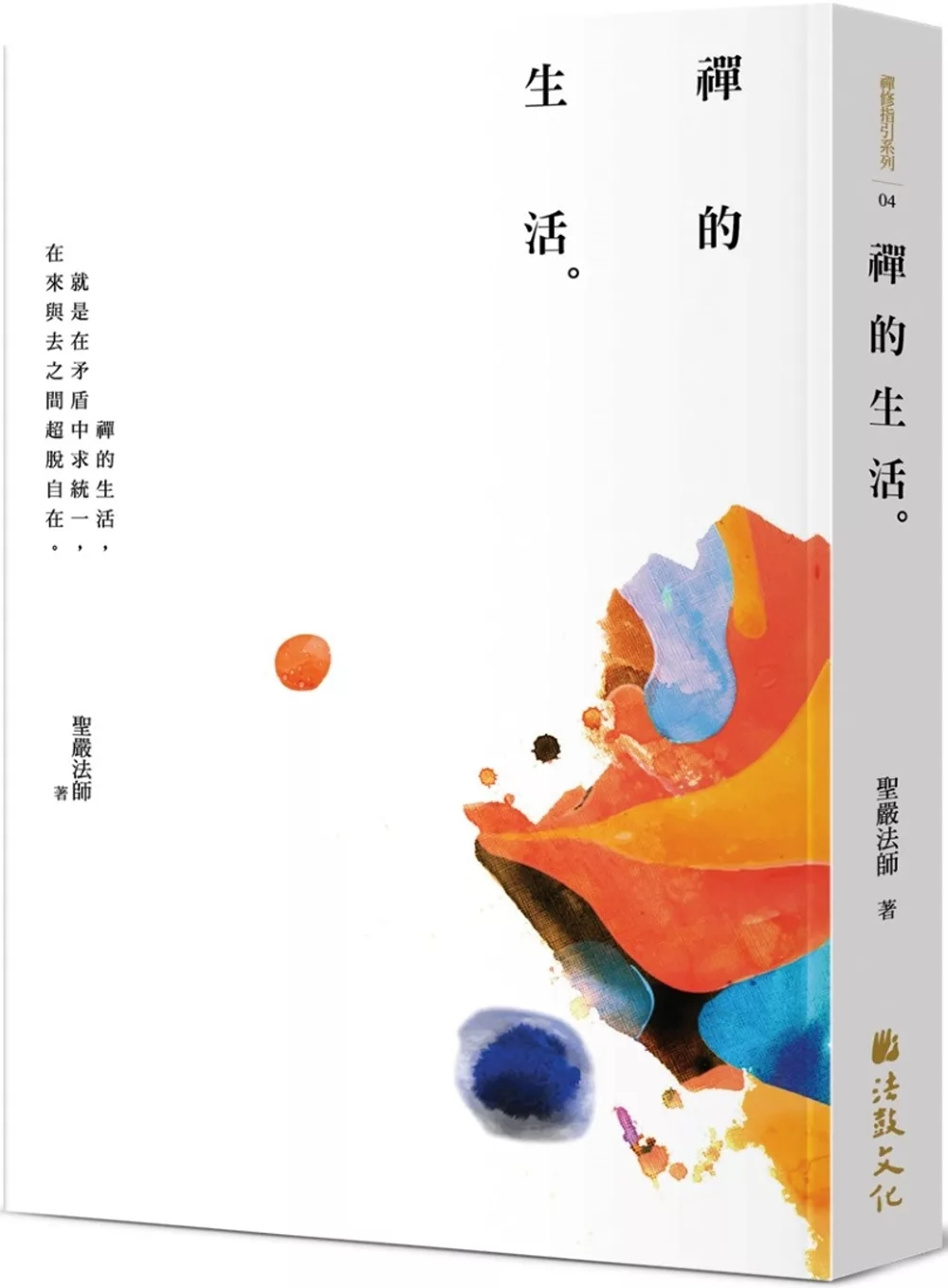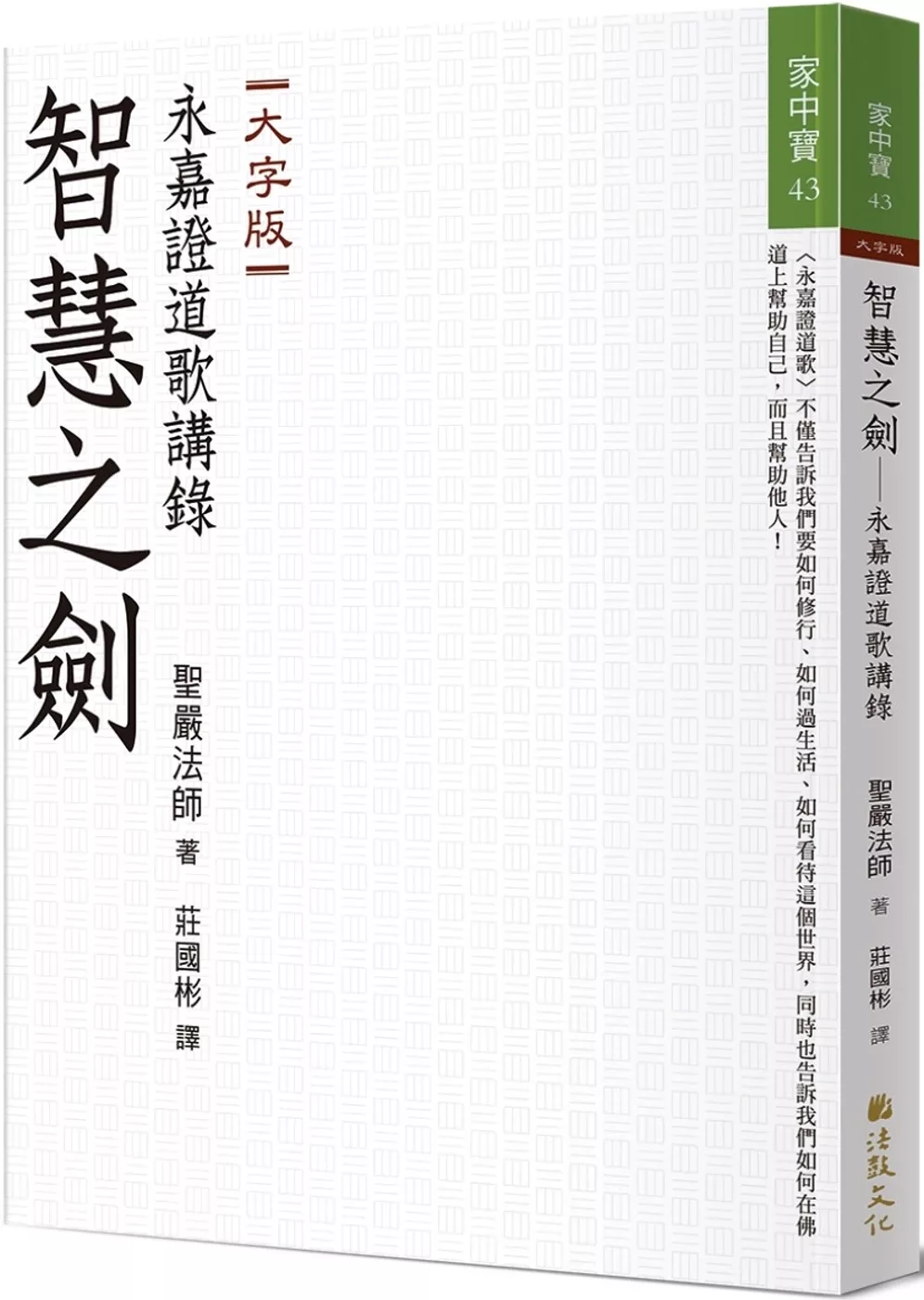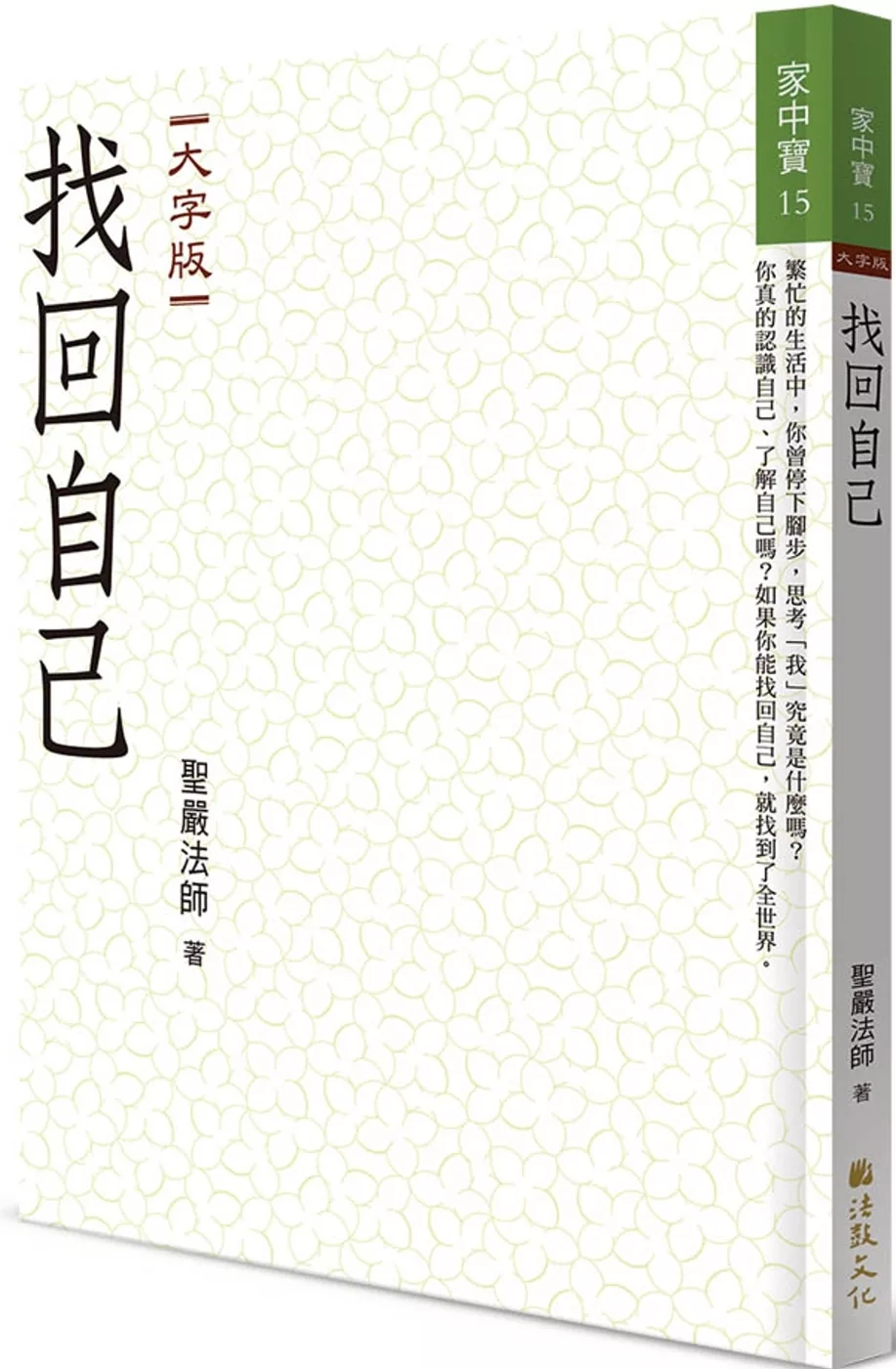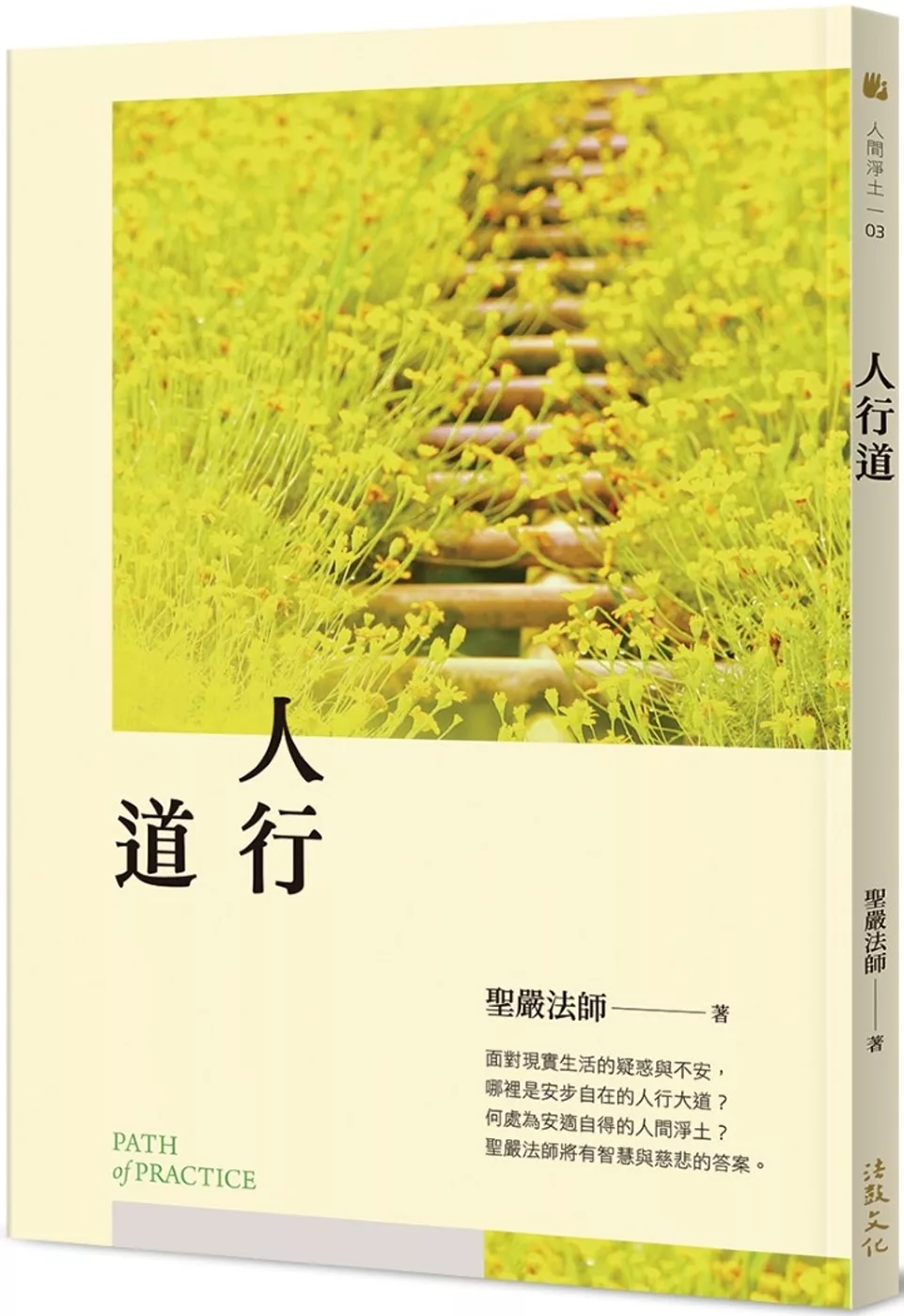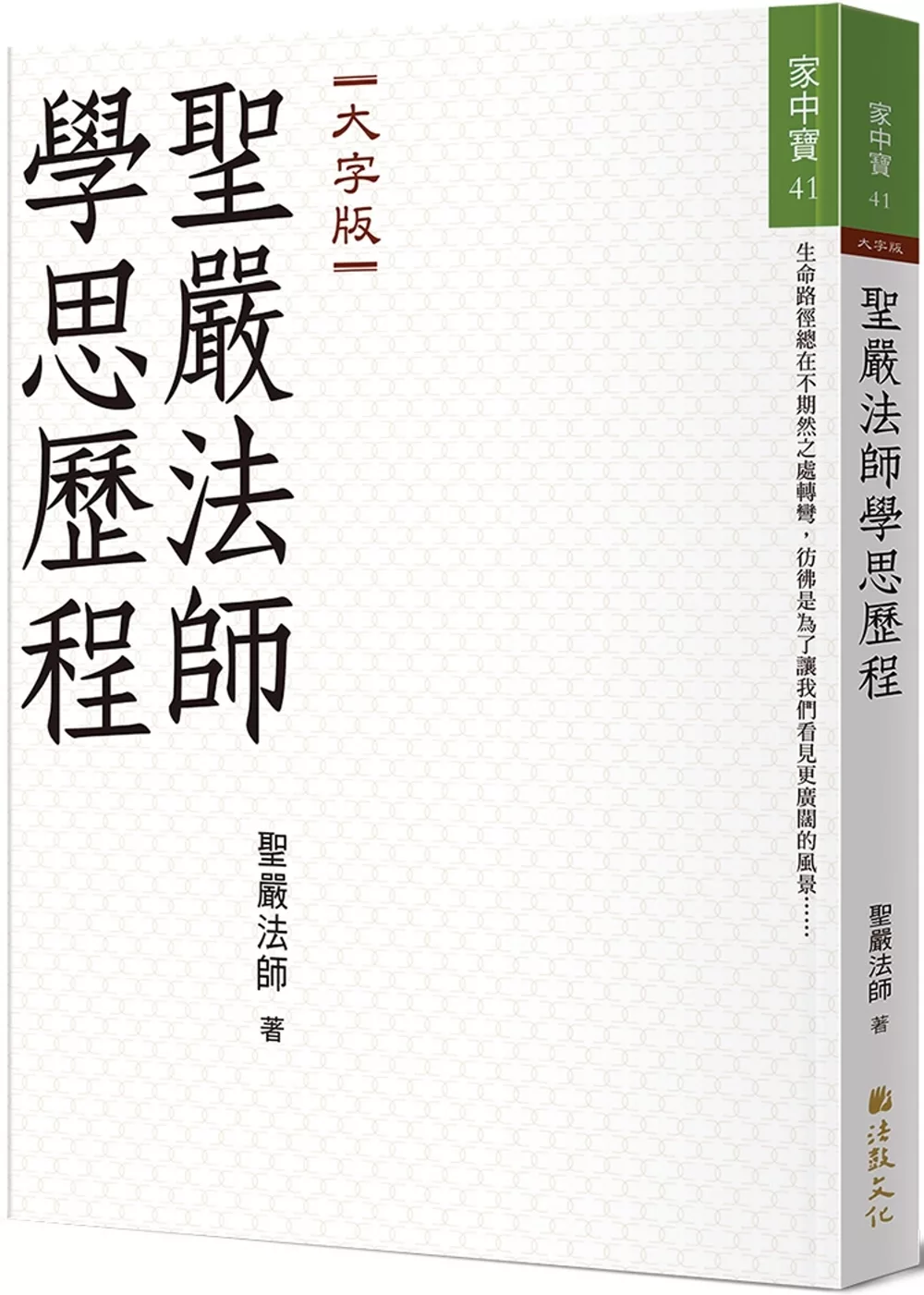前言
當我剛把碩士論文,向學校提出之後,便接到東老人的來信,要我把論文抄一份寄回臺灣,送請樂觀老法師在《海潮音》發表,這當然是我應做而想做的事,同時也感激東老人對我留日以來的關心如此。
其實,我在留日以來的二十個月之中,要想寫出如何精彩的論文,殊不容易。因在第一年中,僅在對於日本語文上,已花了很多精力,另外又得趕學校的碩士課程,忙著趕完兩年之中必須修完的功課,還得抽時間寫些報導日本佛教現況的文字,寄回國內及香港發表。但當第一年的緊張過程剛結束,第二年一開始,就要準備學位論文的撰寫了,近世以來的日本論文,完全學西洋方法,學會了很省力,但在從未用過這種方法的人,相當吃力,於是到處找資料,到處拜訪請教有關的名學者,加緊閱讀,加緊查檢各種工具書。不用諱言,直到現在,對於日文參考書,仍得勤於查字典辭書,始能完全讀通。在此期間,我曾兩度去成田山的圖書館,找明治時代以迄二次大戰之後的日本舊雜誌,至於東京都內的佛教學關係大學如東大、東洋、立正、大正、駒澤各圖書館自不用說了。
可憂的是近代日本學者之中,對於《大乘止觀法門》這部書的專家,簡直沒有一個,我的校長,也是我的指導教授板本幸男博士,他是正在拿這部書作教本,向我們碩士及博士班講授的,當他知道我選擇了這個論題之時,甚至也勸我另選一個題目。後來他看了我送的兩種書,才對我放了心。但我訪問另外幾位名學者時,收穫均不太理想,例如大正大學的關口真大博士,乃是研究天台止觀的權威學者,但他對於我寫的《大乘止觀》,也是愛莫能助。另外一位已逾八十高齡的二宮守人先生,他是天台宗的勸學,然他對於天台以前的本書,也僅對我做了幾點原則性的啟示。
但是,經過六個月的努力,不論寫得夠不夠分量,總算寫成了兩百數十張原稿的論文。而且大膽地直接用日文寫出來。當然,僅以十多個月的語文訓練之後,要想把它寫得優美,根本不可能,甚至在遣用動詞及形容詞的變化之時,往往也要鬧出笑話來。所以當我初稿寫完後,即有一位駒澤大學的佐藤達玄教授,為我做了潤色的工作,佐藤先生也僅四十六歲,和我之間,互為師友,是我留日以來,最好的日本朋友之一。最後,又有熱心的大正大學的牛場真玄先生,為我做更進一步的文字修正。可惜牛場先生為我修正時,我的論文清稿已向學校提呈出去了。然他是日文法的專家,故在他所修正的原稿上,使我看了之後的日文修養,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說起以上幾位日本教授,真是感念無已,他們對於我的論文的關心,好像就是他們自己的事那樣,不但見面時問我,甚至常用電話問我。他們對我的關切,更使我不敢自棄,結果,文章雖然不能真正算是我個人的,論文的內容、資料,是我找來組織成的,文中的思想和考察,也是我自己的。故當板本博士及副指導教授野村耀昌博士,看完我的初稿時,就使我得了幾句聽來很悅耳的話。
不用說,日本教授對一個外國比丘說幾句鼓勵的話,不足為奇,我也不以為這篇長達八萬字左右的論文,是一篇夠上國際水準的東西,但是敝帚自珍,且為向資助我留日費用以及關心我的師友們,表示謝意,還是把它譯成了中文,向諸高賢請教。
至於我為什麼要選擇這個論題?因為我是中國沙門,我的目標仍為中國佛教的前途。誰都知道,我國佛教,一向注重學行兼顧或悲智雙運,以實踐佛陀的根本教義或菩薩精神的自利利他法門,古來宗匠,無一不是沿著這條路線在走,東老人也嘗以寧做宗教家而勿做研究宗教的學者期勉。而在今天的日本,就是把佛陀的教義當作了學術化,把《大藏經》看作研究用的資料,所謂學以致用,他們僅把自己的研究考證的論文,做為謀取職業地位以及生活之資的工具,並非拿來做為自己修證的指針。
實則,若不實修實證,根本談不上對於佛法的理解,這一點在日本的現代學者們也不否認。因為實際的生活環境,迫使他們無法如實修證,所以近世的日本學者之中,僅有資料排比、文字考校、系統整理和歷史觀點的核對,卻沒有一個是偉大的思想家,更沒有一位偉大崇高的宗教家。例如東京帝國大學的中村元博士,在現前的日本佛教學界,已沒有比他出版著作更多的人了,但在日本學術界僅以「資料的寶庫」來讚美他,而非大宗教家,此與中國佛教及儒家正統的學者們比較,未免不夠深度或厚度了。
因此,《大乘止觀法門》這部書,在日本雖無專門研究它的學者,卻有零星的考證文字發表於戰前的一些佛教刊物,他們從文字及浮面的思想架構看這本書,以致懷疑非出於慧思禪師的述作。但是經我的研究之後,這部書確是慧思禪師晚年集其畢生思想的大成之作。在其由教義的疏導而進入教儀的實修之諄諄善誘下,能使一個凡人,深入法海,親證法性。所以當我研究了它之後,既可向學校的要求繳卷,又可做為自己自修方便的依準。同時,此書在我國教界,弘揚的人也很少,藉此機緣,向國內教界,借花獻佛,期收拋磚引玉之效。
一九七一年佛誕日於東京斗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