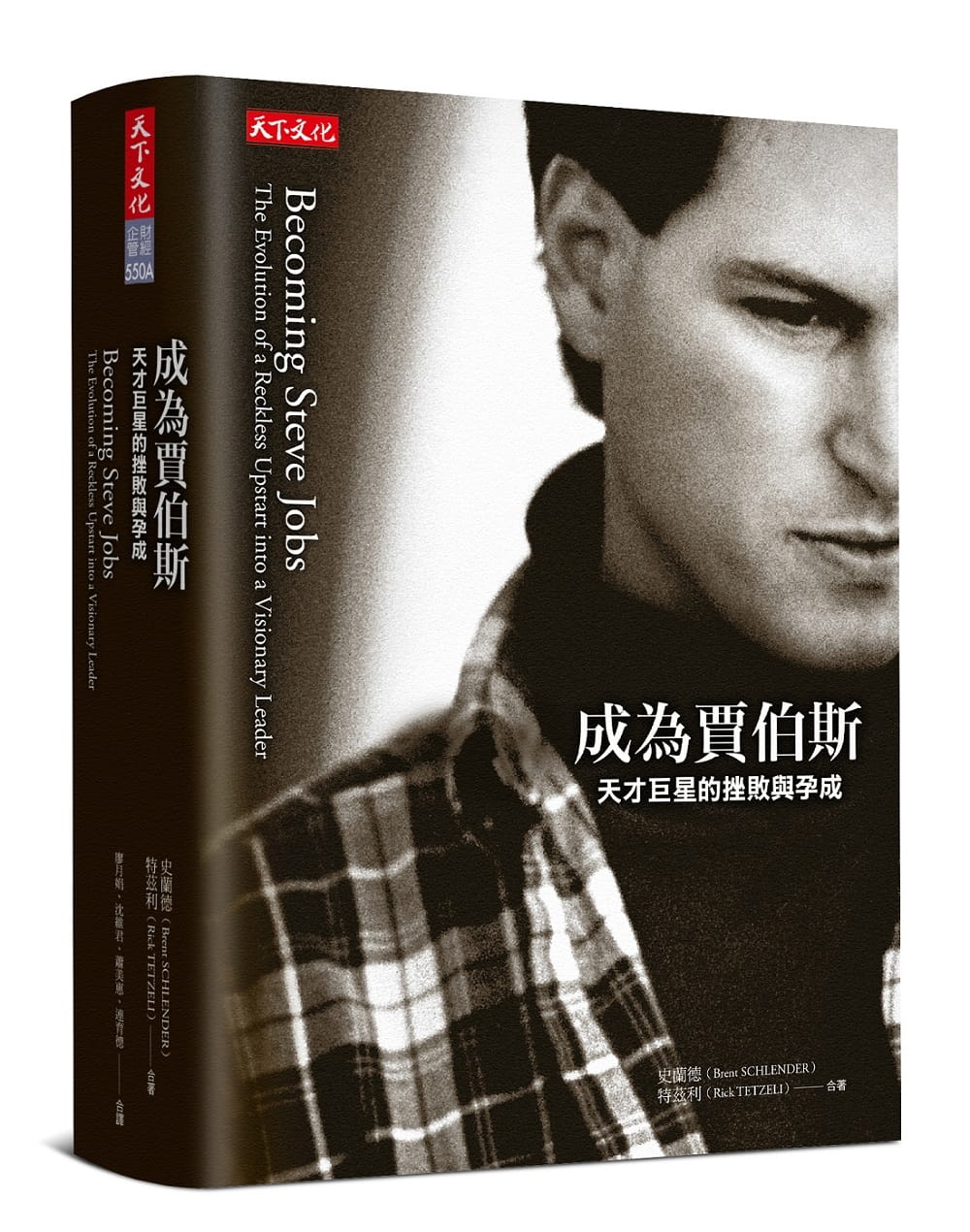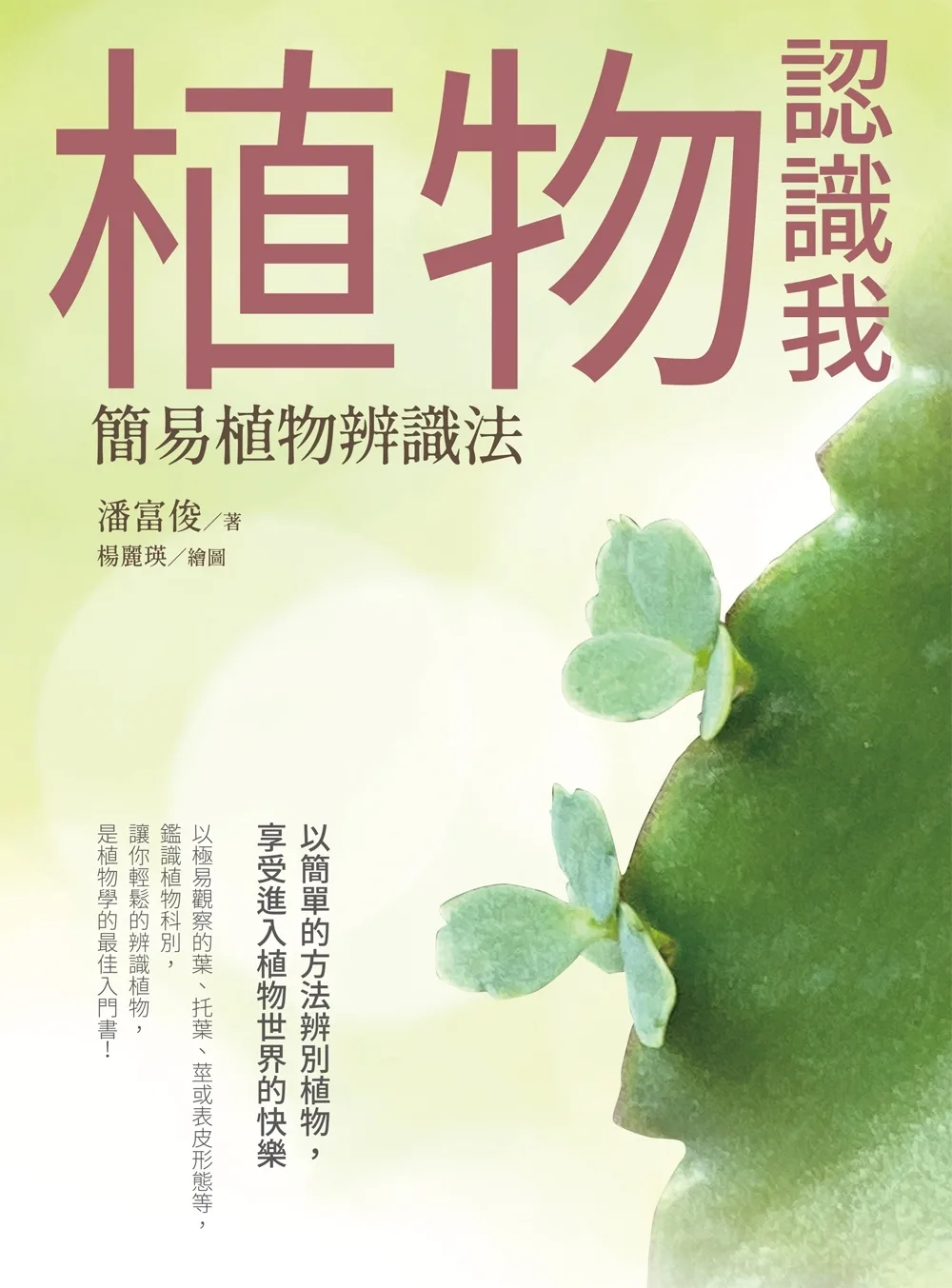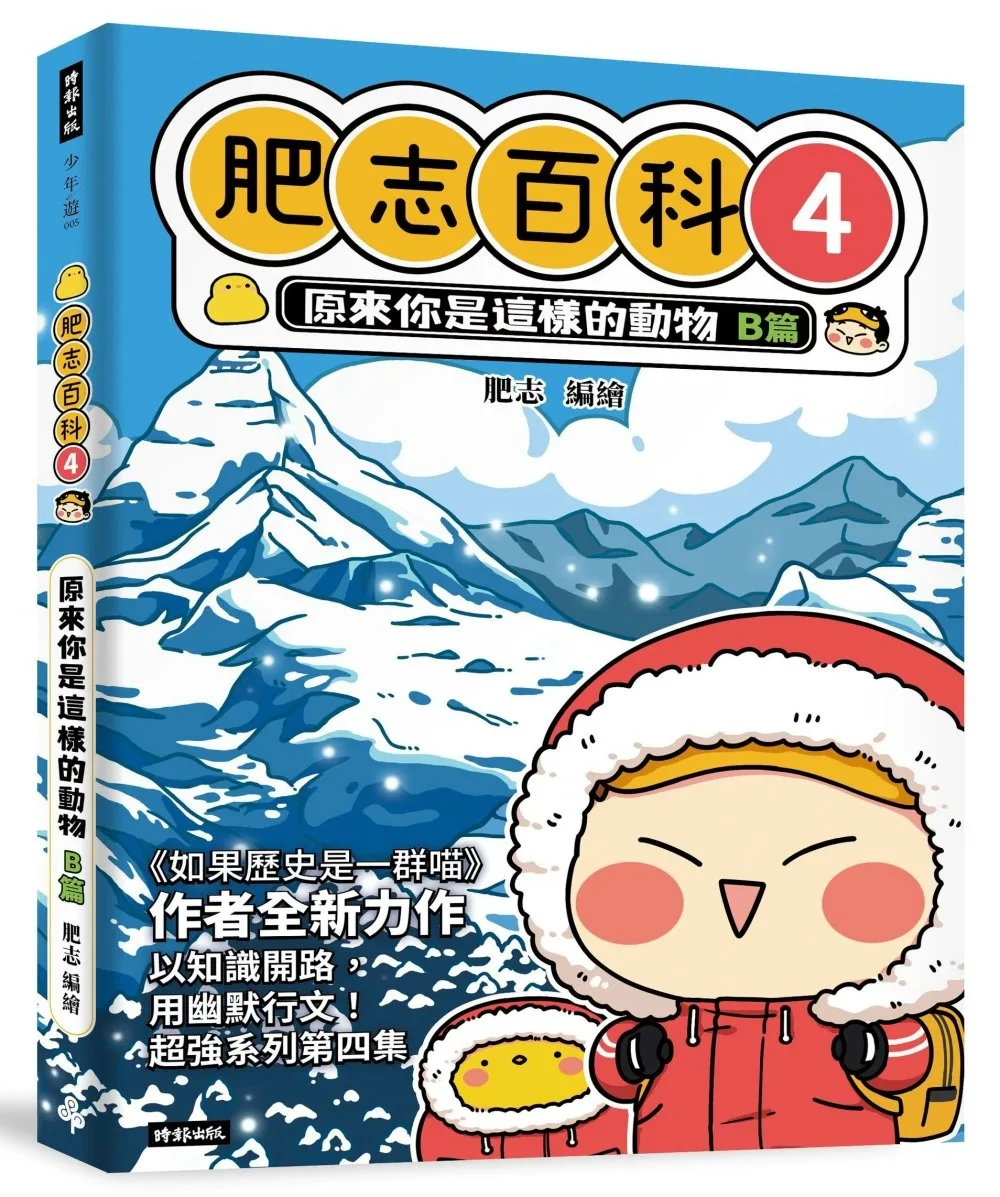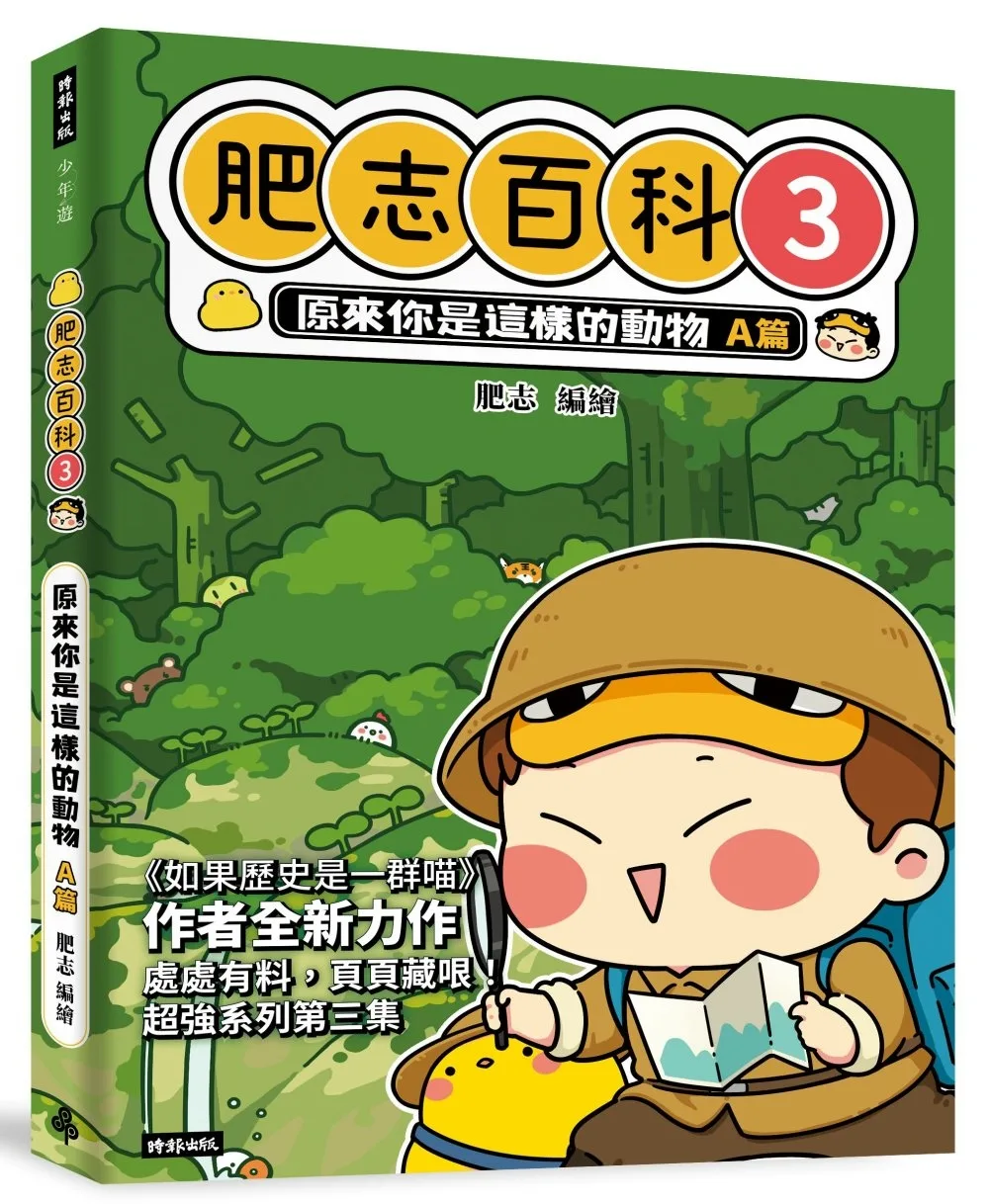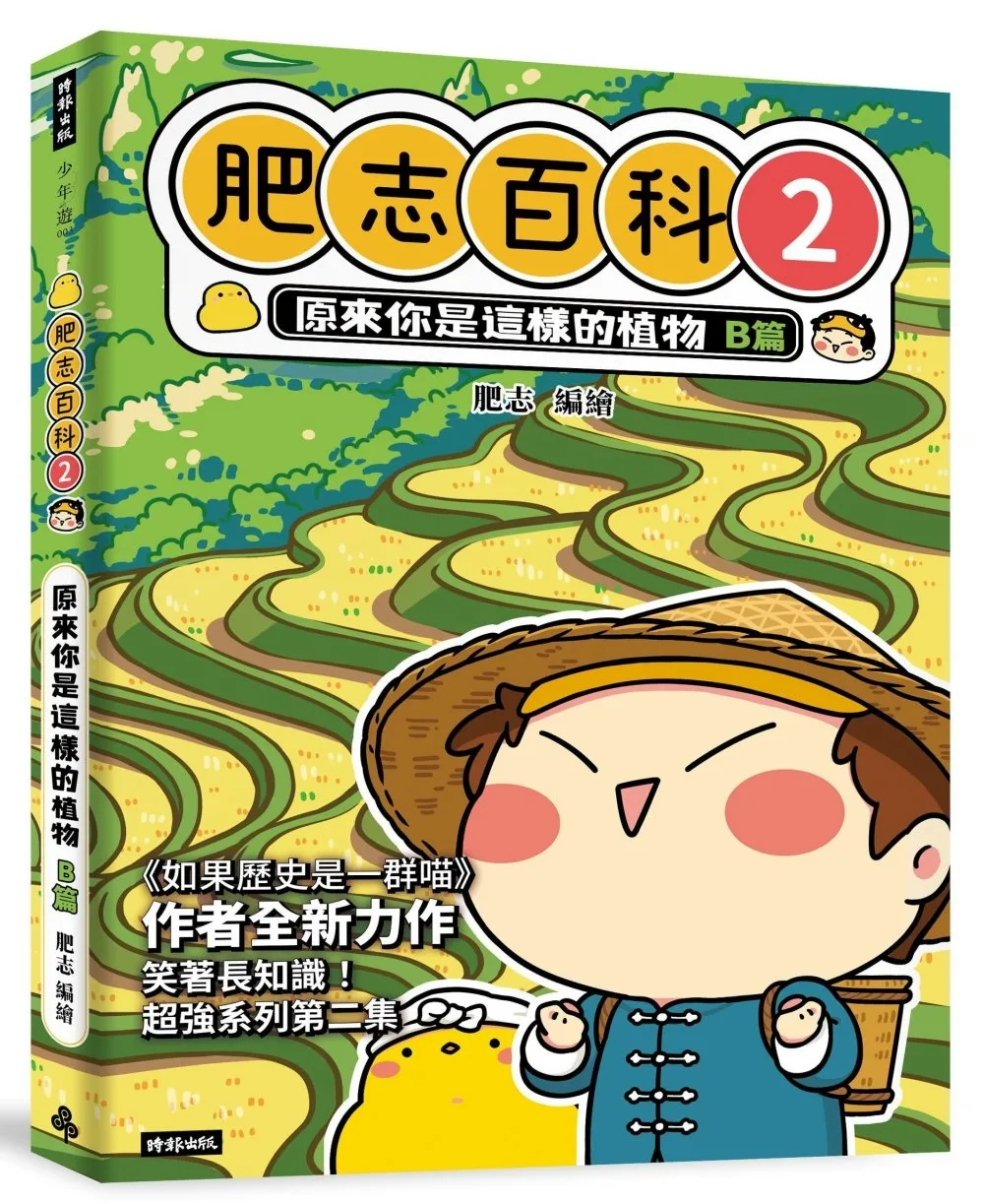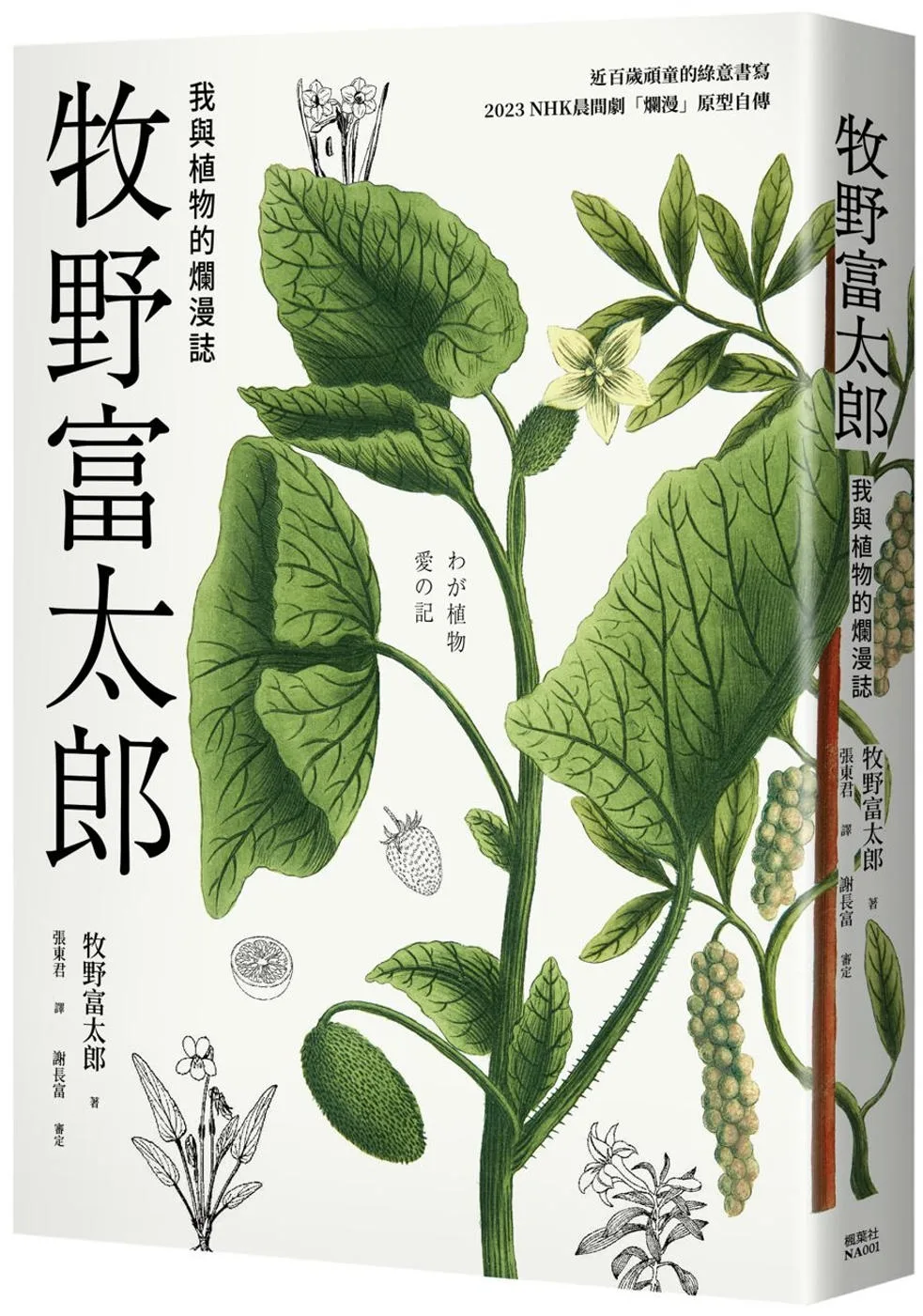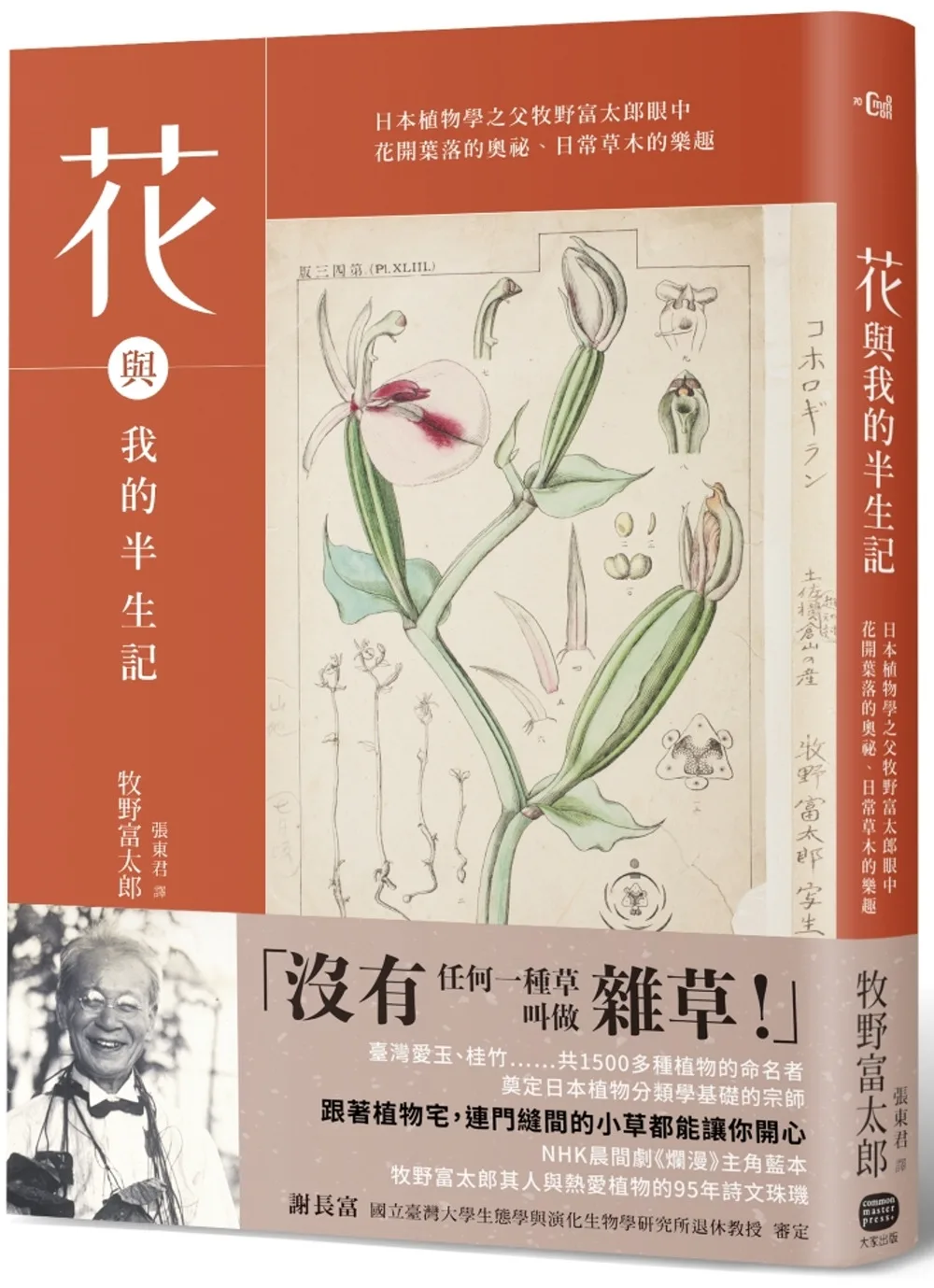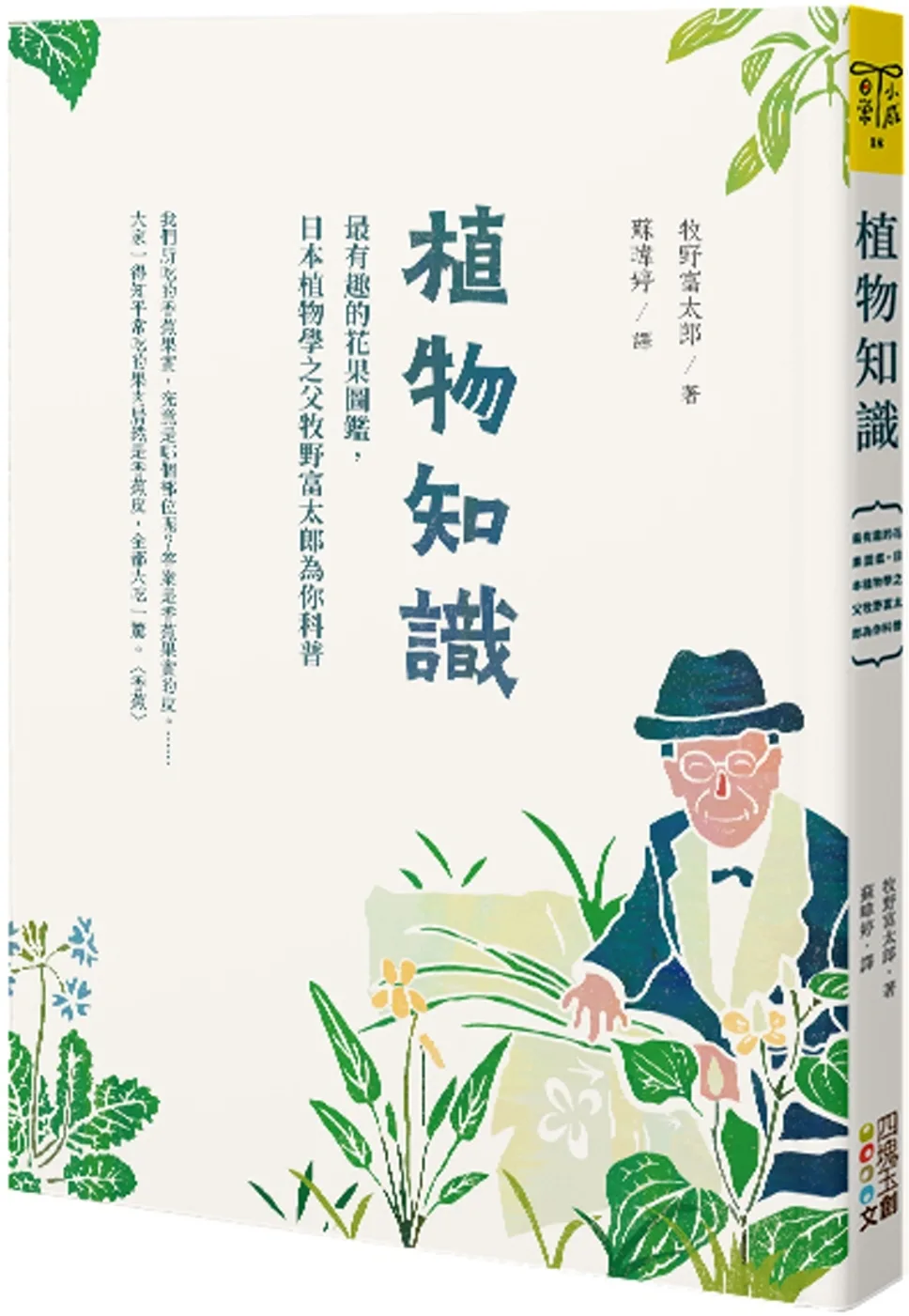私塾學者──牧野富太郎的腳步
梨木香步
?
在野學者
?
與牧野富太郎一起爬山,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主題。
儘管牧野一生之中待在大學研究室的時間並不短,但世人對他「在野學者」的印象卻更為強烈,這大概與他「天生的植物學家」形象有很大的關連。他並非「碰巧會念書就選了植物學」,而是「非植物學不選」。
本書的一大看點,在於牧野描述了童年時期在故鄉佐川山區玩耍的回憶,讀來字裡行間皆彌漫著四國常綠闊葉林帶濃郁的森林氣息。在他後來與登山有關的記述中,最具特色的就是他會將每個場景描述得躍然紙上,讓人彷彿置身他所在的山林。而這都要歸功於他自幼養成的觀察習慣。身為一名作家,牧野在情景描寫上可謂綿綿不絕卻又簡單扼要,而且一定會標明必要資訊。例如有一條溪,就會寫溪水從何而來、流向哪裡;有一座山丘,就會描述它的方位與山勢規模,之後再一一帶過當地的植物名稱。讀者能切身感覺到這裡有這種植物,代表這是在山陰;有另一種植物,表示有些地方濕氣較重,有些地方則較為乾燥;這裡闊葉樹很多,冬天葉子枯萎後,採光一定很好;這裡的泥土長滿高山植物,一定混有碎石(就連乍看與植物無關的〈驚見鬼火〉一文,牧野也以令
人匪夷所思的程度鉅細靡遺描述了地形。文中雖然完全沒有提及磷火,資訊卻多得足以實施科學分析)。即使只是舉出植物名稱,例如這裡有一整片偃松,讀者腦海中也會浮現出栩栩如生的風景──低矮蒼翠的偃松覆蓋著山脊,視野中央到上方是一望無際的晴空──這正是偃松生長的環境。在牧野的筆下,山巒近在眼前。佐川山區相關的散文《狐狸放屁》裡,有一位見多識廣的女傭。這名女傭也非常有趣,「(她)熟知各種草木、菇類的名字,常常令我自嘆不如」,想到農村裡也有能與牧野匹敵、熱愛植物的女子,就令人振奮不已。這可是在野學者(牧野)與在野學者(女傭)難得的交手,真希望牧野能想起她的名字,在文中記錄下來。
根據自傳,牧野富太郎在九、十歲左右於當地學堂接觸了基本科目,拜師伊藤蘭林,修習書法、算術、四書五經。之後,他轉入領主的家塾,也就是後來成為鄉學的「名教館」,在那裡學到了當時最先進的地理、天文和物理知識。目前為止的教學內容皆深得他所好,因此他三天兩頭就往老師那裡跑。然而,十二歲左右,由於當時頒布了新學制,他被迫就讀小學,而小學並不適合他。他早已接觸過進階的學問,當然無法忍受從頭學習基礎知識,於是他輟學了,學歷從此中斷。輟學後,他仍一心求知,進入了位於高知的私塾,學習歐美植物學的知識,度過了充滿活力的少年研究生活。
他表示「我不喜歡(學校),所以輟學了」,至於原因「我目前還不清楚」。也許癥結點在於學校千篇一律的填鴨式教育,忽略了每個學生都有不同的天賦與興趣所在。早在那個時代,這個問題就已經浮出檯面。
?
天真爛漫
?
介紹牧野富太郎的文章常會有以下敘述「年幼時失去雙親,小學中輟後,自修植物學」。這樣的描述固然沒錯,卻像是在介紹於貧困中苦讀的偉人。然而實際上,他出身於富裕的釀酒商,在祖母的悉心呵護下長大。他之所以能從外國訂購書籍和器材,也是歸功於家中能幹的掌櫃不斷在經濟上支持他。他熱愛植物,一心想深入研究草木,遂前往東京大學理學院的植物學研究所,取得了教授的許可並出入研究室。想必教授也因為牧野的博學和對植物的熱情,被迷得暈頭轉向吧。
然而隨著牧野在國際上獲得肯定,教授也從意亂情迷中幡然醒悟(或許是忌妒他,又或許是遭情勢所逼,畢竟研究室的知識財產不能任外人予取予求,也可能兩者兼有)。仔細梳理,會發現東京大學對他的態度反反覆覆,一會兒被迷得七葷八素,一會兒又清醒過來,想方設法趕他出去,然後又有其他人為他著迷──就連祖母和掌櫃,也不惜耗盡萬貫家財,即便破產也要供應他研究費與生活費。不過最辛苦的還是牧野富太郎的妻子壽衛,她在十六歲時嫁給他,過著捉襟見肘的生活,還生下十三個孩子。為了撫育孩子長大並捍衛牧野的研究,她經常獨自與討債人周旋(債主上門時門口會立旗子,牧野總是確定旗子降下後才敢回家)。
為了籌措生活費和研究資金,她甚至經營起茶館,最終因為疲於奔命,五十多歲便過世了(但要說她過得不幸福嗎?這點只有她自己才能下定論。)牧野自小對植物學的熱情,幾乎迷倒了以祖母為代表的所有親朋好友。或許是他探究植物學的熱情,以及勤奮好學的態度,讓大家發現自己心中也有類似的單純夢想,進而激起了保護他的欲望吧。
事實上,牧野富太郎的「單純」還有另一個層面──幼稚,這麼講可能會有語病,稱為「天真爛漫」更恰當。牧野在樂不可支的時候,經常隨口吟出充滿赤子之心的詩詞,例如本書〈可口的食用菌──馬糞蕈〉中的大量俳句便令人拍案叫絕,彷彿看到了國小男生因為「大便」一詞而興奮得手舞足蹈。不光是這一篇,當讀者看到類似的有趣篇章時,肯定都會因為他活潑的筆觸而會心一笑。
此外,他雖然在公眾場合信誓旦旦地說自己對地位、聲譽和功名「沒有野心」,但在〈因廁得福〉這一篇中,卻又像個孩子不斷爭辯自己比大久保三郎早了六、七年採集到羅漢柏羊栖菜菌。其實他並不是在找碴,而是他的個性就是不吐不快。
他還說希望再遇到一次大地震,想看富士山爆發。不僅如此,他還企圖把火山一分為二,簡直是口無遮攔。然而,這分天真爛漫正是他研究的原動力,這點毋庸置疑。從〈吊石蜘蛛〉可得知,他即使在專業領域之外,也依舊「明察秋毫」,而這正是他的生活之道。
大概是因為他有著一顆閃閃發亮、難得一見、教人無法招架的「天真爛漫」,所以在他陷入人生困境之時,總會有男男女女對他伸出援手吧。
?
私塾學者──牧野的真本領
?
在〈《草木圖說》的澤薊與真薊〉一篇中,有這樣的描述:「圖解中收錄的澤薊圖與一旁的真薊圖兩者放反了,至今卻從未有人發現。」以及「也許圖片放錯只是作者偶然搞錯了順序,卻導致我們現在修正時,得將過去植物界慣用的澤薊與真薊的和名顛倒過來。」雖然我孤陋寡聞,不過據我所知,現在這兩個名字依舊沒有「顛倒過來」。Cirsium sieboldii 人稱真薊,但這所謂的「真薊」偏偏生長在濕地和沼澤。
以孩子單純的眼光來看,這就如同「國王的新衣」,稱之為「澤薊」顯然更恰當。牧野的追根究柢還不只於此。「近江國伊吹山腳下的村民」自古就會摘真薊來食用,對真薊的形狀肯定瞭若指掌,問題在於這個「真薊」到底是澤薊還是真薊呢?照理說只要不是新品種,自古流傳的稱呼就應該是植物的本名才對。於是,牧野請住在京都的朋友前往伊吹山腳,總算取得了那種植物,發現它的葉片寬大又柔軟,於是「心滿意足,高興得不得了」(過去人們口中的「真薊」葉子狹窄而多刺,並不適合食用。換言之,這種植物正是牧野當時堅稱「正確」的澤薊)。此番謎團儼然已在他心中拍板定案,然而牧野去世以後,真薊卻從昭和年間首度出版的《牧野新日本植物圖鑑》之中消失了,只在「澤薊」的項目中驚鴻一瞥,與水薊、煙管薊並列為澤薊的別名。都已經詳盡闡述澤薊和真薊的區別了,牧野啊,你這又是何苦呢?這代表了一件事──他在獲得新知後,可以毫不猶豫推翻自己從前的說法。得出此番結論,想必過程也是一波三折吧。
他在「澤薊」項目的結尾寫道:「除了本書摘錄的物種,日本還有約七十種薊類(Cirsium),彼此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足見他下過多少苦功。如此真誠、毫不矯飾的行文,或許正是源自江戶時代末期盛行於日本各地、他所耳濡目染的私塾風範吧。
大學學術圈的人叫做「大學學者」,那麼當然也有「私塾學者」,這群人百花齊放,個性又「偏執」,卻自成一個完整的宇宙。每間私塾都充分展現了創辦者各自的心性,可謂與公家學校截然不同。不拘泥定論、不失赤子之心,不顧形象也要一解心中的疑問──這正是私塾學者牧野的真本領,他是在野最閃亮的一顆星。
想與牧野一同爬山涉水的人,絕對不只有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