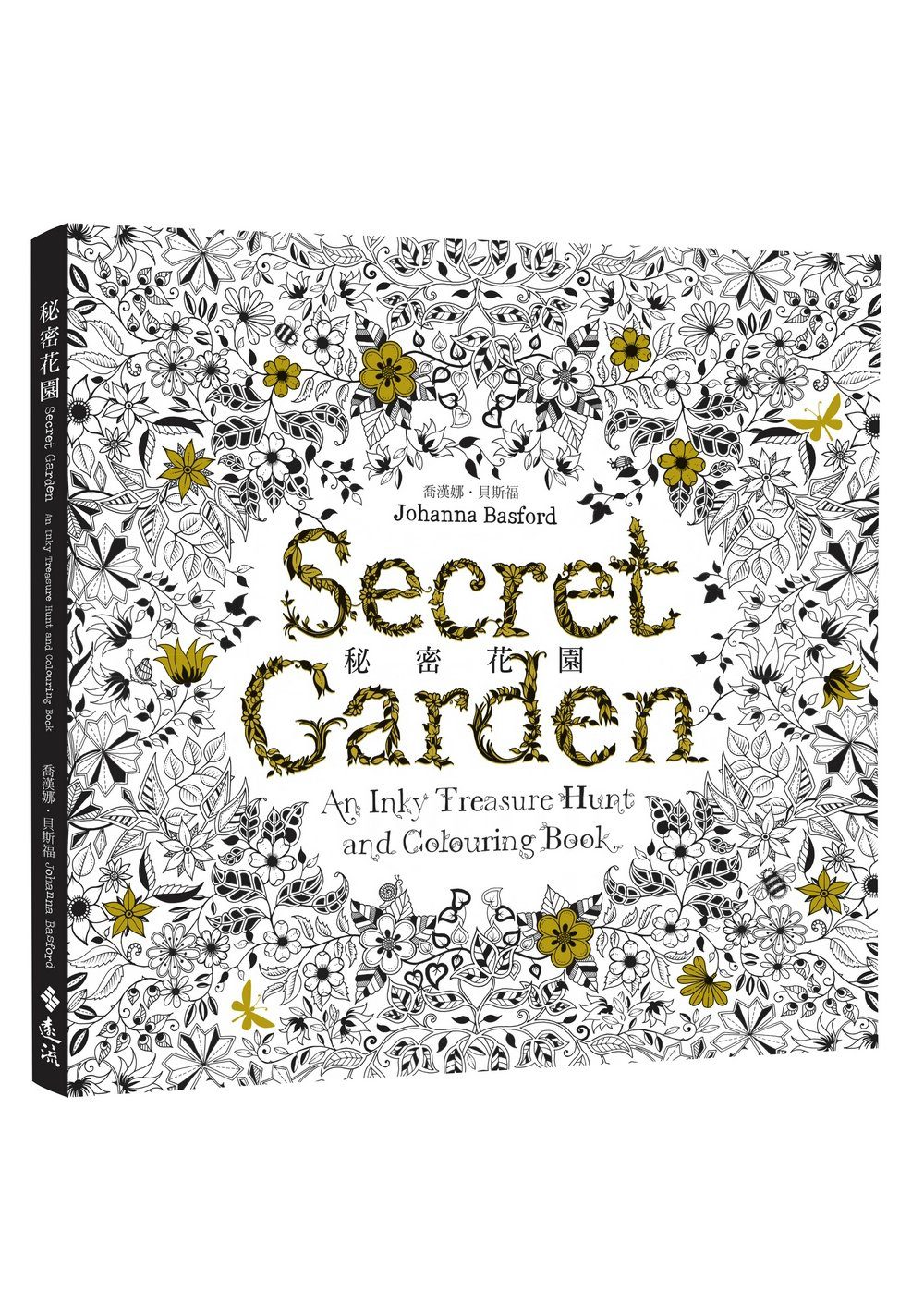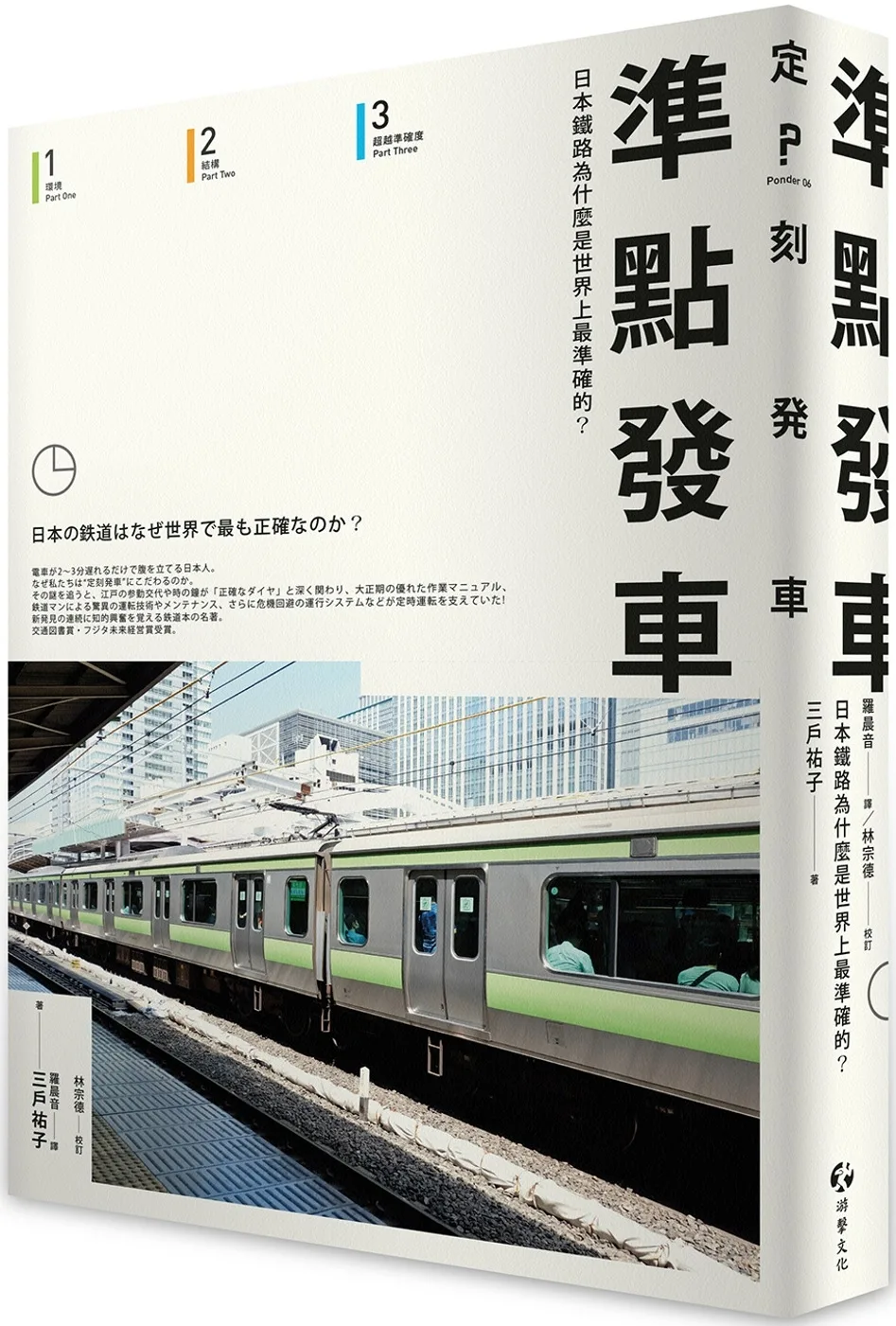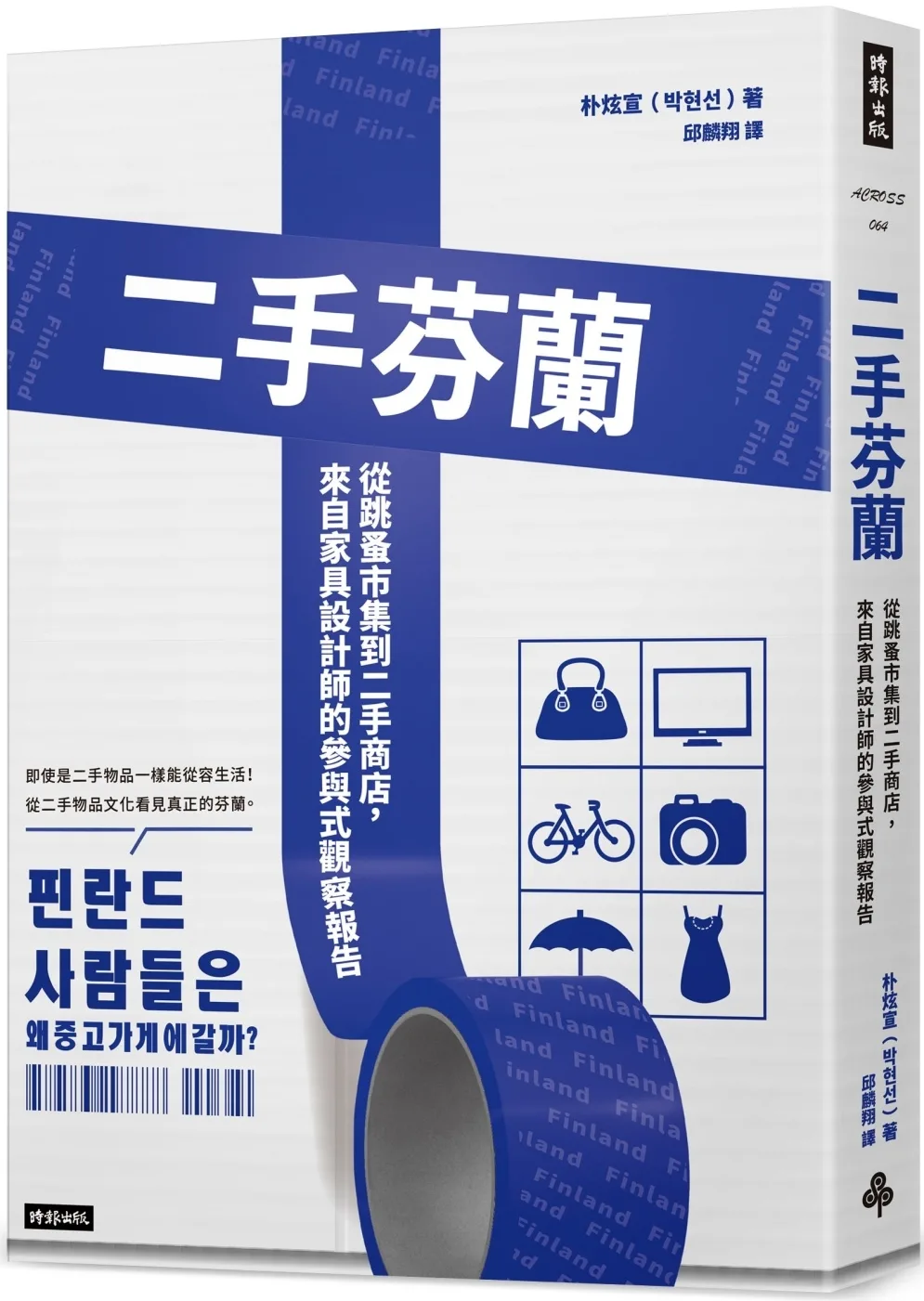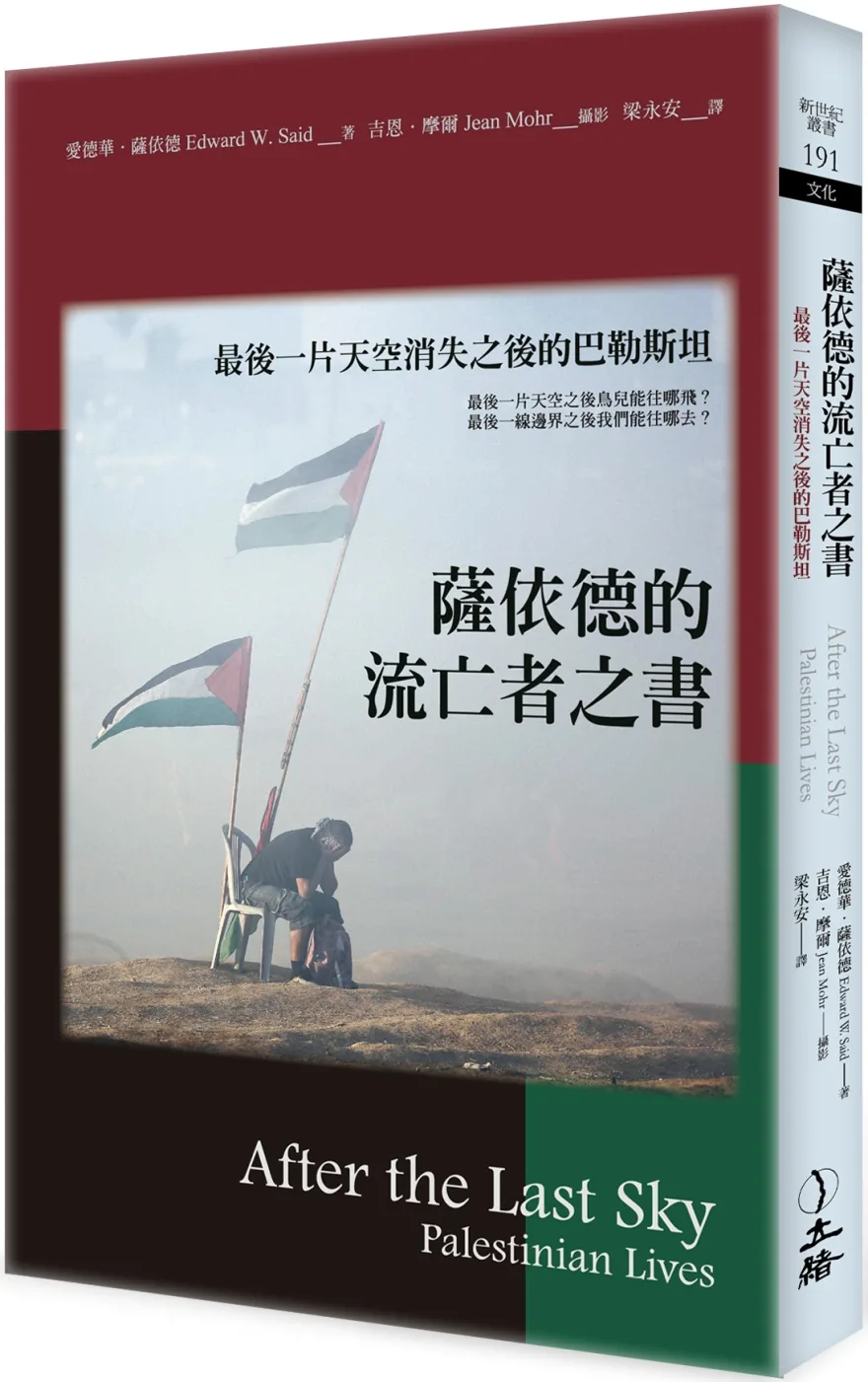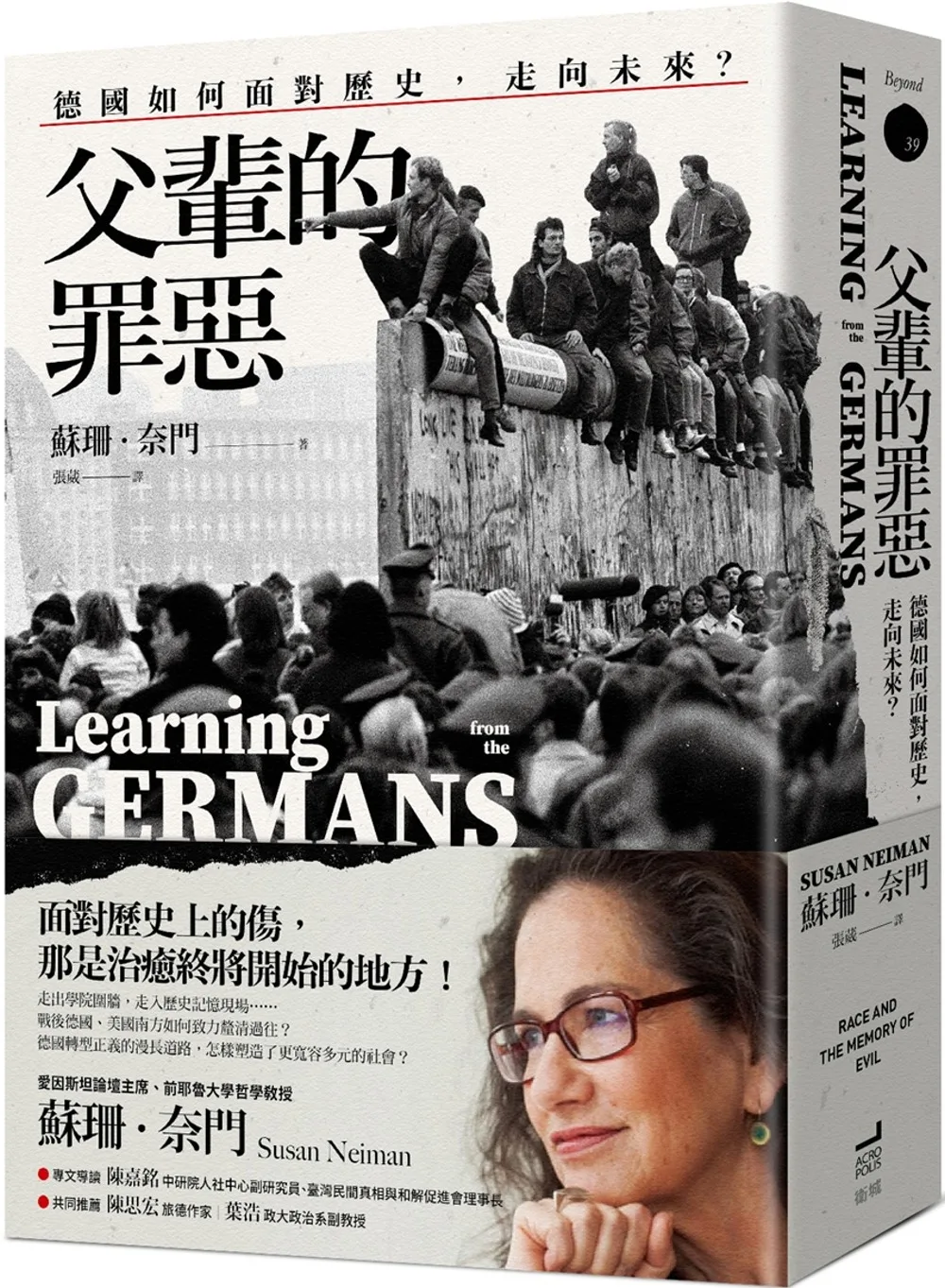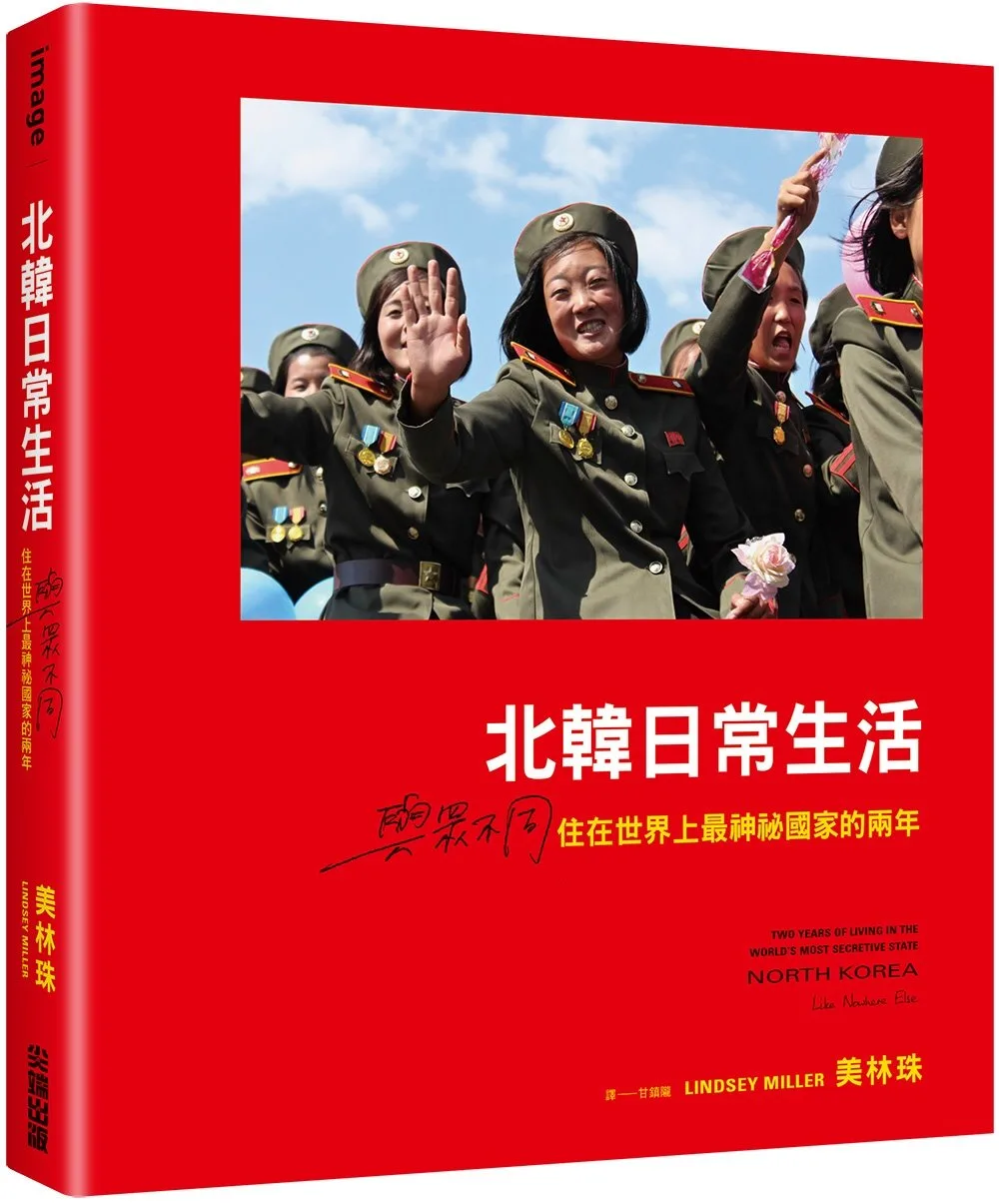「我總是幻想著與哪個爺爺奶奶不期而遇,被帶回家,
擠在家徒四壁的小屋裡,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分享一切。」
───── 宛如台灣版《憂鬱的熱帶》─────
走過安地斯、踏越亞馬遜,不是探險,是探心。
擠在家徒四壁的小屋裡,一起生活、一起工作,分享一切。」
───── 宛如台灣版《憂鬱的熱帶》─────
走過安地斯、踏越亞馬遜,不是探險,是探心。
▎「我幻想自己像一棵植物,長出根系、抓住大地,以一顆赤心。」
▎一趟融入南美山林的無計畫旅行,現代世界遺忘的質樸與純真。
「爺爺在石磨上敲打著凍乾,奶奶到倉庫拿了幾隻羊腳丟進鍋裡,
那裡頭就像濃縮的高原:羊駝、馬鈴薯凍乾;沙土、湖水、寒氣與陽光……」
2023年,楊理博與伴侶帶著一只後背包,開啟一段長達八個月的南美之旅。他們不觀光,未訂旅宿與回程機票,一路上跟當地偶遇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一起回家,高山上挖馬鈴薯、做凍乾,睡在牧草床上;雨林裡抓魚、釀樹薯酒、採草藥……
旅途尾聲,兩人參與一場十天的靈境追尋儀式,求道者帶著對生命的探問上山,期間禁食、禁水、禁語;守護者留在山下為他吃、為他喝,也為他祈福祝禱──這不是宗教,而是「成為自己」的古老練習。
楊理博說:「我的身體,已烙著深深的土地與時間的印記。」這趟不帶時間表前進的旅行,是一顆純淨的心正試圖看見自己、看見土地,真真實實地活在世界裡。
★專文作序
洪廣冀|台灣大學地理系副教授
感動推薦
阿潑|文字工作者
雪羊|山岳作家
郭熊 郭彥仁|作家
詹宏志|作家
詹偉雄|文化評論人
鄭漢文|東台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謝旺霖|作家
鴻鴻|詩人
(依姓氏筆畫序排列)
各界好評
●阿潑(文字工作者)──
楊理博不僅以其低調、開闊的身段融入安地斯山脈、亞馬遜流域的生活中,從而展開有細節、有溫度、有文化厚度的書寫,也從中提煉出極為動人的哲思。文字既有對當地文化和居民的尊重與理解,也帶著對土地自然的深情。因此,這雖是一本以旅行為題的書,但幾乎不見「人的旅行」,反而是南美洲的歷史底蘊,因楊理博的筆,向我們而來。讀來很是深沉、溫暖。
●雪羊(山岳作家)──
理博可說是一個奇人,他拋開台大電機系的主流頂尖光環,歷經旅行的漂泊,最後落腳台東布農部落,全心學習布農族與土地連結的生活方式,還善於書寫。
聽到他要將在南美屋脊安地斯山脈與地球之肺亞馬遜雨林中生活八個月的記憶轉化為文字,我非常期待。因為那將是一個深深扎根台灣山林土地的靈魂,與地球對面山岳文化的珍貴交織;讓我們能透過有著布農之心的台灣人之眼,探究遙遠、神祕而美麗的安地斯山脈,挖掘深藏聖山之上的靈性日常。
●郭熊 郭彥仁(作家)──
無論是台灣的山或海,亦或南美洲亞馬遜雨林的任何一處,只要用心觀察、慢慢體會,即可找到與自然母親的共同語言,那我們都是家人。
●鄭漢文(東台灣研究會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這是一本行走的民族誌,理博以參與者的謙卑,見證了文化韌性持續在文明的裂縫中萌發新芽;但其同時也給出一聲警醒:那種聽得見土地的歌聲,將土地視為生命一體的靈性視野,正是當代文明最需的生活哲學。
●鴻鴻(詩人)──
瑪黛茶和死藤水,馬鈴薯凍乾和木薯酒……楊理博的書寫帶著亞馬遜的溼度與安地斯山的味覺,令人感官全開,一起進入薩滿之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