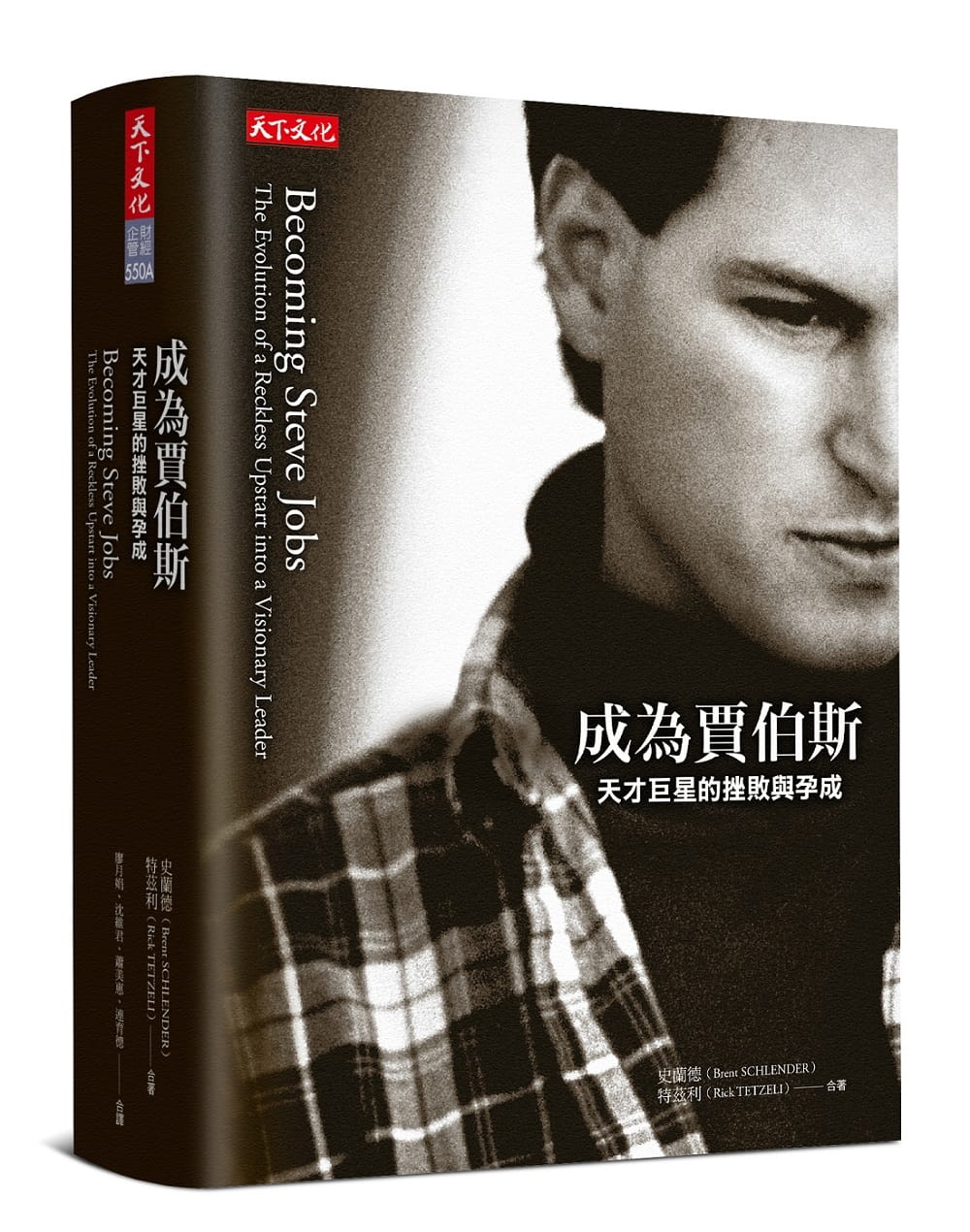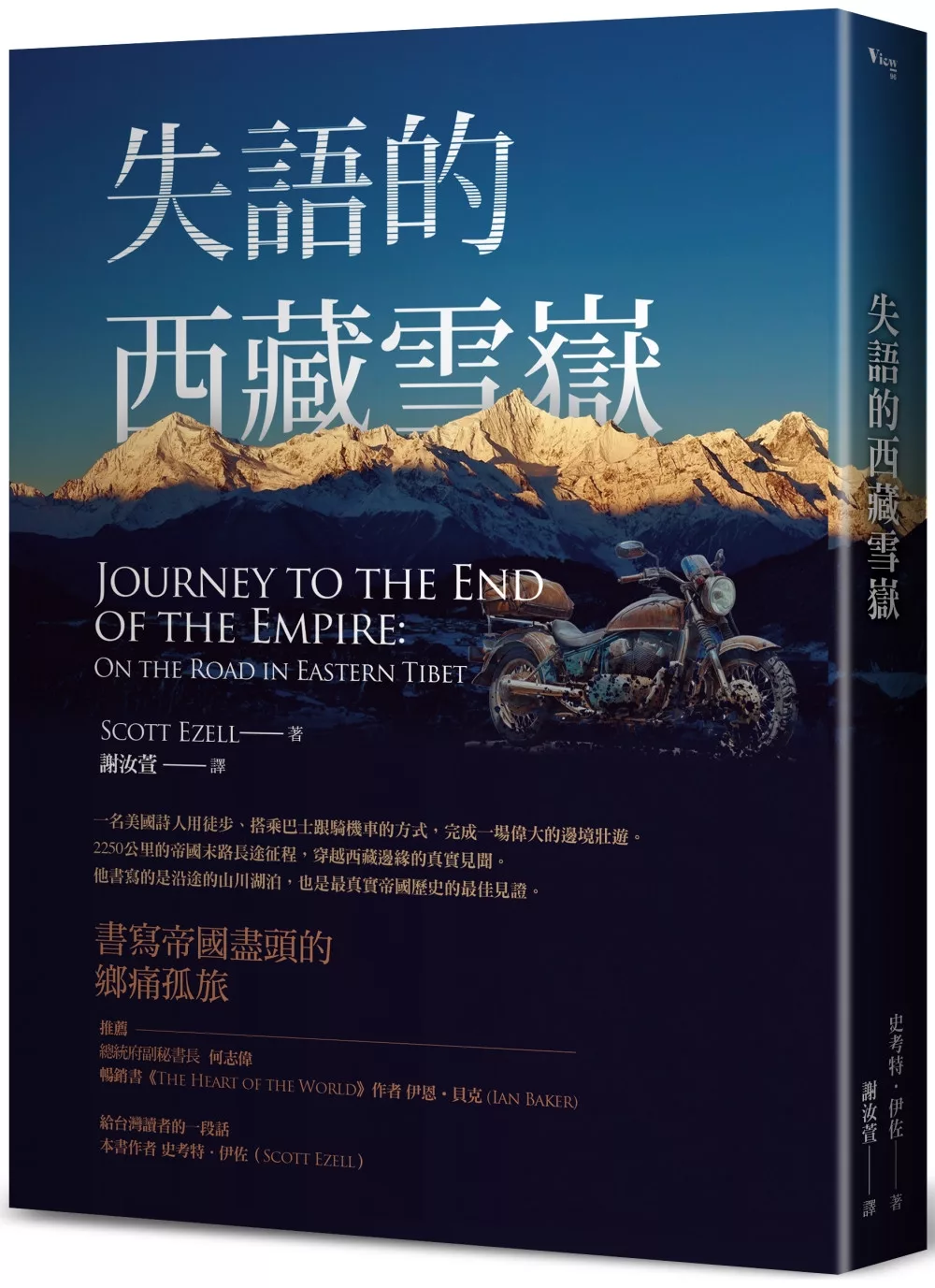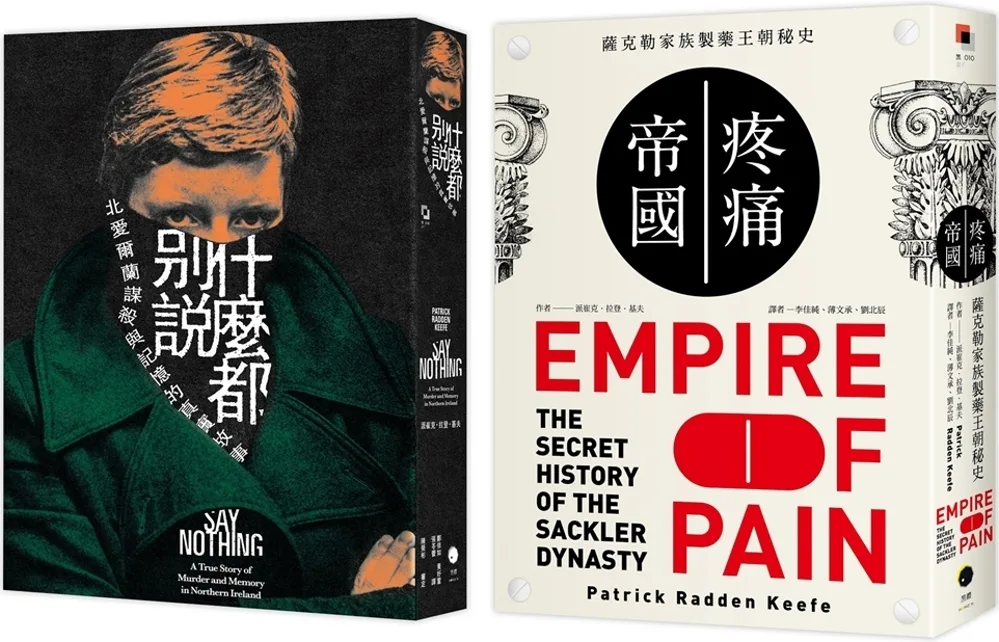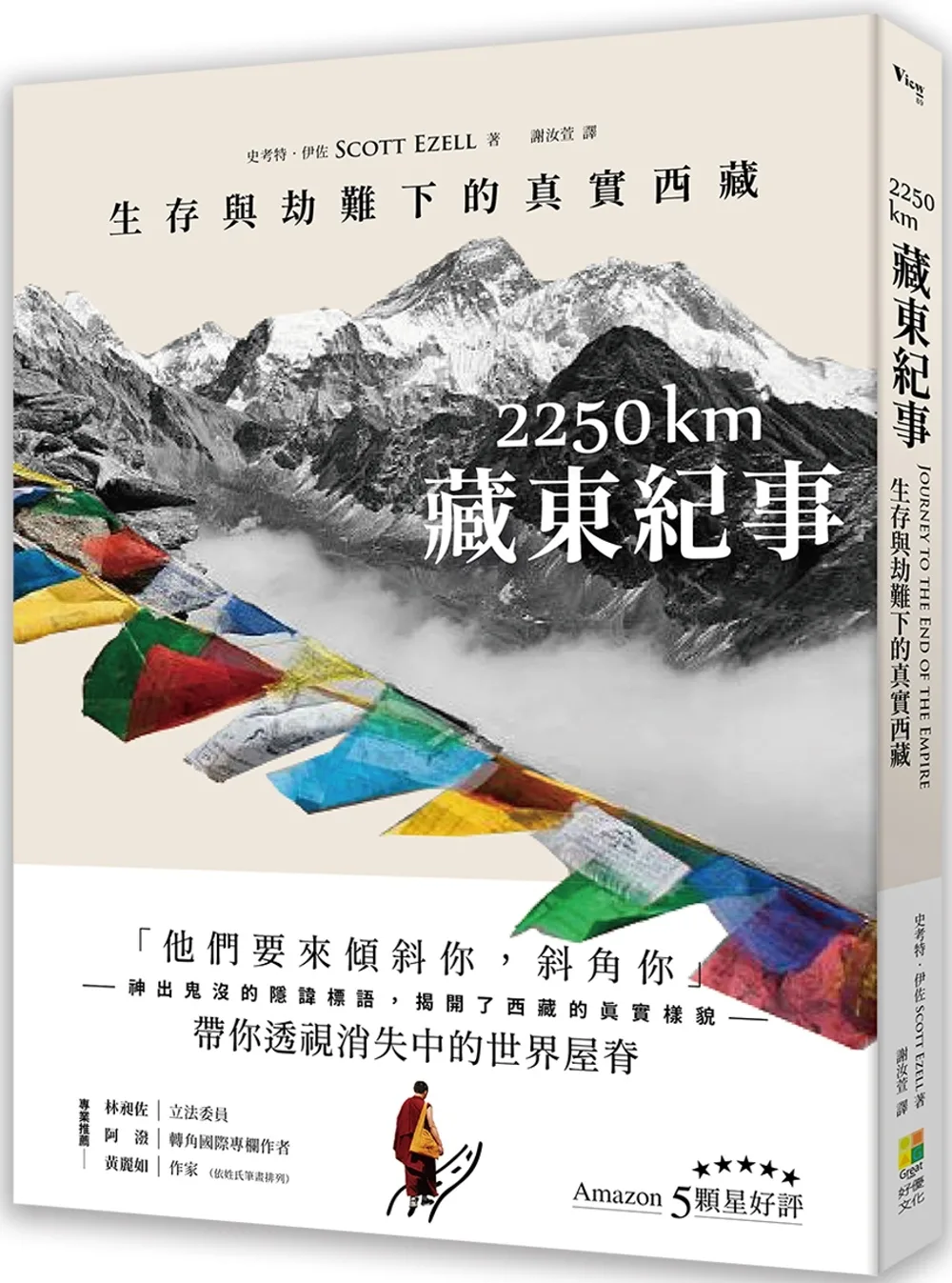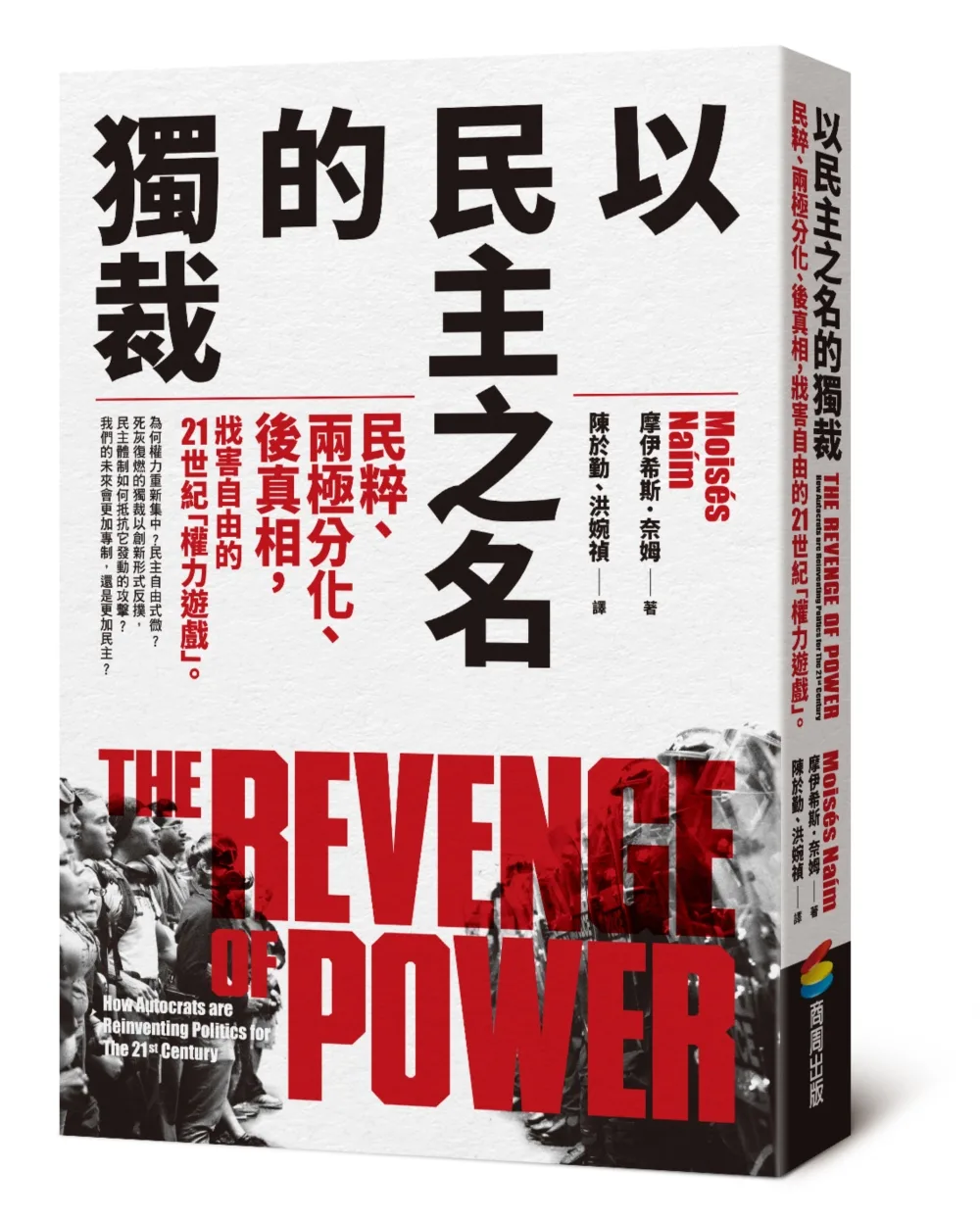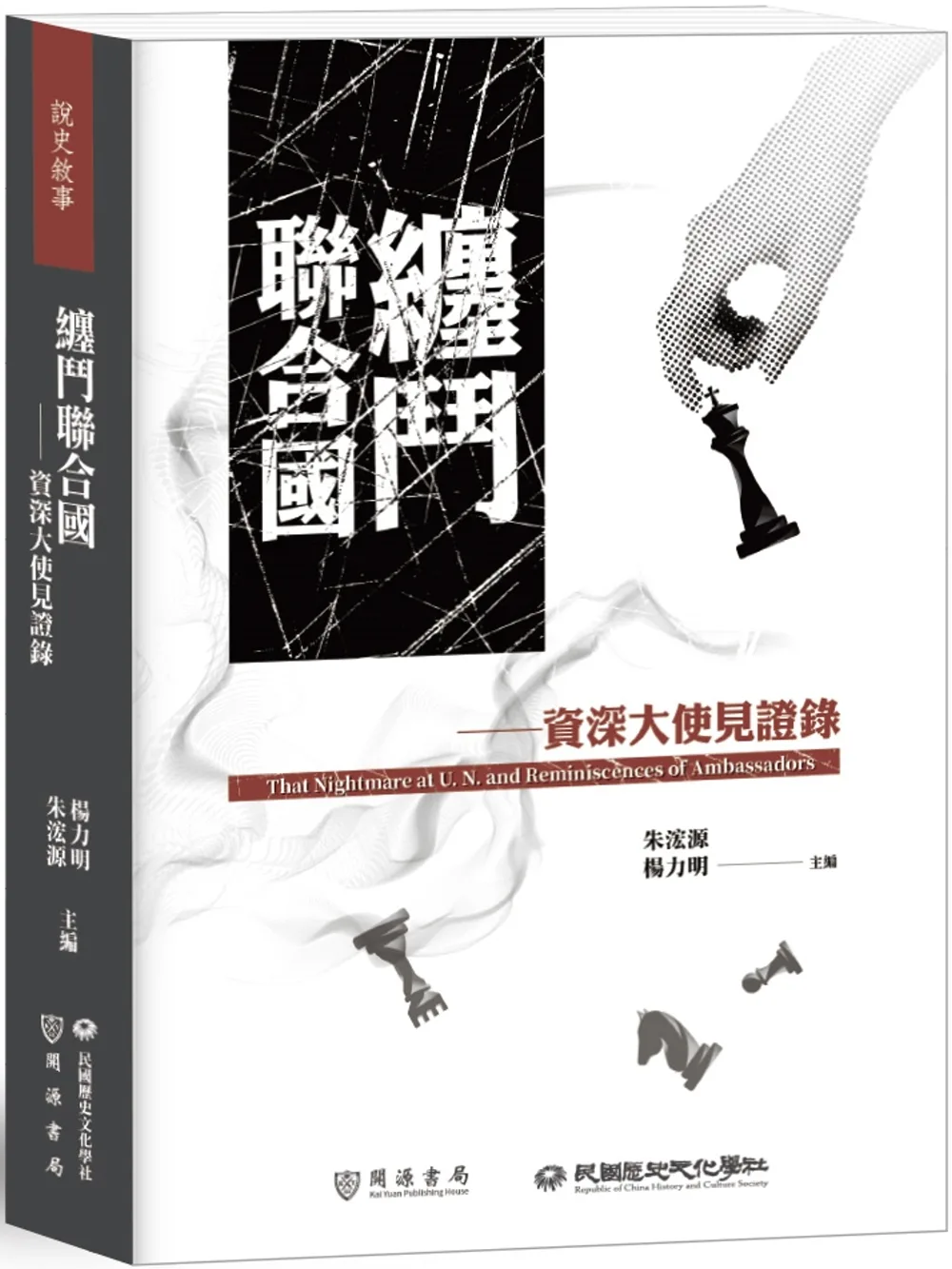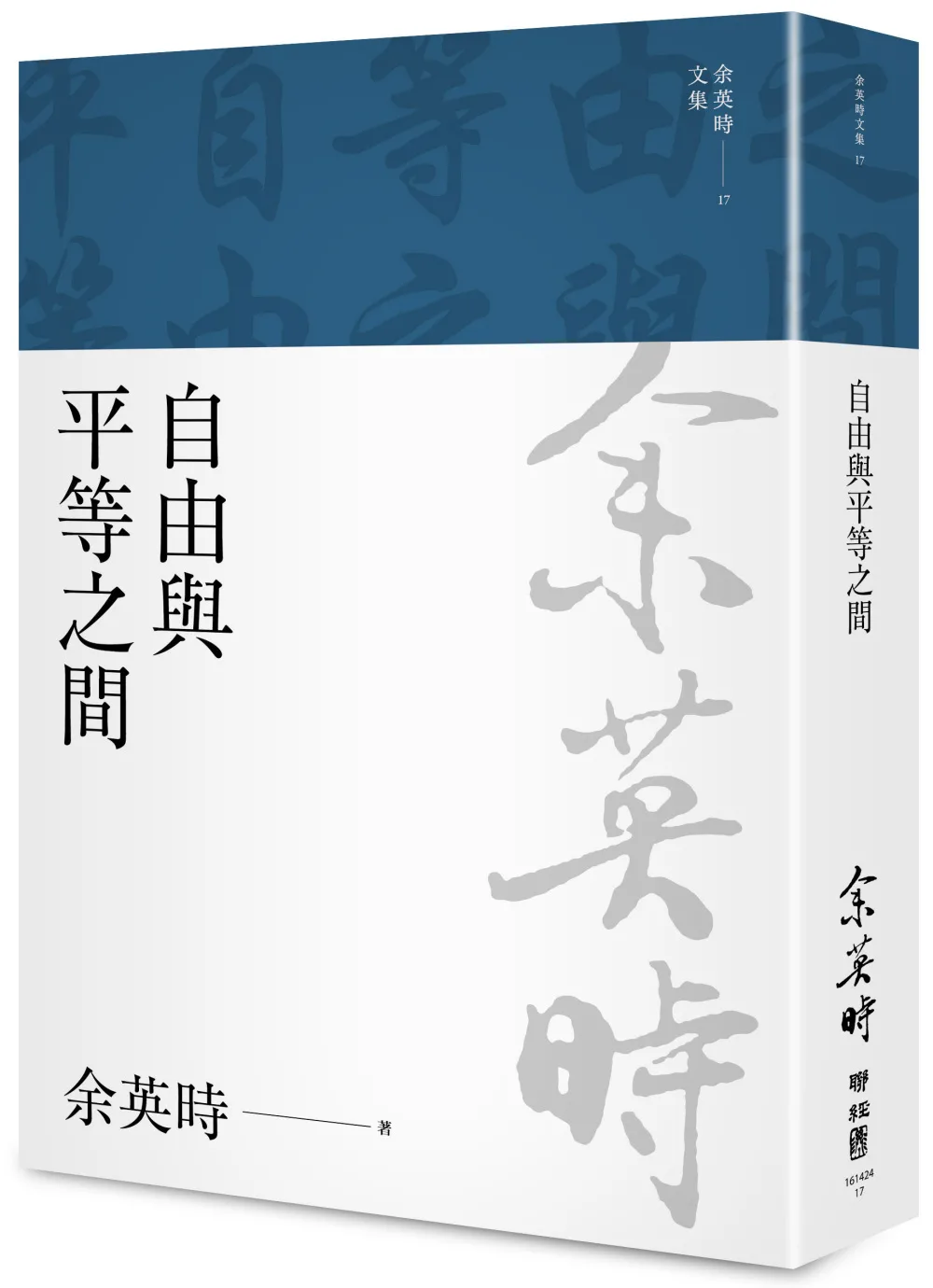作者序
給台灣讀者的一封信
某種程度上,我在西藏的旅程,其實是從台灣開始的。
一九九二年,我為了學習中文來到台灣。後來在二○○二到二○○四年間,我住在台東都蘭北方的「意識部落」,那是一個原住民藝術家社群。當時的太平洋海岸還相當偏遠,沒有今天的衝浪民宿、文創小店或熱氣球觀光。那裡的原住民長者,仍完整地保存著他們的語言、信仰與歌聲,那是一種延續了數千年的生命形式,真實而完整地存在於他們自身之中。
我在都蘭結識的阿美族、卑南族與排灣族藝術家朋友,多數在三十歲上下。他們生活在一種「邊界」之間,一邊是深植於土地與傳統的族群身份,一邊是現實中由中華民國政經體制所主導的生活結構。對他們而言,創作與生活的一大核心,是回溯記憶、重拾族語,並在現代國家體制下重新建構屬於當代的原住民身份。
當我與他們一同生活時,也開始思考:這樣的身份與土地的議題,對我自己、對整個世界意味著什麼?二○○四年離開都蘭之後,我決定往更遙遠、更高處去,前往東藏那些偏遠的地方旅行。
在西藏,我看見山脈、草原、社群與信仰之間的一種合一,彷彿那遼闊的高地本身就是「佛性」的具象呈現,同時存在於天地與人心之中。無論走到哪裡,人們都以真誠喜悅的笑容迎接我,像是等待多年的貴客。他們慷慨地遞上手中的東西:核桃、梨子、麵餅,或邀我進家裡喝酥油茶。那片土地似乎閃著光,恆久不滅,彷彿什麼都不會改變。
但當然,世事終究改變。
接下來十五年間,我多次重返西藏,目睹了環境與文化的破壞。東藏地區逐漸被軍事化與嚴密監控,山河被開挖、鋪上水泥,原本的村落被迫遷入安置區。這些景象讓我聯想到歷史上殖民過程的重演,如美洲原住民的滅族,日本與中華民國對台灣的統治,同樣的模式也出現在我後來旅居的寮國、墨西哥等地。水壩讓河流死亡,森林被清空以種植橡膠與棕櫚油。像宏都拉斯的貝塔.卡塞雷斯與墨西哥的伊西迪羅.巴爾德內格羅,這兩位「環保界諾貝爾獎」高曼獎得主都因為帶領族人捍衛土地而遭暗殺。
如今,西藏的生態浩劫與極權壓迫仍在持續,也已不再只是中國內部的問題。吞噬西藏的「帝國」不僅是國家政權,也包括跨國科技公司、全球對礦產的需求,以及那些透過剝削中國勞動市場而牟利的西方企業。它們輸出大型機械與水壩設備,間接促成西藏的工業化開發與土地掠奪。西藏人被迫離開家園的悲劇,其實與全球其他因戰爭、開發而流離失所的人民息息相關,自二○○二年以來,美國的「反恐戰爭」就已使超過三千八百萬人被迫遷離。
「自由的目的,是為他人創造自由。」
這是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在獄中二十七年間寫下的一句話。
沒有任何個人能單獨讓西藏重獲自主,但西藏人對土地的神聖感、他們在苦難與壓迫中仍展現的慷慨、尊嚴與喜悅,本身就是一種在束縛中的自由表現。
雖然每個人都受權力體系所制約,但有些人仍擁有相對更大的言論與行動空間。我在台東的意識部落朋友,至今仍持續為部落主權與環境保育發聲——這在中國是不可能的。從二○一一年起,他們以藝術行動與現地抗爭的方式,對抗位於台東市與都蘭之間、違法興建且破壞生態的美麗灣渡假村工程。經過兩年的努力與全台聲援,一連串的訴訟最終讓該度假村無法開幕。
相較之下,西藏人只要稍有異議,就可能被捕入獄。許多人為了讓世界聽見文化滅絕的真相,不惜以最極端的方式抗議——自二○○九年至今,已有近兩百位藏傳佛教僧侶自焚,以此表達對土地與文化被毀滅的抗議。正如越戰期間,越南僧侶以自焚抗議美軍佔領與暴力一般。
二○二五年,達賴喇嘛迎來九十歲生日,同時也是「西藏自治區」成立六十週年。作為地球的「第三極」,西藏擁有僅次於南北極的冰川儲水量,並孕育十條大河,供應超過二十億人口的用水。中國對西藏的佔領,並非當代世界的特例,但由於其生態與政治的重要性,西藏已成為全球被佔領與被邊緣化民族的象徵。這些重要的時間節點,提醒我們回顧歷史、思索未來,不僅是為了西藏,也是為了所有被壓迫的族群。
我希望《失語的西藏雪嶽》能成為一部獻給西藏的禮讚,也是一種守護。
我衷心感謝好優文化在這個關鍵時刻推出中文版。
同時,我也榮幸地宣布,本書推出的印度版本,讓我有機會於二○二六年前往達蘭薩拉,達賴喇嘛與流亡藏人政府的所在地,親自將這本書帶回西藏社群。
能夠在這樣的循環中回到原點,對我而言,是一種深深的榮幸與回饋,獻給那些在西藏各地慷慨接納我的人們。
二○二五年十一月
SE 墨西哥.恰帕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