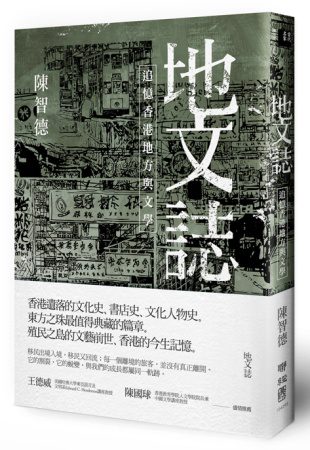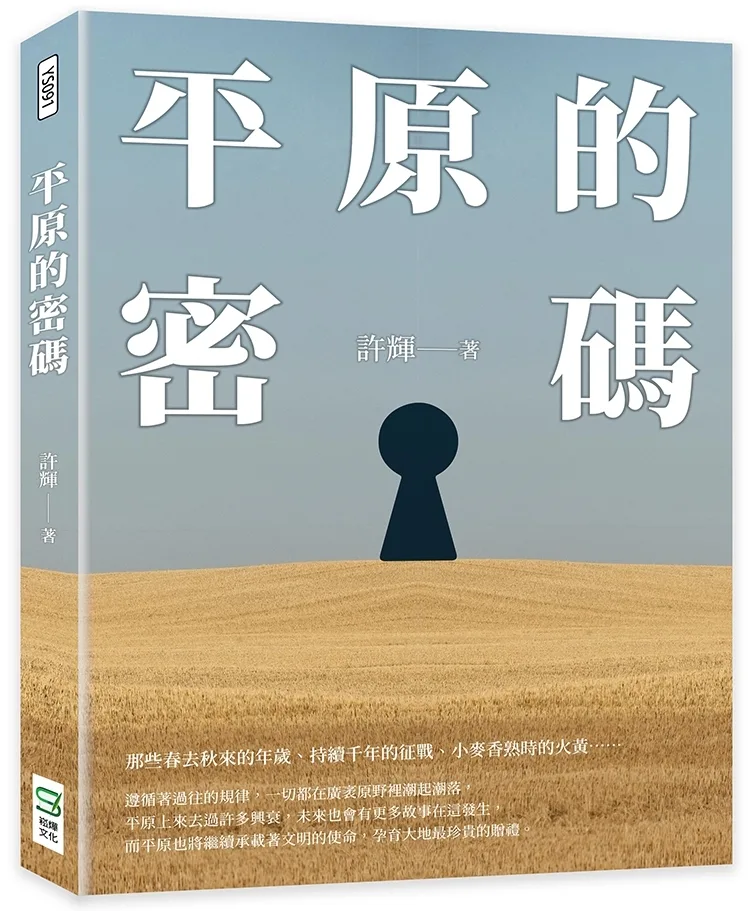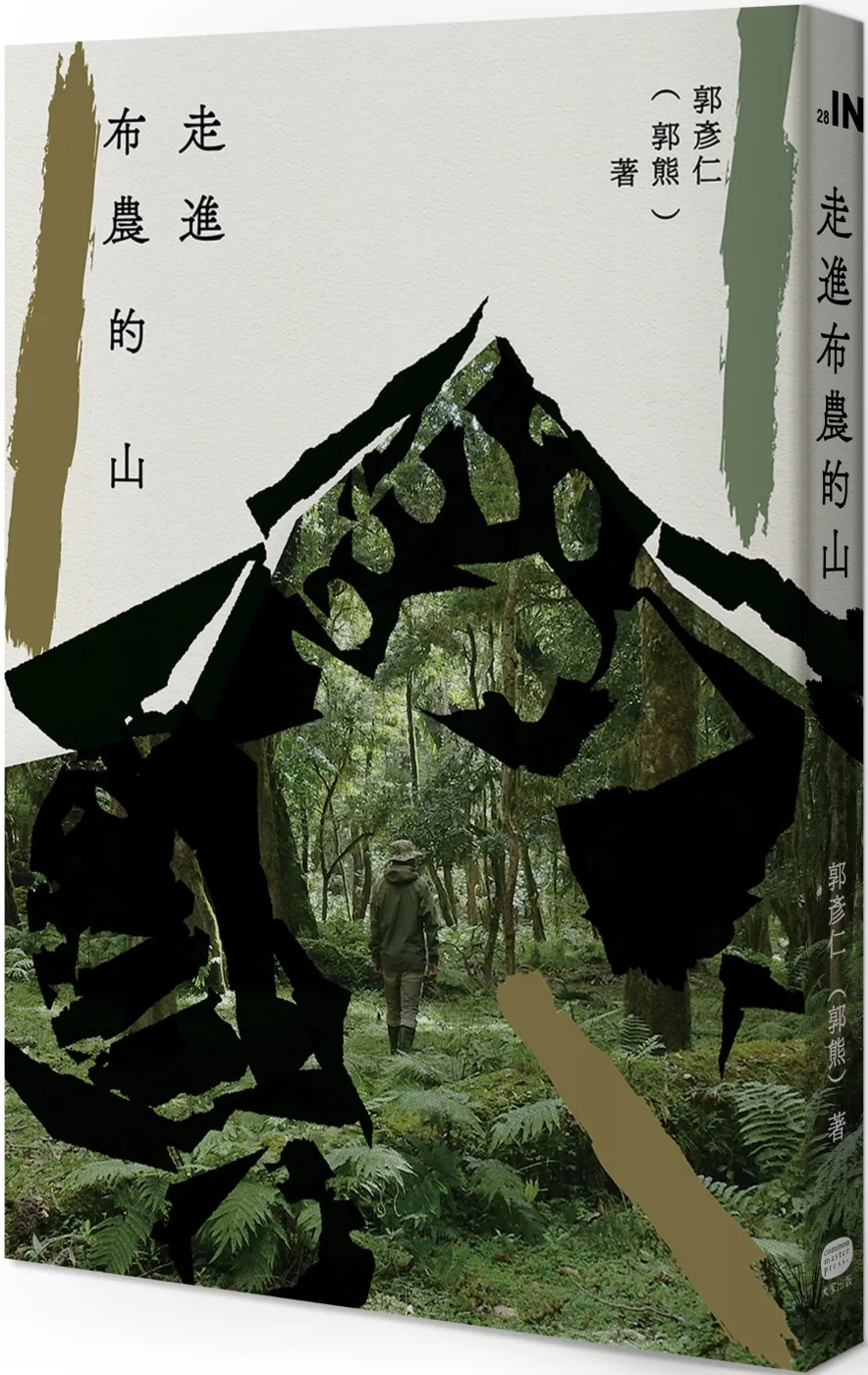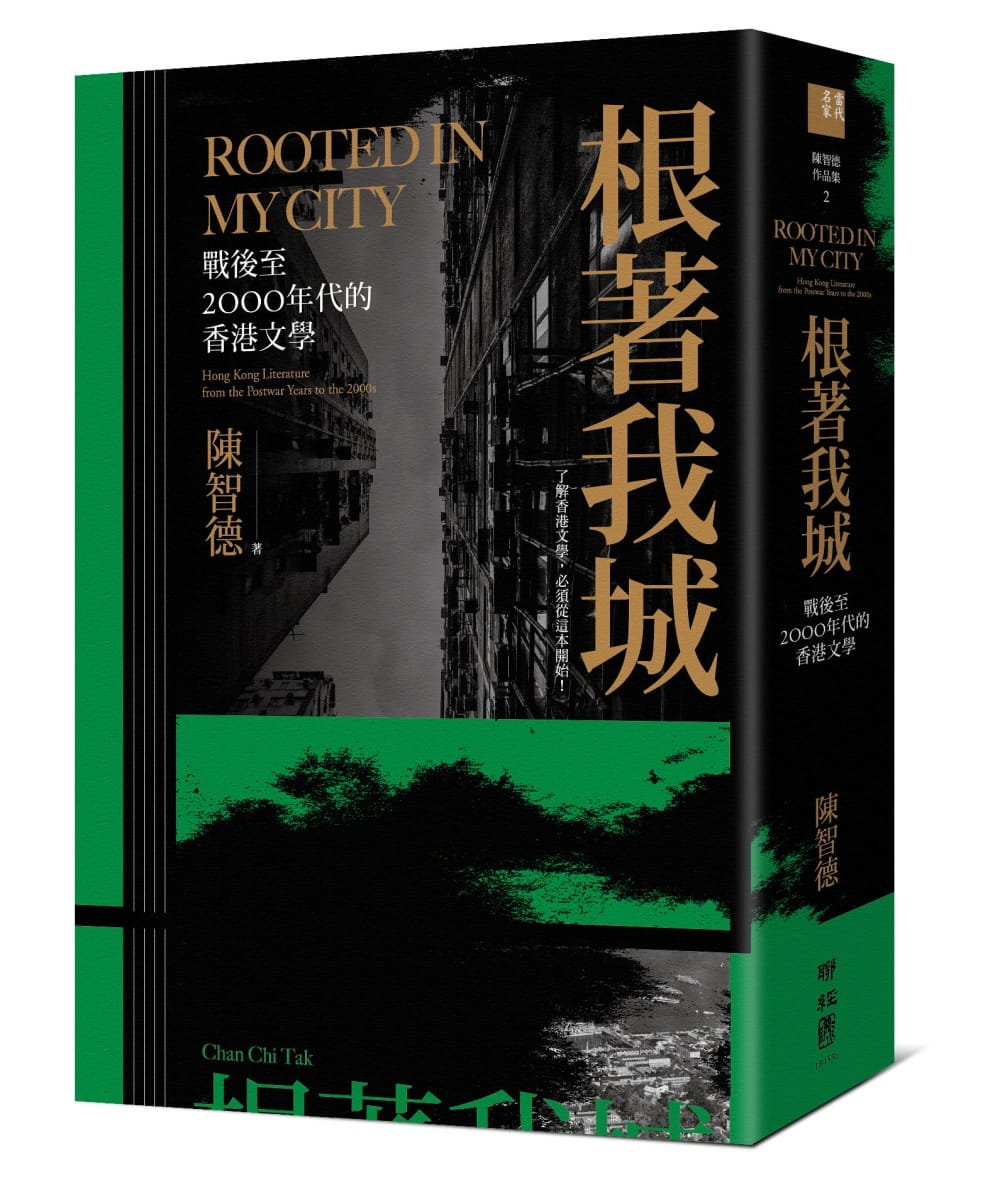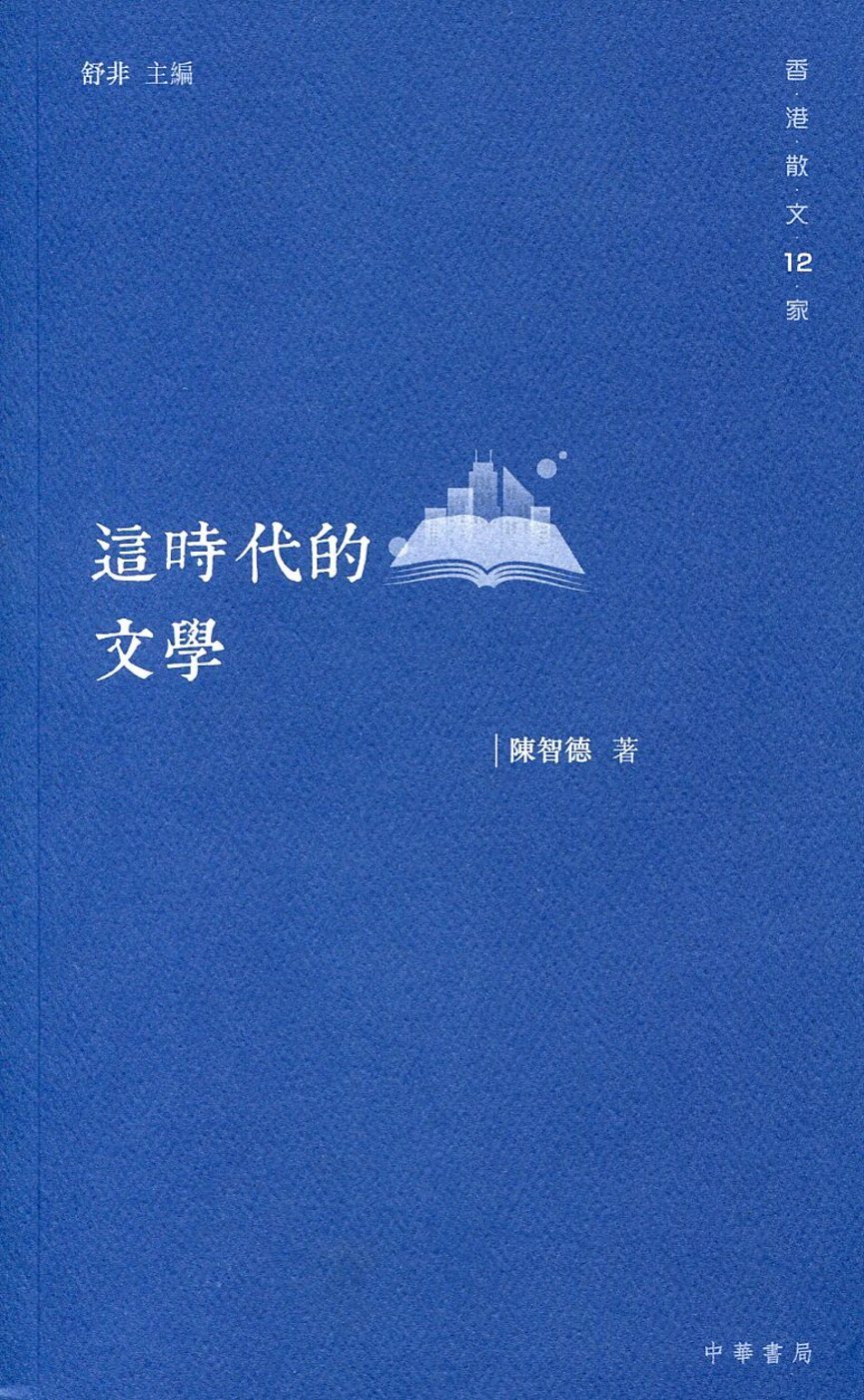序一(節錄)
我看陳滅的「我城景物略」�陳國球(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講座教授)
誰是陳滅?
很多年前,故人影印《信報》一篇專欄文章給我看,還笑著臉,說:「是你的仇人寫的吧?」文章作者是「陳滅」,內容是評論我和朋友合編的一本書。故人的言說方式,是文人的,迷信文字有其魔力;也是庶民的,一切行為以實用為尚,不作無謂之事。
我回說:「你沒有看到『滅』字的『火』嗎?」
我這個解釋,當然不合字源之學;可是,我看到的,確是陳滅不滅的火,那「抗世」的火。後來看到更多陳滅的詩與詩話。
後來認識了嶺南大學的博士陳智德。看到智德在研討會宣讀論文,解說香港文學歷史,編集香港的詩與詩論;從他說話的節奏、語調,的確是唯智尚德。
在香港,如果對文學還未絕望,大概有賴心中的一團火。在香港,如果要提倡文學,還是需要智慧、需要具備「足乎己而無待於外」的意志。
讀《地文誌》,我既看到陳滅,也看到陳智德:「歷史不容竄改?歷史一向被現實竄改,還有生命、故事、文學、香港或什麼都可以……。」「音樂是一種美,搖滾教我們看穿假象。假象不美,假象令人作嘔生厭,但有時竟和美融合,這是悲哀的。……」「由一九九七年起,香港的時鐘開始撥快,各種事物加速消逝,彼此的距離愈行愈遠……。」
讀《地文誌》,我看到我城我民的前世今生。
我的父母長輩,經歷戰火亂離、時代興廢,別去南中國的故土,只帶來「休洗紅」的文化記憶;同鄉聚居,他們營造了香港又一個互相取暖的「半下流社會」,無效地抗衡城市經濟與一切的聲光化電;父親手握一管充滿鄉音濃情的筆,心中有一面虛幻的旗。這許多的精神史,以超簡式的書寫,呈現為《地文誌》。
打開《地文誌》,還見到我的童年往事、我的青?歲月,灑落在九龍半島的西岸。「芒角」是我的「好望角」;爸爸跟小時候的我說:不要怕迷路,只要你記得彌敦道,你一定可以回到旺角西陲,你的家。像同時代的小孩、少年,我們還有一個可以歷險成長的實景空間;書,還是可以手捧揭頁的。花近高樓,登樓訪書可以望盡天涯;由彌敦道的「港明」,花園街的「寰球」,洗衣街的「新亞」、「南山」,西洋菜街的「田園」,到奶路臣街的「學津」、「學峰」、「文星」……記憶中就是不歇之數;最有象徵意義的,莫如回轉地下,離棺材店不遠的「廣華」,店內灰塵撲面,盈眼是朦朧書影。
如斯種種,感盪心靈;《地文誌》對於一輩香港人如我,弦動共鳴自是縈迴不盡。
然而,《地文誌》不止於傷逝的金鍼指南。智德寫《地文誌》,寄心乎晚明的《帝京景物略》。
方逢年序《帝京略》說:「燕不可無書,而難為書。……燕難為書,燕不可無書也。」
一個城市的故事,真的這麼難說?
序二
破卻陸沉──陳智德的「抒情考古」書寫�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香港不是一塊滋潤文學生長的地方,但香港文學卻有靈根自植的能力。
多少年來,香港的文人墨客,從侶倫到也斯、從劉以鬯到董啟章、從張愛玲到西西,為他們生長或移駐於斯的土地書寫他們的心影屐痕。筆鋒所至,皆成有情文章。而放大角度,香港本身的歷史與地理從無到有,或璀璨、或滄桑,又何嘗不已經就是一種傳奇,一種文學?
陳智德先生是詩人、學者,也是地道的香港人。他憑著個人對香港文學的熱愛、以及對文學香港的深情,寫出了一本獨特的散文集《地文誌》。這本散文集糅合了不同的文類,地方紀事、掌故拾遺、成長回憶、文學談片,無不引人入勝。述之敘之不足處,又穿插個人及他人的詩作。以此更加凸顯本書作為極具魅力的個人書寫風格。
陳智德娓娓回憶香港啟德機場的升沉,如何與九龍半島、甚至遺民歷史相輔相成;北角的一晌繁華,竟成為三代詩人李育中、馬朗、也斯的生涯註腳;維多利亞公園見證香港半個世紀的政治風雲,以及與作家如辛其氏等的創作起伏。屯門萬丈高樓興起,掩不住原來魑魅虎狼的陰影;調景嶺曾經的風風雨雨,又埋藏多少人的家國心事?
少年陳智德出入港九大街小巷,但讓他駐足最久的地方是書店。這是香港文學最奇特的所在。陋街深處,危樓一角,卻偏偏散發出書香,或更多時候是霉臭,的味道。廣華復興,青文東岸,就在狹仄的空間中、層三疊四的書堆裡,一個文學啟蒙的故事緩緩展開。曾幾何時,少年已經微近中年,那一間間書店已經歇業關門,那灰塵中的風雅只成為少數人的回憶。
在這層意義上,《地文誌》所要從事的是一個人的考古學。陳智德其生也晚,已經錯過香港文學無端興起的那神奇的一刻,而後現代加後社會主義治下的香港,以往人文景觀快速崩毀。他尋尋覓覓,鉤沉訪舊,無非期望在一個時代灰飛煙滅之前,考證、存留一鱗半爪的證據。就像在熙熙攘攘的旺角鬧市地下,誰能想像能發掘出漢代、晉代、唐代文物?在浮光掠影的生活中,想必還有珍貴的文學靜靜等待有緣的讀者:
事物之真象,向為我輩所執著,然詩人筆下之城市,每多流光幻象,唯秉燭探照,終見本真幽隱其內。
陳智德的考古學又是一種抒情考古學,此無他,他考察的對象是文字的因緣,情感的流轉,想像的歸宿。「抒情考古」語出汪曾祺,原用來描述業師沈從文後半生從事工藝美術研究的方法。一九四九年後,沈從文無緣繼續創作,卻在工藝史裡發現了另外一種「創作」的可能,並從中有了深刻體悟。沈在《抽象的抒情》(一九六一)寫道,生命的發展「變化是常態,矛盾是常態,毀滅是常態」,惟轉化為文字,為形象,為音符,為節奏,可望將生命某一種形式,某一種狀態,凝固下來,形成生命另外一種存在和延續,通過長長的時間,通過遙遠的空間,讓另外一時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無有阻隔。
陳智德也許無從比擬大師所經歷的生命斫喪。但在面對歷史的另一刻僵局時,是否也心有慼慼焉?用陳所敬重的女作家鍾玲玲的話來說,《地文誌》所要追尋記錄的正是「時光中無法摧毀的糊狀物,終於凝固為形狀不一的物質,成為心靈中,易碎的珍愛物」。
《地文誌》的書名或有諧仿《漢書.藝文志》─中國最早藝文經籍的目錄─的意圖。無論如何,陳智德為香港的地景與藝文做出觀察的宏願不容小覷。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然而如陳所言,「『狹窄』與否本不在乎所寫的地方,而在乎執筆者的眼界和文學修為。」誠哉斯言。破卻陸沉,洞昭盲瞽,陳智德的香港抒情考古,可以如是!
前記
陳智德
我的文學啟蒙不在學校或課本,而是初中時代旺角奶路臣街一帶的路邊書攤,繼而是樓上的書店,仍記得初次讀到一九四八年上海星群版辛笛《手掌集》、一九七五年臺北志文出版社新潮叢書楊牧《瓶中稿》和一九八二年香港素葉版馬博良《焚琴的浪子》三書的情形,盛載真正文藝的書籍那溫婉而堅軔的本質,教我著迷而無從脫離。
辛笛〈夏夜的和平〉一詩這樣寫上海:「最後一列電車回廠了�都市心臟停止它不自然的抽搐」,楊牧〈瓶中稿〉有這樣的名句:「但知每一片波浪�都從花蓮開始」,馬博良〈北角之夜〉這樣寫香港的北角:「最後一列的電車落寞地駛過後�遠遠交叉路口的小紅燈熄了」;三首詩談的都是作者自己的本土經驗,正給時屆初中年紀的我以莫大的震動和啟發。
由那時開始,我矢志從事文學,不覺流連至今。從古典到現代,從中華到香港,無論走到何處,都離不開腳踏的土地。本土經驗本就是我們的成長以至更大範圍下的共同體社會經驗,我們生活其中,也愈發認清我與非我的真幻;是以書寫本土絕不等同歌頌本土,本土也有許多負面事物,教我們疾首,我們有時也嚮往遙遠的他方、願意承接更古老的傳統、參與更宏大的整體世界,但知每一個出發點,不都由當下腳踏的土地開始。
二○一二年,我有幸獲選為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的香港作家,八月底出發赴美,參與為期兩個半月的計畫,與國際作家交流之餘,我把握近幾年難得的空閒,起草構思多時的《地文誌》系列寫作,本書大部分文章的初稿,都在愛荷華完成。除了珍貴的閒暇,也認識到國際作家層次不同的本土關懷,讓我再思本土經驗的普世共性。十一月中回港後,以僅有的工餘時間修訂內容、補充資料,再加入若干增補過內容的舊文,耗時多月始得完書。
本書以散文形式撰寫,結合香港文學的地方書寫、歷史掌故和我個人的地方生活體驗,穿插他人及我個人的相關文學片段,節錄的文字有新詩也有舊詩,有散文也有小說的片段,由此引申出相應的評論性文字,但不同於學術評論,主要用以結合我個人的地方生活體驗,互為闡發,也嘗試讓散文與自己的詩作融合,有時,散文部分成了詩的載體,有時是詩作為文意未盡的延伸。本書追跡地方性的文學故事,建構基於本土文化認同的情志和關懷,這樣的散文創作,用現有的術語來說,或可歸入一種「地誌書寫」,但應該不完全等同,我姑且暫稱為一種「地文誌體」。
我知道許多人視「本土」─尤其是「香港的本土」為一種「狹窄」的題材,我不想在這裡申辯,只想說,香港一地,無論感覺多狹窄,從文學的角度,與地球每寸土地、每個城市都是平等的。我時常自警於本土之可能褊狹和自我封閉,然而「狹窄」與否本不在乎所寫的地方,而在乎執筆者的眼界和文學修為。如果本書最終也淪入「狹窄」之議,責任在我力有不逮,與香港無干。
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首有言:「夫都燕,天人所合發也。陰陽異特,睠顧維宅,吾知之以天。流泉膴原,士烝民止,吾知之以人。此《帝京景物略》所為著也。」本書也差不多以同一態度去寫香港,也同樣視香港是由「天人所合發」,我們的文學、我們的歷史,以至由土地化生的願望、情志,本歸於更超越的共同。願這書屬於香港,也獻予所有關懷土地的人、寫給與大地同一呼息的地方─即使不現實,至少可作此文學幻想。是為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