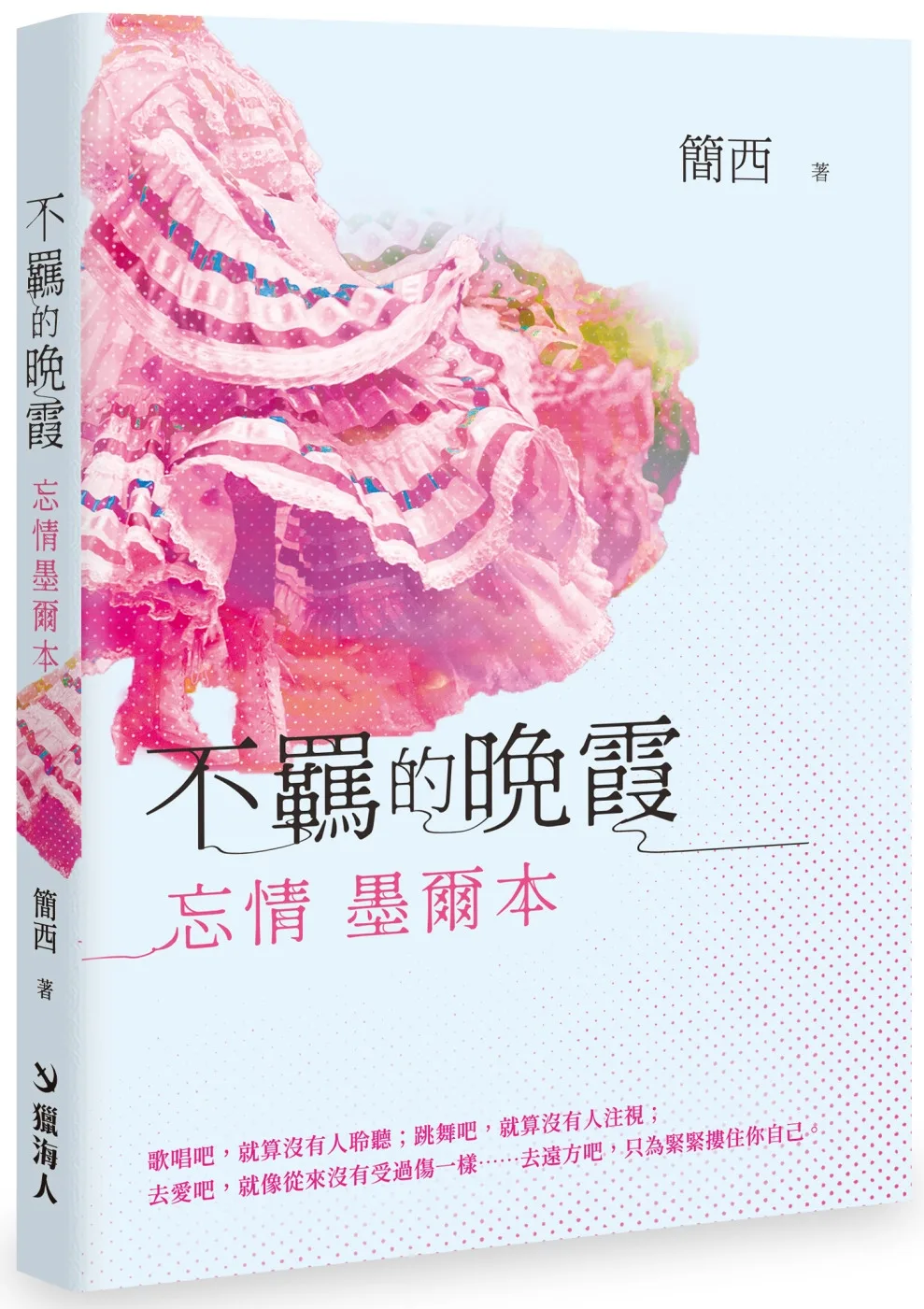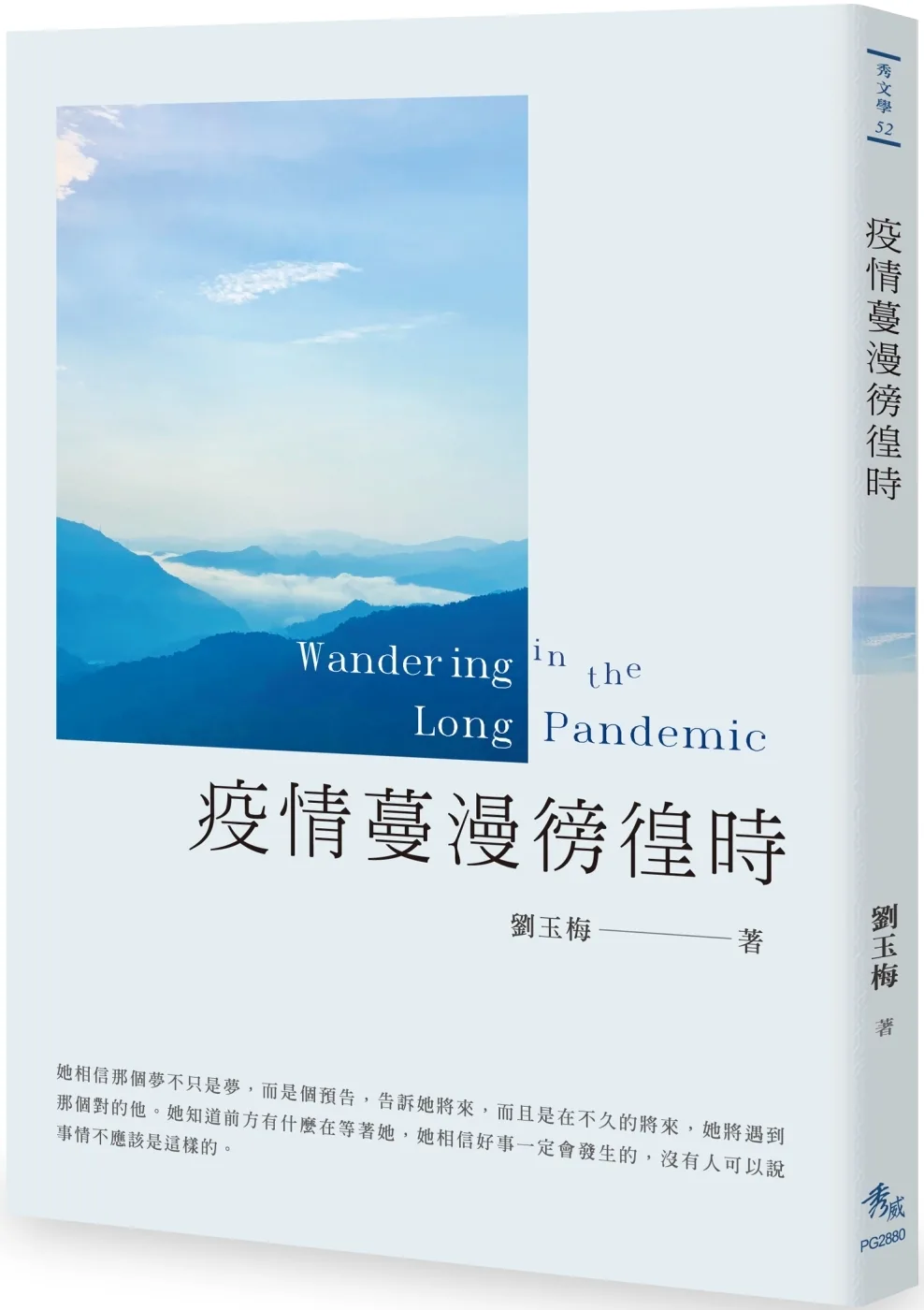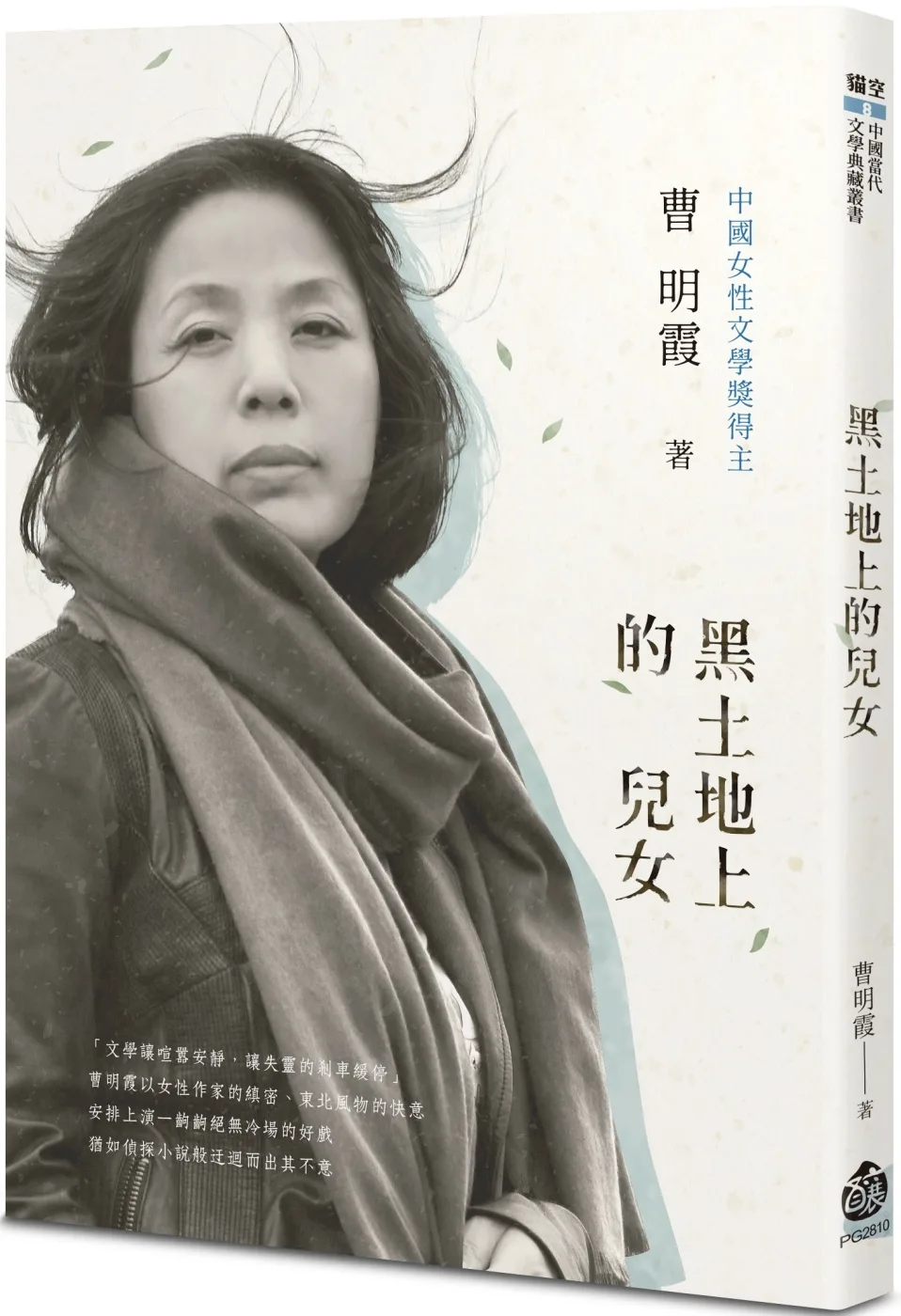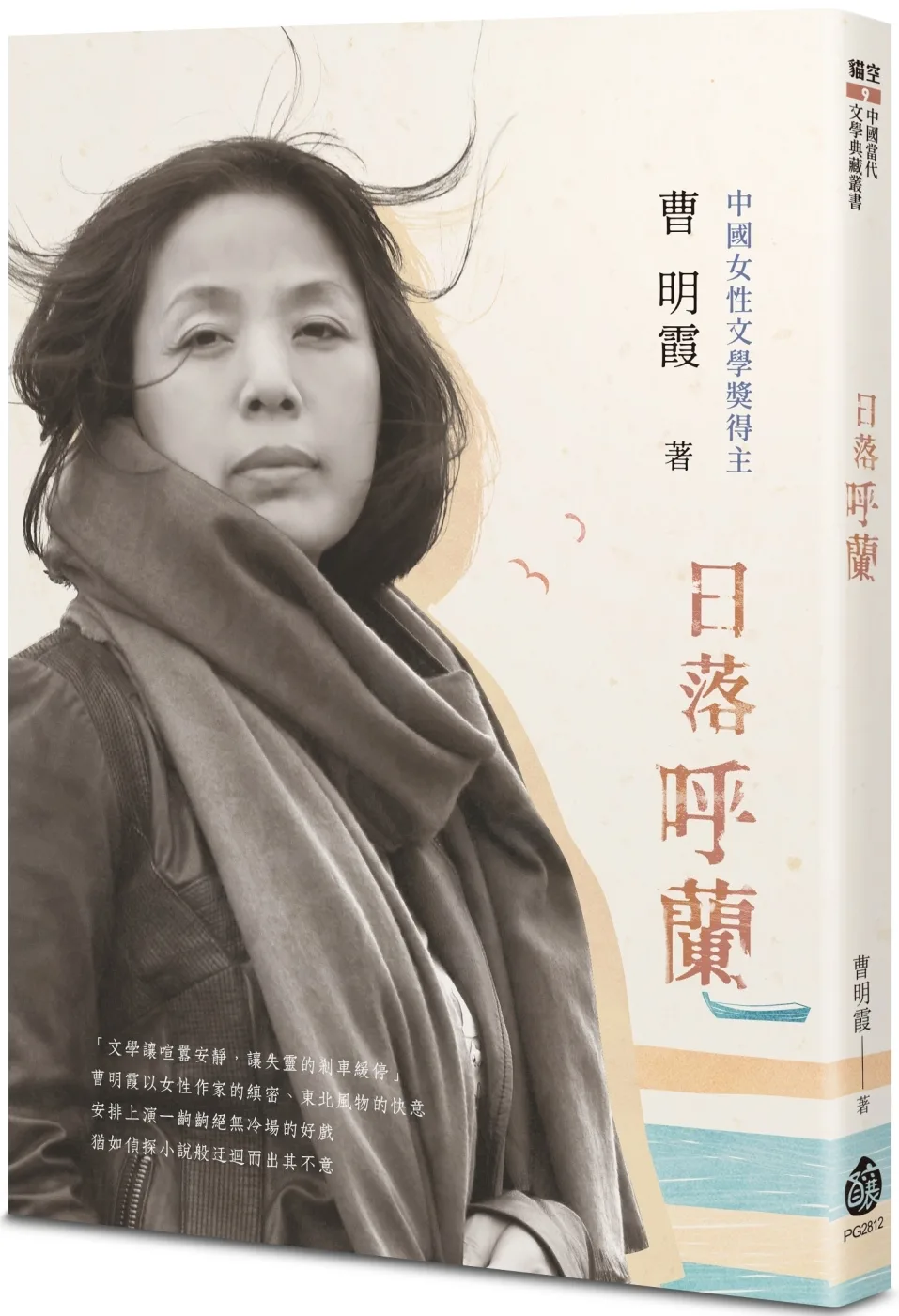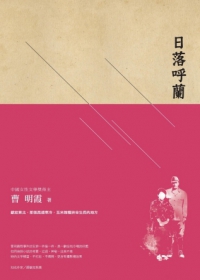序
煙囪與呼蘭之間
文藝書寫容易從己身出發,記憶永遠是敘述著作上好的方便素材。以當今叨絮過往,事件與人物是堅實的、膚近的,時與空的乖隔,讓回憶的過程與手續得以上彩黑白褪色的經驗,也能夠在刺枝裡剪出玫瑰。然而,小說非自傳,故事中的「我」不必要是作者本人,正如同,「妳」或「他」可以輕易是百分之四十七點三五的作者自身一般。
曹明霞的《呼蘭兒女》便是這麼樣的一部小說。她不僅採用了一般書寫回憶慣用的時空跳接手法,也以不同人物為敘述主體,牽帶出和這些人有關的周遭實體、社會理念,以及地方習俗與迷信,也因此,對於同一時間裡的相異空間,或同一空間中不同時間的著墨配置,必定無法避免地有所重覆。然而,明霞卻能機巧地避開無謂,她在即將重疊之處便已煞住,把「不說」的部份,留待在其他章節開展。而那「煞筆」定點並不顯得突兀,讀者以為此即終結,不料在他處竟然終結復生,不但復生,敘述更往細裡去。就像是一旦舞台背景拖拉到觀眾跟前,所有的材質、紋路與中介色彩就要逼人靜靜審視。原本的陪襯人物一旦成了要角,哪怕是臉上皺折也不給遁形。這種柳暗花明的銜接手法,非有書寫前的縝密佈局與計劃不能成就。
四代人,一個世紀的世事變遷是驚人的,也是令人神傷或欣喜的。書中主述的家庭人物從貧困到小康,甚至富裕,其中的款款周折,因國家社會大環境變遷而影響小人物生活所呈現出來的自然與突兀,也出現在明霞的書寫語言本身。在她極具地方色彩,約半個世紀前,甚或現在,中國東北特有的語辭、語境中,有時會跳躍出極現代的政治、經濟字眼。從這個角度出發,明霞是站在一個遠距離的情境裡,冷酷鳥瞰可以讓人體會溫熱、聽到潑辣、摸到粗劣、聞到怪異、看到蒼涼的過往。明霞手握一根灰色大棒,毫不遲疑地驅趕人氣喘噓噓地跟著她的人物奔跑、叫喊、翻騰。
「多年後,當我離開家鄉到處流浪,身心疲憊的時候,靜躺下來,就特別想念那曾經的呼蘭河,河西那株百年老樹。……當我再回來河邊憑弔的時候,呼蘭河水已經變得像個衰老的醜婦……遠方那株古樹,也衰朽成了一個老頭……一河一樹,它們更像一對年老的夫妻,相伴在天地。」這段告白令人想起俄國小說家蕭洛霍夫(Michail Sholokhov)的代表作《靜靜的頓河》(And Quiet Flows the Don)。頓河發源於莫斯科東南一百五十公里處,全長近兩千公里。蕭洛霍夫一生鍾愛自家村子臨近的頓河,不願離開,正因那「水邊的石子被河水沖得泛出灰色,就像一條彎彎曲曲的花邊,再往前,便是奔騰的頓河水。微風吹動,河面上掠過一陣陣碧色的漣漪。」蕭洛霍夫筆下的哥薩克士兵葛里哥利(Grigori)歷經戰亂、欺偽、背叛、流離、痛楚,畢竟要回到那承載他生命開端與終結的頓河,也只有這條緩緩前行,悠長紛擾一如人間世的長河,才能與葛里哥利的情仇與共。
五百多公里長的呼蘭河在哈爾濱市注入松花江。大河孕育生命,培植消長。曹明霞一出手便道出呼蘭河域四個世代的故事,特別是女人的故事。在歷史的時間軸上,她從上世紀初日本佔據東三省起筆,跨越到一胎化政策的時代,當然也沒忘了「小平說,允許一部份人先富起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效應。小名「留住兒」的主述者劉君生,引領讀者觀看因逃避兵亂,與家人失散,後被賣入慰安所的姥姥、姨娘,以及其他年輕女子,站在敞頂的軍車上,美花一般地招展過街。這是二十世紀初,中國哈爾濱市的妓女廣告手法。在那「歪瓜裂棗也不得進」的妓院裡,得遵守「花姑娘八不准」:不但「不准與人合謀、私奔、不准挑肥揀瘦、不准敷衍了事,必須童叟無欺」之外,還要「不勾引士兵、不偷搜腰包」,並且「撿到失物要歸還、態度要好、恪守行規、勤肯幹好每一天」。一旦不慎懷孕,就要經歷一場生不如死的墮胎浩劫。「給女人喝下一種湯藥,是用來打胎的。在女人的小屋裡傳來高一聲、低一聲的痛叫,一個小時過去了,聲音沒有停止……日本軍醫去乾淨的辦法,是叫來那兩個操練模具的中國武士,一人一邊,把女人倒立著架起來……藥水注入後,扶著不動…以保證體內藥水充分化合。……大約過了一刻鐘……倒下來的女人,全身沒了骨頭,也沒了聲息,變成一具沒紮住口的袋囊,血塊兒,一點一點,流了出來。」
正當德國納粹橫掃歐洲各國,大批猶太人遷往巴勒斯坦地的同時,黃愛荷在中國東北的日本佔領區裡開了家「貴賓俱樂部形式」的「女人間」。她讓「滿堂春」裡的姑娘們識字、學藝,讓她們不輕易賣身,更讓那些大戶犯癢而闊手撒錢;如此的生意伎倆也只有黃愛荷這般高手才使得出來;她認錢、花男人的錢、翻臉無情的人格特質,也似乎是得以適時培養,進而內化了。
明霞讓美麗精幹的姥姥黃愛荷,「像扔傢俱一樣頻繁地扔棄她身邊的男人」。她的那雙小腳「又臭又恐怖,聞不得,也看不得,太嚇人」,而且「晚上洗屁股,嘩啦嘩啦,天天不落(不間斷)」,在一年只洗一次澡的地方,老姥姥每天的身體清潔工作,「有那必要嗎」?
母親李連生是貫穿全書的中心角色,也由於她的「多產」,讀者才能見識得了故事中有如滾滾珠玉般的精彩人生。這個由「大姑娘」,也就是未婚媽媽,所生下的女嬰讓姥姥撫養,十四歲時自己改名為李麗君,看上了有著厚實胸脯的劉慶林,十五歲嫁了過去,十六歲生子,此後,肚膛就從來沒空蕩過。雖然夭折了幾個幼兒,仍在窮困環境下拉拔十個「野草般生命旺盛的兒女」成人。以軍管為家管,自是母親的過人之處。「媽媽說話如訓示,孩子聽話如聽訓」是作者自己在書中的命定。整本書裡,不論是人物對答或者場景描述,曹明霞筆下厚實的地方主義色彩(regionalism)有如數公噸重的鮮麗油漆,潑灑得讀者滿身滿臉,氣味特異,黏人手腳,不是一下子能洗脫得了。
這母親不但懂得唱壓軸,「她換上了沒有漿糊的衣服,臉洗得乾乾淨淨,站到地中央,丁字步,兩手扣握,舞台上的大牌演員一樣」;她還能玩撲克,「母親一女流,敢於爭戰在三個爺們兒中間,而且她總是能摸得一手好牌,敢叫板。……母親張口就給蓋個七十;而且隨著那七十的叫喊,她手中的撲克,能發出﹃啪﹄的一聲脆響,震撼極了。」母親的特立獨行更表現在她對夭折嬰兒的處置上。北林鎮是故事發生的主要場域,「當地人習慣把夭折的嬰兒隨便就拋了。……我們常能看到光著身子的嬰兒,凍硬得像個塑膠娃娃,他們散落在豬圈或廁所旁,頭已經被啃掉了。……凍成冰雕一樣的糞便上,直挺挺地躺著一個小死孩兒,都長頭髮了。……母親都是花五塊錢雇了那個光棍老頭,讓他用草簾兒捲了,從窗子遞走,給埋到呼蘭河邊的那棵百年老松樹下。死的孩子不能走門,從窗子改轍,免得後面的孩子跟著他走。」粗糙又堅韌如亞麻的母親,只會因著骨肉受屈而倒下。當她知道女兒英子和班上的花花公子私奔時,便因心臟「上火而癱倒」,後來英子嫁了個有父母姐妹一大幫的瘸子時,母親能不再犯心臟病?
對於母親李麗君的身世,作者把兩次伏筆藏得那麼精緻,有如春風吹過,秋霧散去,毫不留下痕跡。直到尾聲,明霞的魔法棒輕輕一點,讀者才立時大悟,二姨娘光著身子簷下淋雨的絕美淒清,以及女人們為了賞金丟下工作,連遮攔都不屑的貪婪,雖是一掃先前迷疑,讀者頓起的愁情再也無法壓抑。
《呼蘭兒女》的語言跳躍、滑溜、粗嘎、喧囂、瀟灑、潑辣,帶筋也帶勁!它傳達了部份作者的性情,傳達了故事發生當地鮮活的人際關係──一種「打是疼,罵是愛」的淋漓詮釋。至於以刀鋒言辭對答,傷害彼此之後才默默地以行動補贖的互動模式,是否得宜,可否是貧窮階層的專屬,應該是心理及社會學家所要埋首的功課。而公器私用,無處不貪的作為,如同「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屬於當地,也屬於中國?難道數十年前的「新中國」和近日的「阿拉伯之春」雷同,雖是不怕了,敢頂撞了,卻腐敗依舊、沈?依舊?
「呼蘭」是否意為滿語「煙囪」有待考證。呼蘭河域世居人家的裊裊炊煙依舊迷茫,從不止息。一柱煙囪之下就有「炕上一個個的腦袋,炕下一排排的鞋子」;一盞清燈邊旁就有一頁情緣、一段生死、一番拚搏。呼蘭河畔,總會有女人切腕、喝紅礬自盡,也總會有男人手術後縫合的腿上像被塞了一團的繩子,成了無法解開的筋疙瘩。
顏敏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