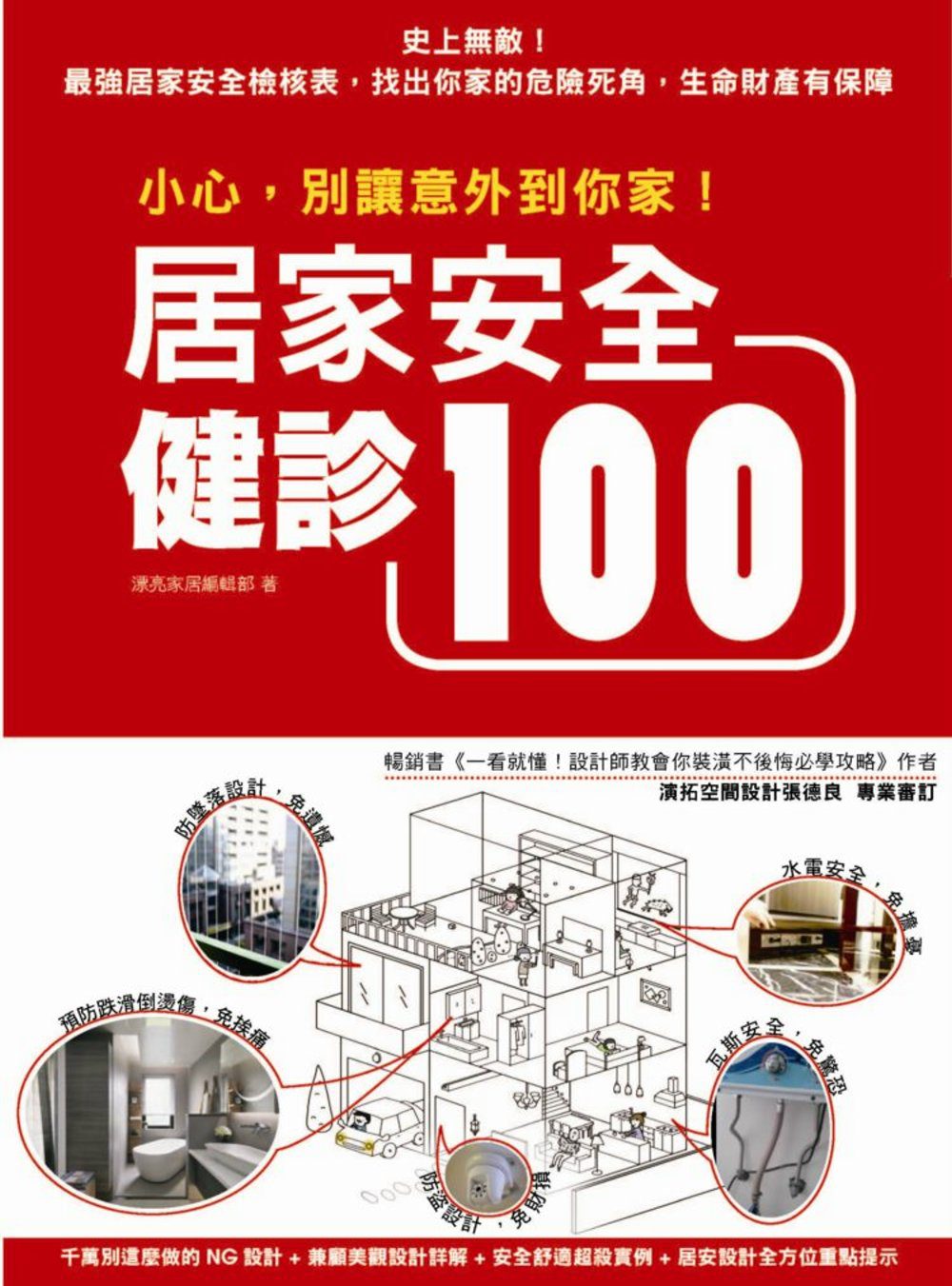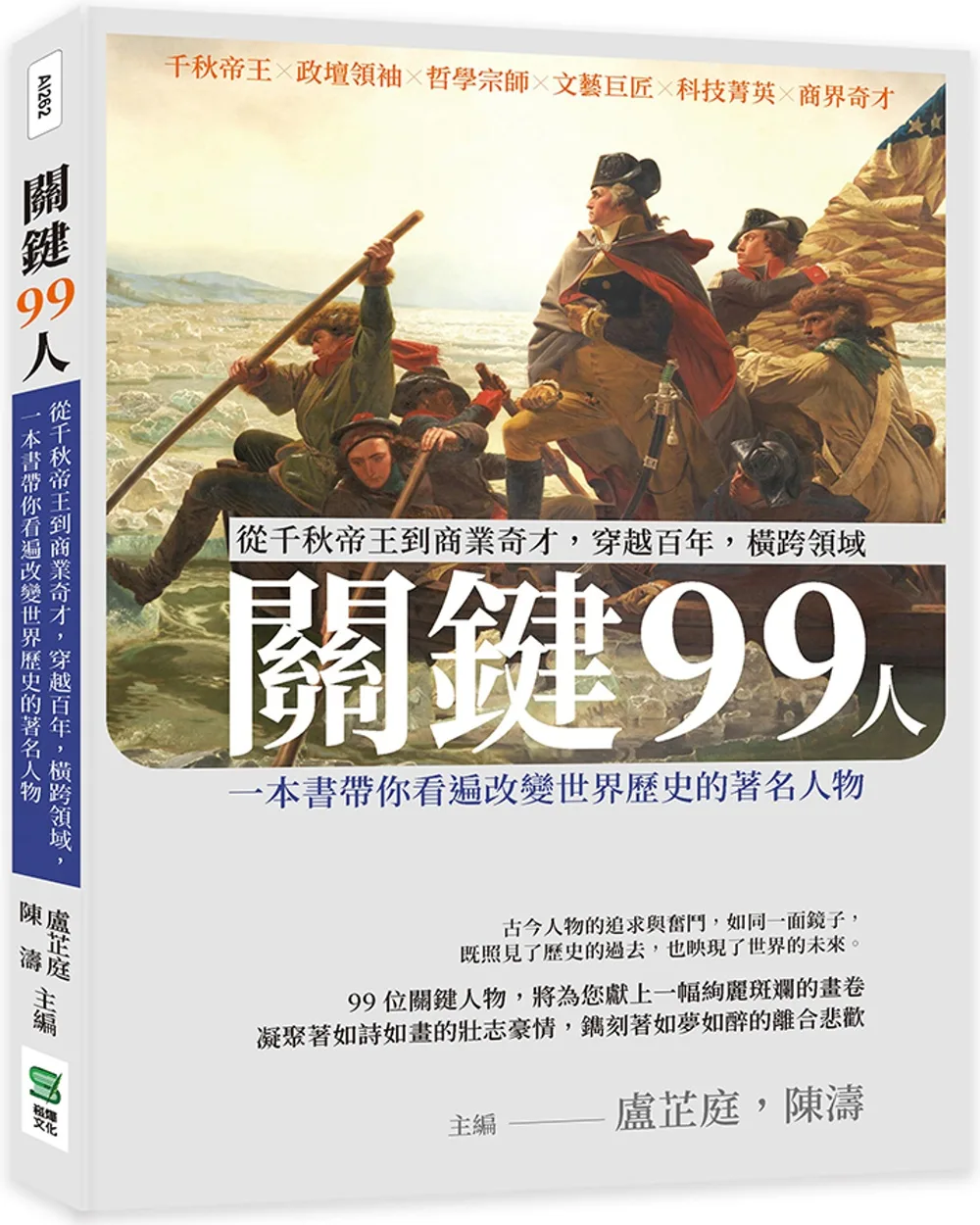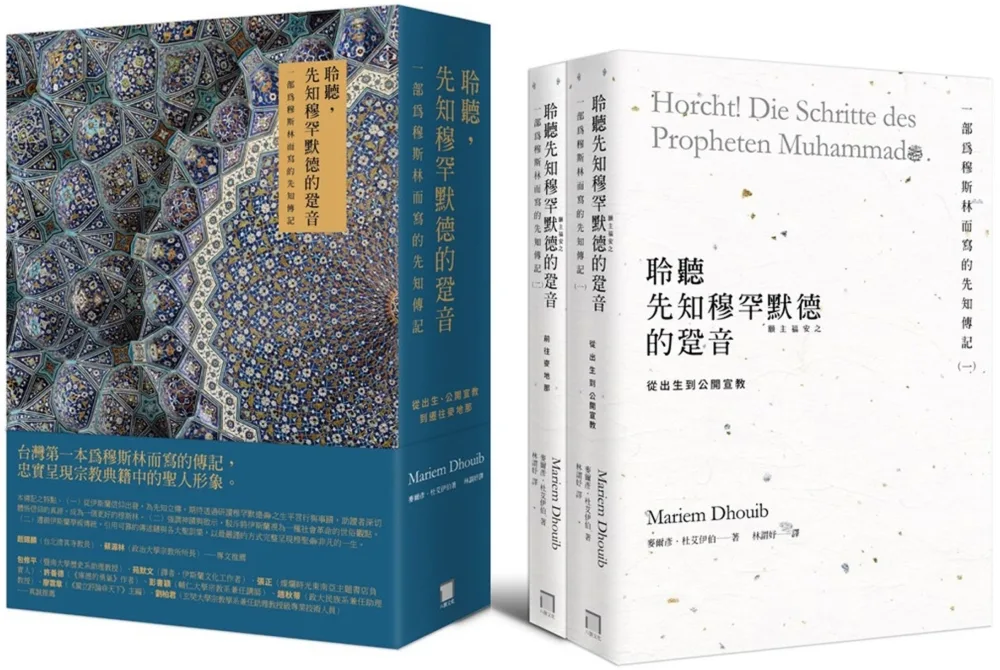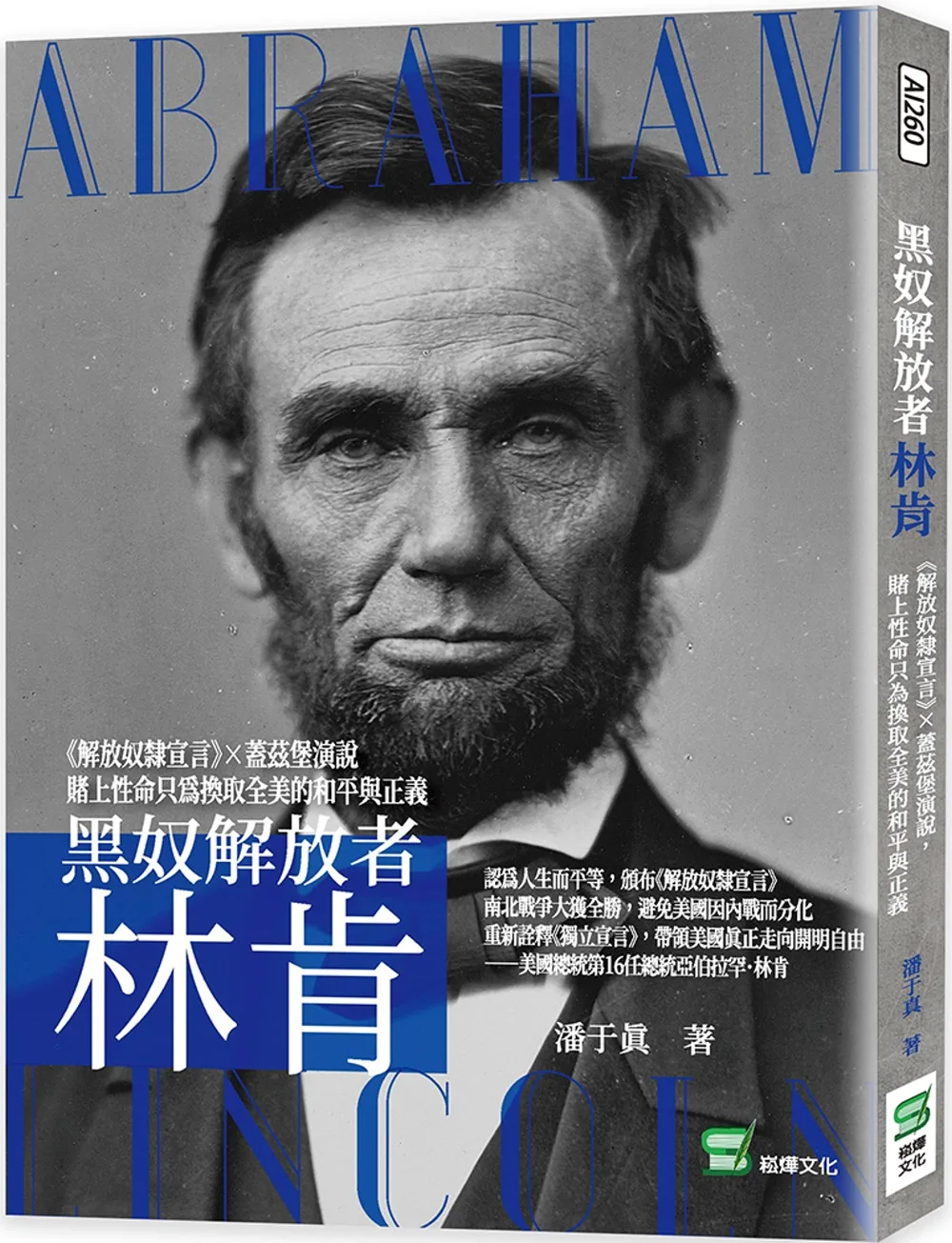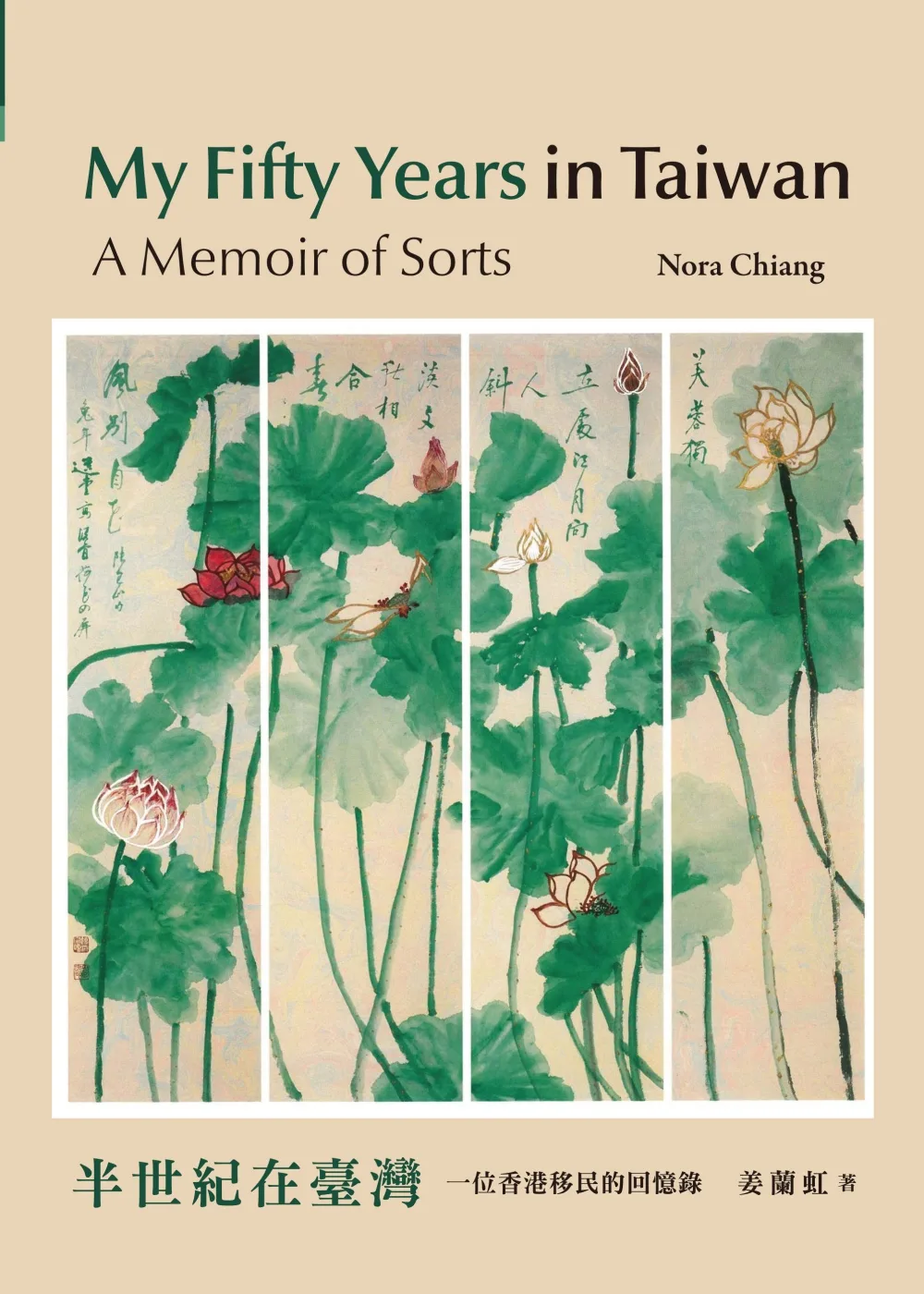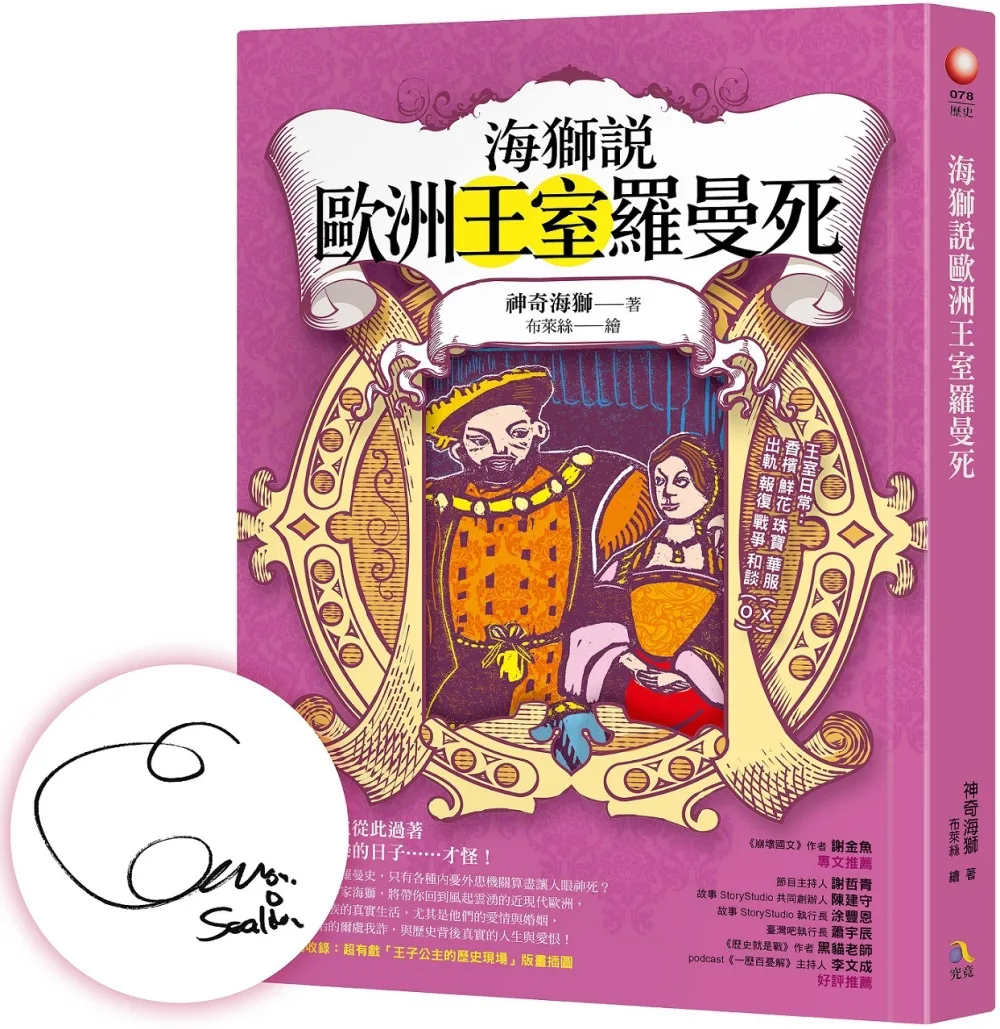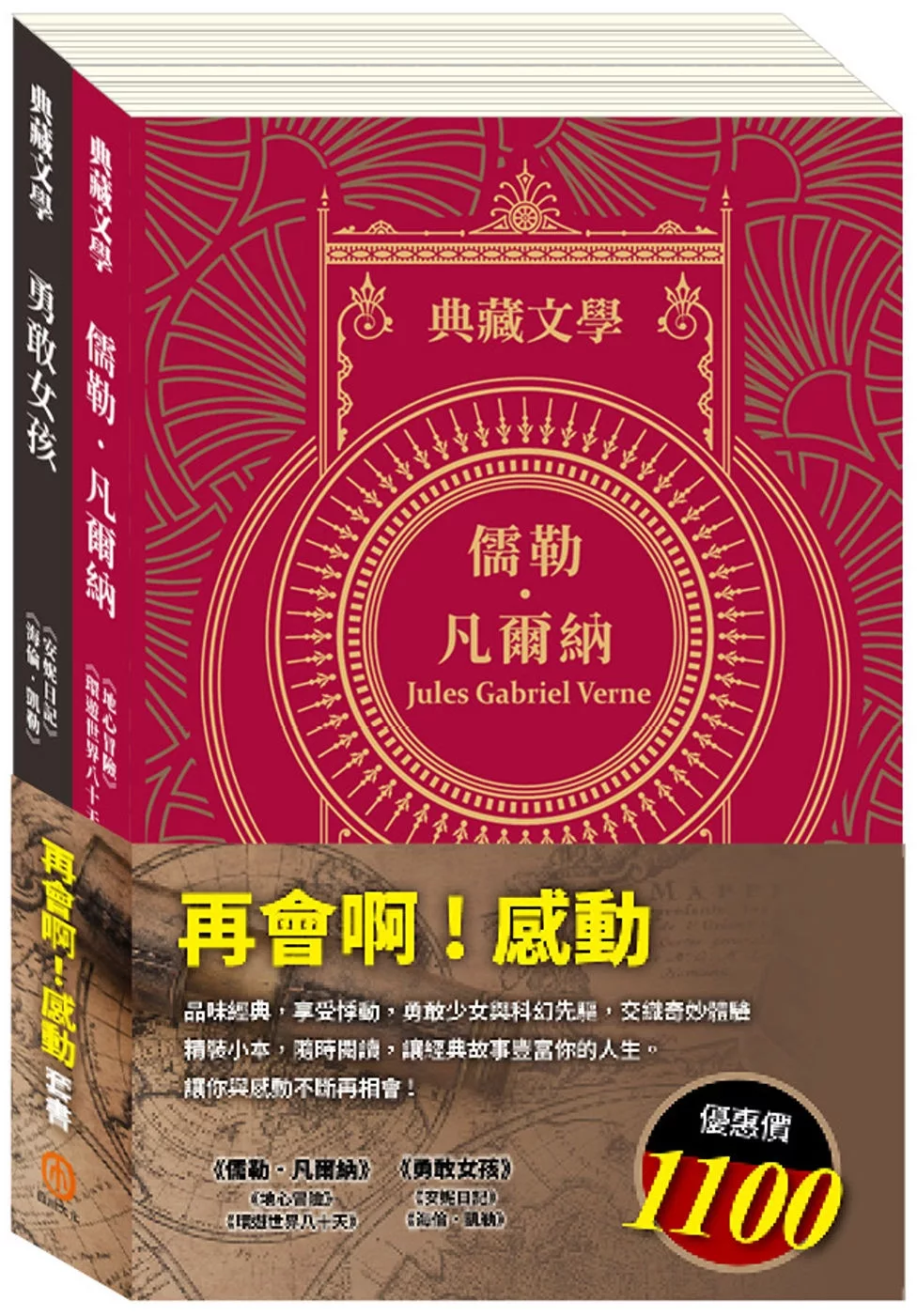譯序
二○一八年是海倫凱勒去世五十週年紀念。我忽然覺得可以用「不世出的奇才」來形容這位集盲、聾、啞於一身的偉大女性,因為她打敗了三種障礙,創造出比看得見、聽得見的人更偉大的成就。
那麼,這本日記的可貴之處何在呢?海倫凱勒曾說,如果老師安妮.蘇利文.梅西離世的話,她就會成為「真正」的聾盲人。蘇利文在教導了海倫凱勒五十年之後,於這本日記開始之前的兩個月去世了,海倫凱勒在成為「真正」的聾盲人後,如何去面對三重的打擊—失去了「老師」蘇利文,她等於失去了眼睛、耳朵和終生伴侶?答案就在這本日記之中。
日記起始於坐船前往英國、再轉往蘇格蘭,終結於前往日本訪問的途中,歷時約六個半月,但在這樣一部不算長的日記中,我們看到了一盞美妙的心燈照遍了她內心的各個角落,也照亮她所看不到的世界的各個層面。
首先在政治方面,她不諱言同情沙皇俄國(包括列寧);憎惡德國希特勒的專權,並對英國的兩位首相格拉斯頓和狄斯累利提出深刻的評騭,筆鋒犀利,令政治家望塵莫及。此外他對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評論也一針見血:「我長久以來都覺得,解決猶太人問題的唯一方法是:讓他們有一個故鄉,可以在那兒平安無事地發揮他們在宗教、藝術和社會正義方面的天分。」就某個意義而言,這部日記也是世界歷史的重要文件。
除了世界大事之外,海倫凱勒對文學的造詣也可以從這部日記看出一二。她提到T.S.艾略特(T. S. Eliot)的名詩〈空洞人〉(The Hollow Men),並試圖去了解其含意;她顯然閱讀佩皮斯(Pepys)的大部著作《日記》;她閱讀雨果(Hugo)的《海上勞工》(The Toilers of the Sea)和《悲慘世界》。在莎士比亞方面,她引用史奎爾爵士的評論:「我們的時代不喜歡莎士比亞,因為他的藝術大部分訴諸我們的想像力,機械似乎抑制了想像力。」最難得的是,她在前往日本的船上閱讀了大部頭的點字版名著《飄》(Gone With the Wind)。海倫凱勒對詩的喜愛在日記中多處可見。除了艾略特的〈空洞人〉之外,她也提到了華滋華斯的〈勞妲蜜亞〉(Laodamia),並在日記中不時穿插富有哲理及美感的詩。她引用濟慈「美就是真,真就是美」的名言。在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中,他寫道,「在很有家的氣氛的高雅起居室中安靜地坐幾分鐘,花園中滿是丁香花,那種感覺很好。」她對植物和花頗多著墨。失去視覺、聽覺後觸覺特別靈敏的她,喜歡觸碰雕刻(如羅丹的《沉思者》),這也是她欣賞藝術之美的最直接途徑。
海倫凱勒見到的名人何其多,包括馬克吐溫、卡內基、卓別林、泰戈爾、愛因斯坦、蕭伯納等(還不包括外國君王)。關於愛因斯坦,她在日記中說,「我只能說,當我站在愛因斯坦身邊時,突然感覺好像地球的喧囂聲在他的個性所散發的大量友愛靈氣中變得靜寂……」關於蕭伯納,亞斯都夫人把海倫凱勒介紹給蕭伯納,海倫凱勒說,她多麼高興遇見他,但蕭伯納似乎對她沒有表現足夠的興趣,於是亞斯都夫人說道,「蕭先生,你知道,海倫小姐又聾又盲。」誰知蕭伯納的回答竟然是:「嗯,當然了,所有美國人都又聾又盲!」但海倫凱勒卻說,她一點也不惱怒,「我已很習慣他的奇怪、尖刻、投機性的言語。」
海倫凱勒對中國很感興趣,除了在日記開始不久的地方引用中國詩人張志和的軼事之外,也對當時的蔣介石、張學良等有所評論,尤其日記以有關中國的一則故事做為寓言性的結束,令人佩服她的博學。
她對財團的看法很契合時代的開明觀念:「商業的關聯已經從家庭事業擴展到財團……開明的政治家和經濟學家現今都很恐懼財團,視之為目前為止最有權威的寡頭政治。」此外,海倫凱勒雖篤信基督,卻認同無神論的湯瑪斯.潘恩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信仰基督的她也在最後一則日記中「強烈地認同佛家對於『不朽』的態度。」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整部日記無時無刻穿插著對「老師」安妮.蘇利文.梅西的真誠懷念、孺慕之情,如果我再引用,就會洩露全書的「天機」了。
我想引用海倫凱勒最醍醐灌頂、振聾啟瞶的一句話做為結論:「我利用我的受限之處做為工具,不是做為我的真正自我。」這樣一位海倫凱勒不成為「不世出奇才」也難。
陳蒼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