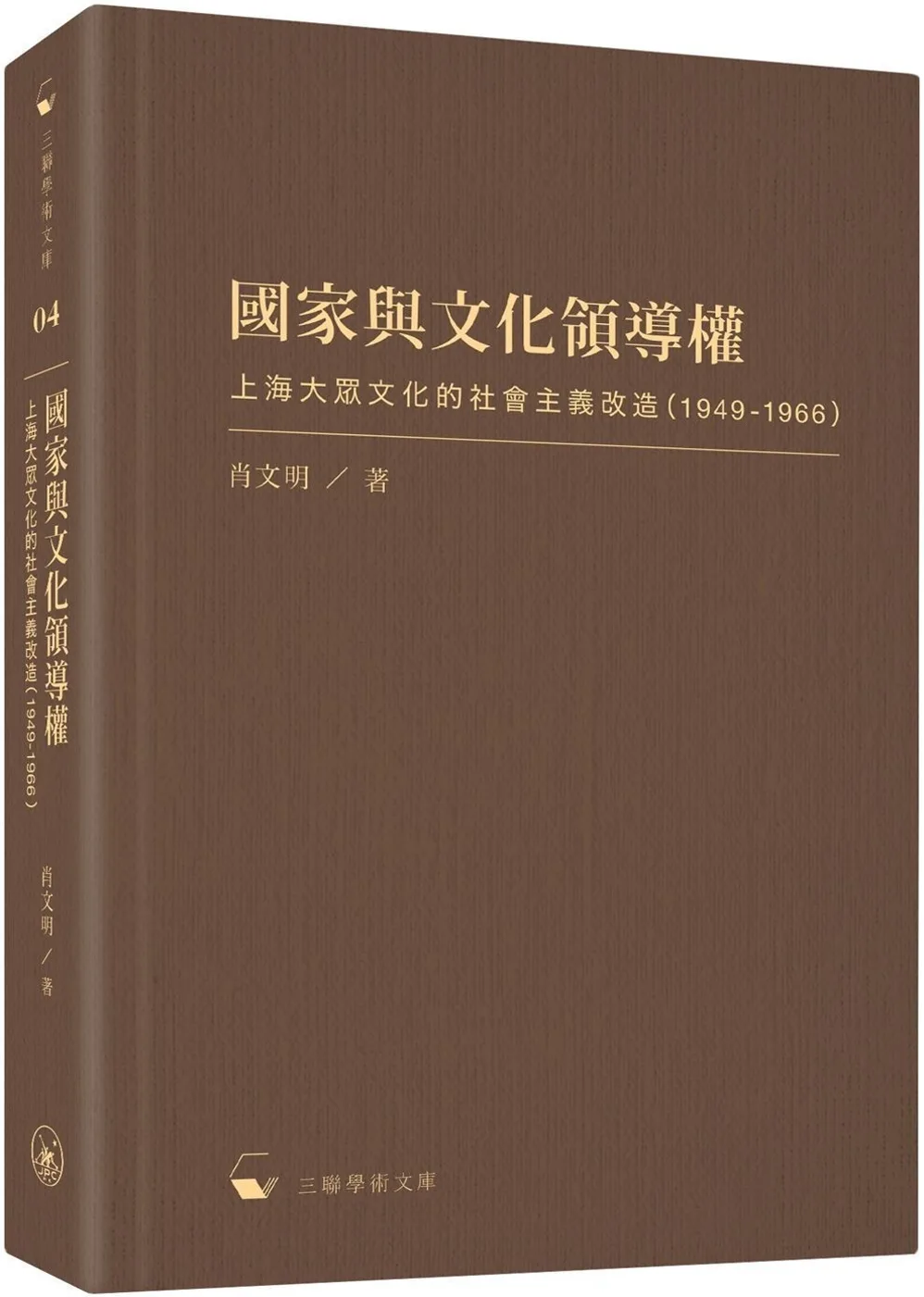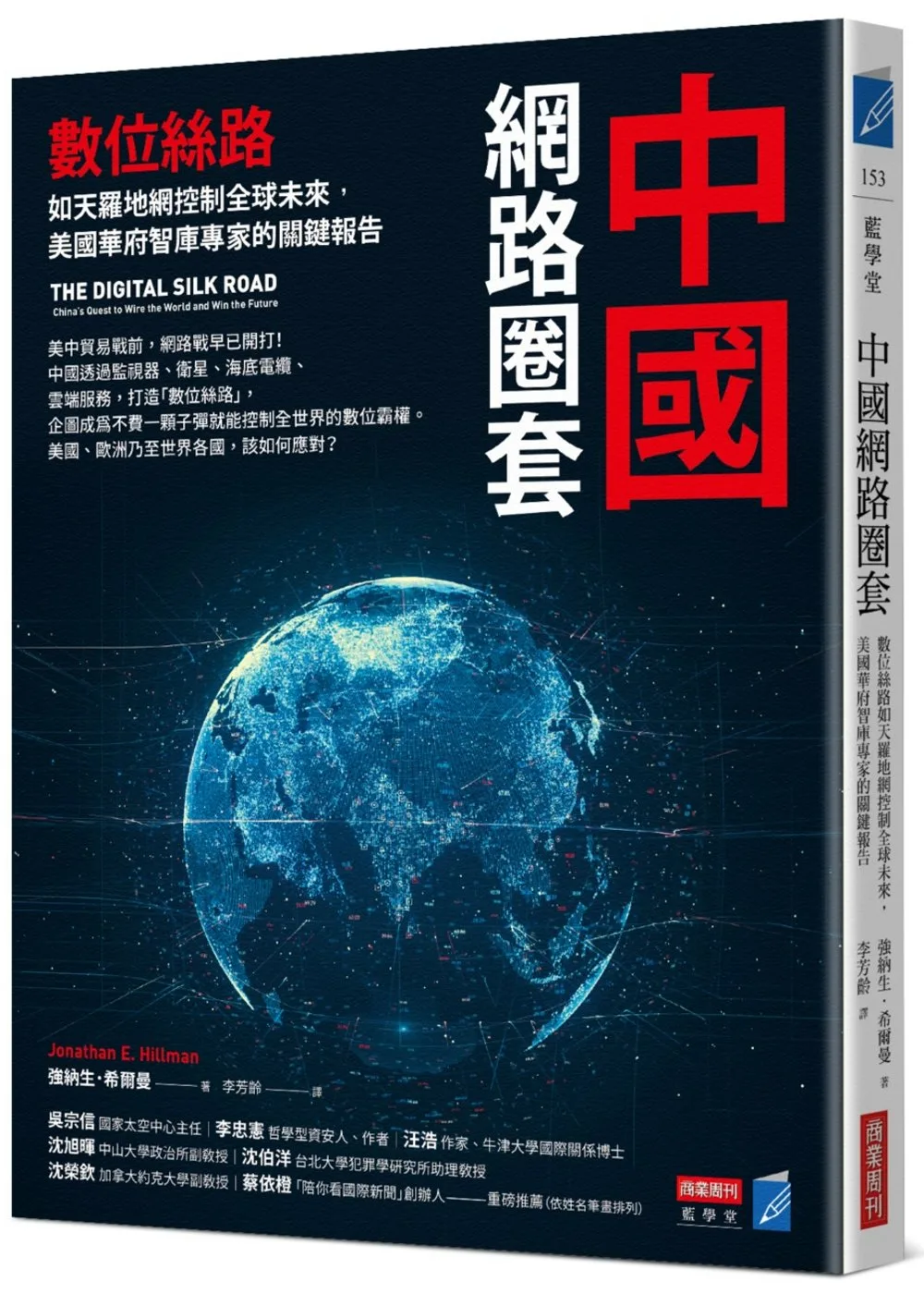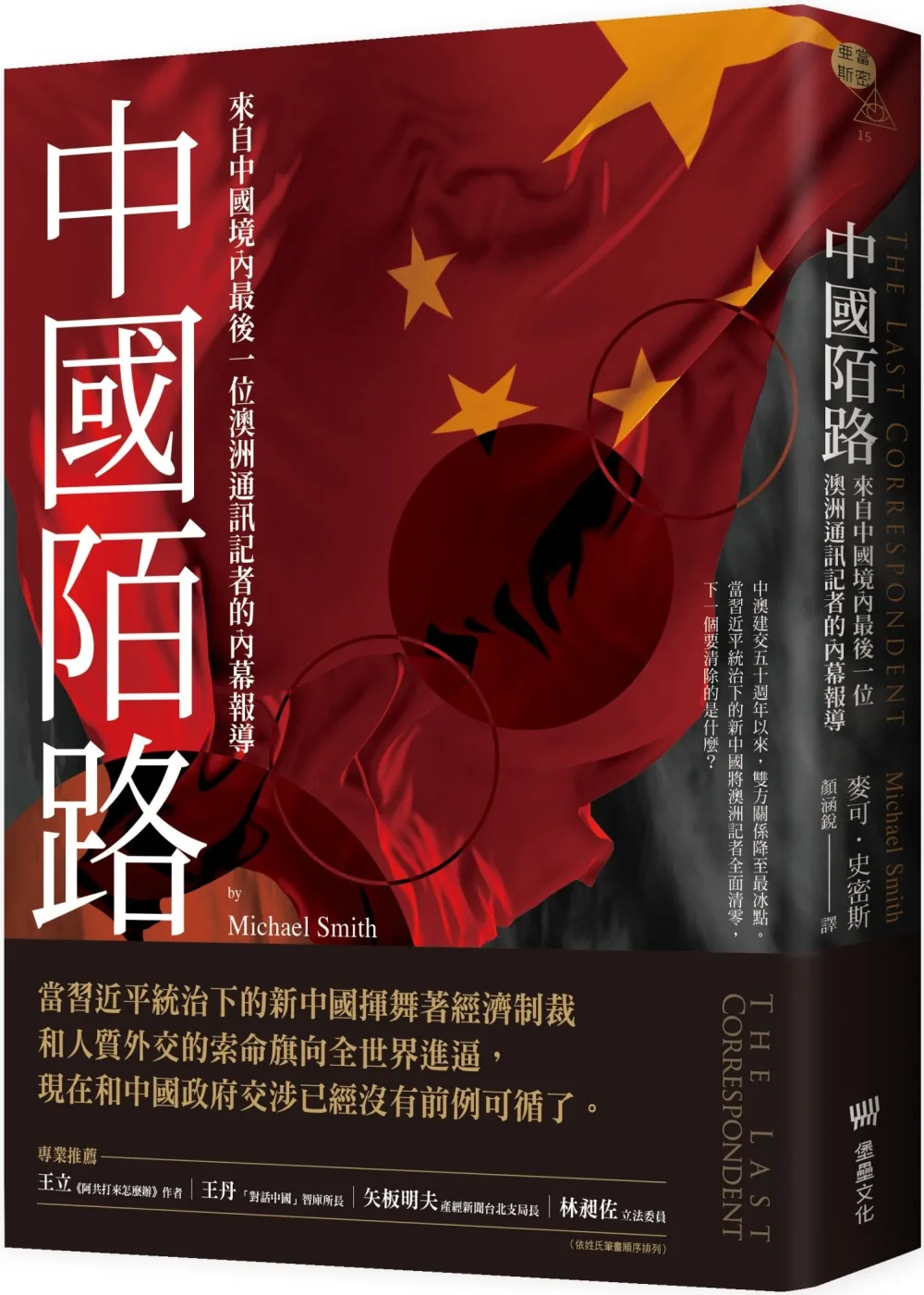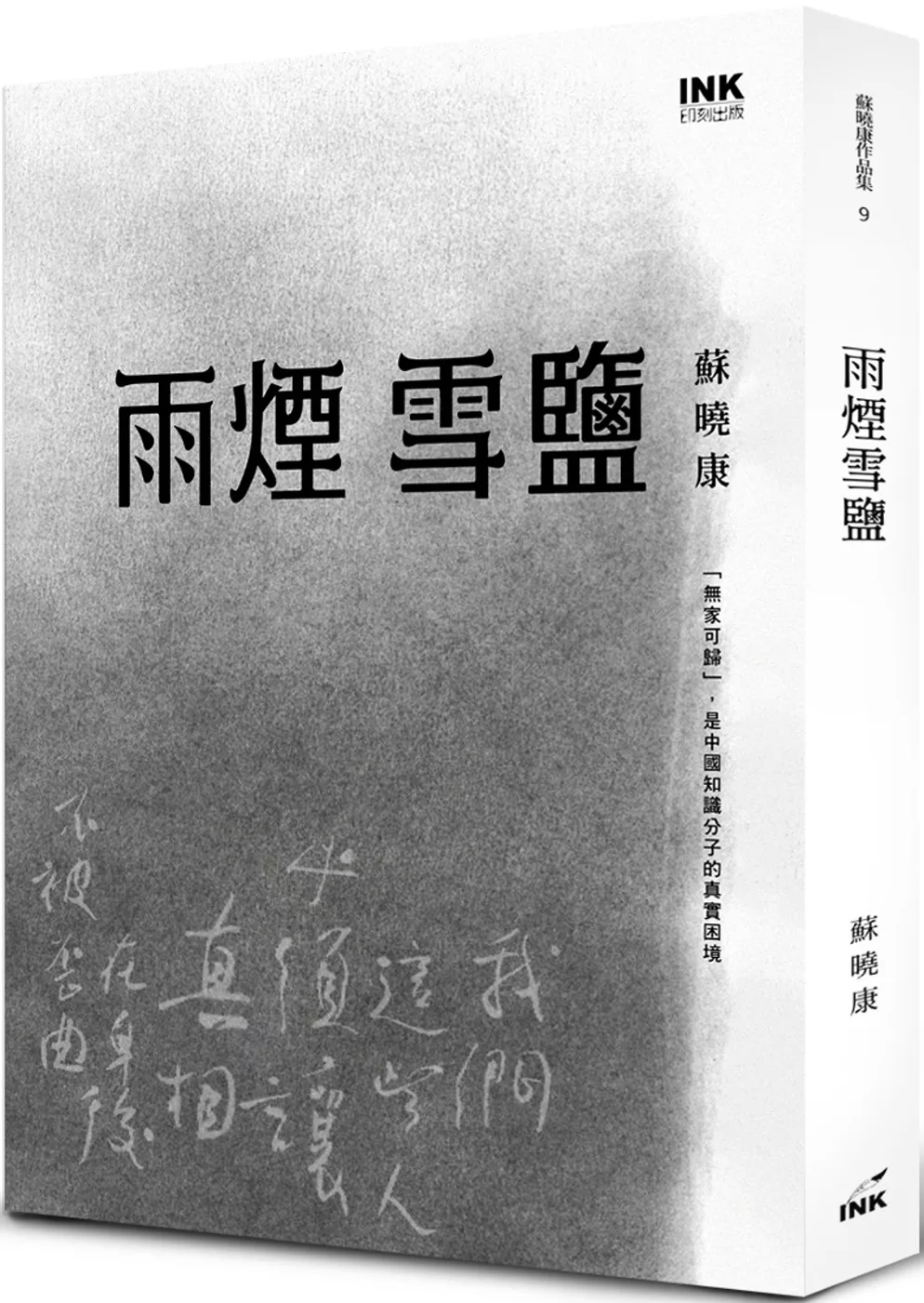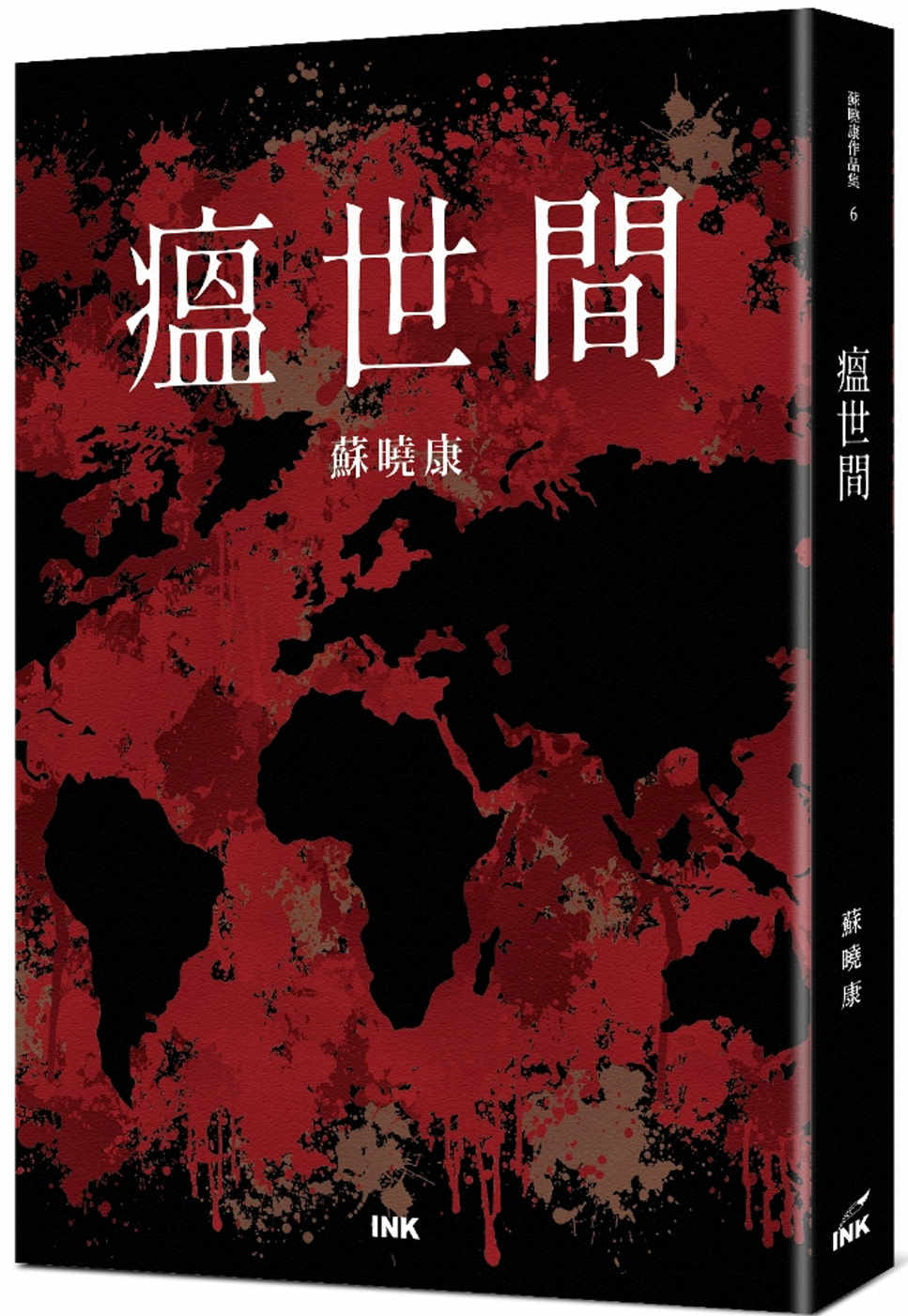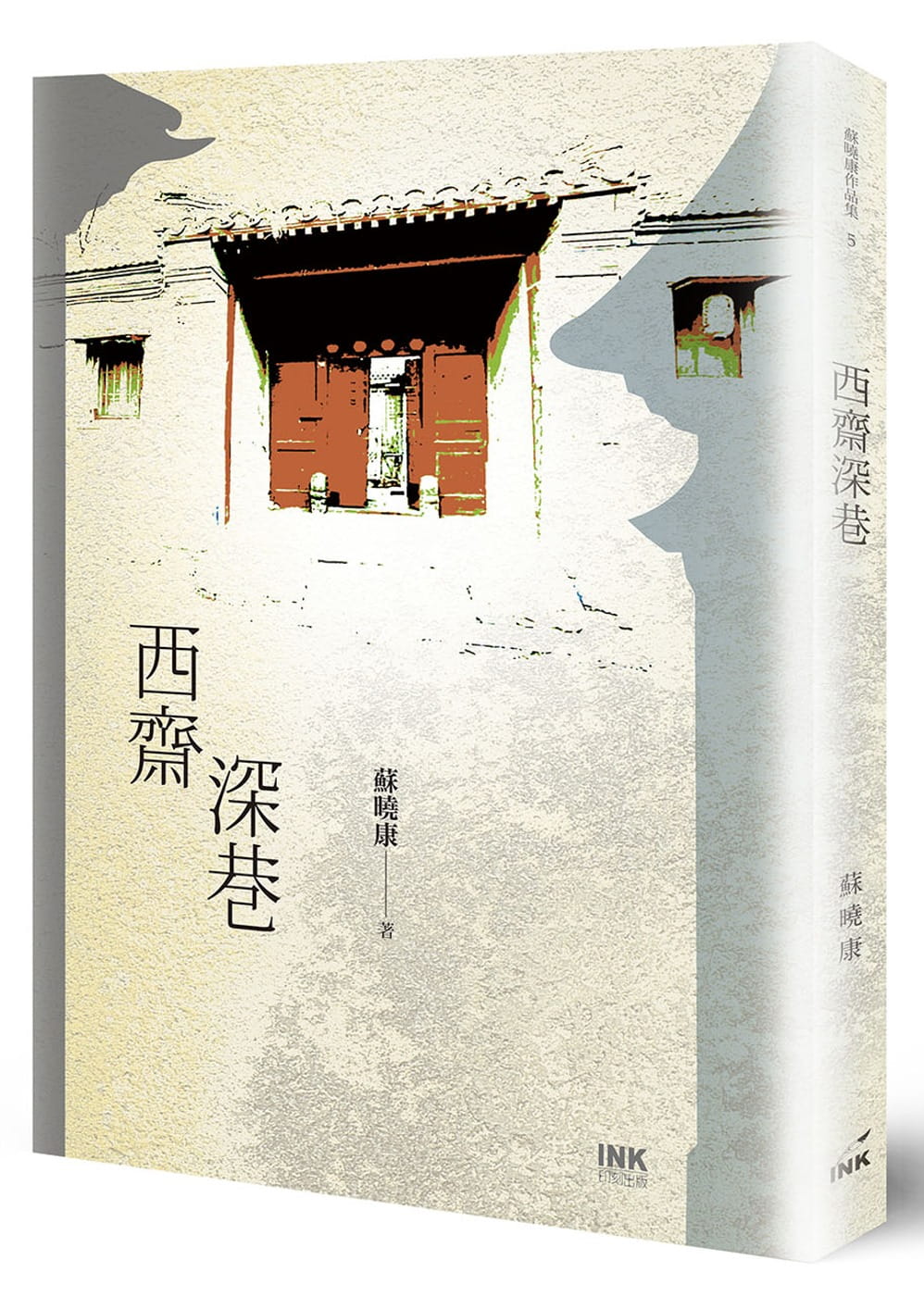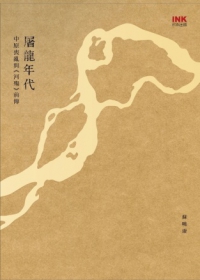代序
魔幻三十年
鐵蹄子,踏爛百姓肉皮子,
炕頭捲去破席子,磨道牽去毛驢子。--東北民歌〈白吃飽〉
一九八九年五月裡,曾有異人指點我:天有異象,血光之災就在眼前。我似信非信,沒有當真,依舊我行我素。不料,六月初果然京師屠戮,血染長街。此一巨變,不但我從此去國他鄉,餘生漂泊,更兼世態跌宕,歷史翻轉,也是一路不回頭了。由此雖世道仍迷茫不可知,我猶信冥冥中會有神祕預兆示人。
近三十年孤寂偷生,窺覷世態於河漢微淺之際,臨摹感懷於星雲無語之時,每每瞠目造化之乖張,驚歎世道之冥迷,卻綿延十幾年,盤桓紙筆與鍵盤之間,幾度存廢,欲罷不能,幸得數十萬言,滿紙荒唐,不知所云,仍不失為零珠碎玉,所思所想,若編纂成冊,未知不是一本奇書?
我們經歷的,是魔幻的三十年,魔幻又無非三件大事:一、大屠殺與經濟起飛;二、民族主義與中國霸權;三、國際綏靖與歐美衰退。回眸所來之徑,可曾有人預知期間迷思:
一、中國崛起的訣竅
二、西方民主制包裹的利己內核
三、中共體制「馬基維利」化的脈絡
現代西方雖有十八世紀的突破,卻依舊仰慕中國之文明悠久;華夏自古「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原是沒有某種想像的維度;中外近現代史上,不敢說幾無人傑窺見東方的大災難,有之亦人微言輕,卻有一個大音似希的預言,竟然來自世界屋脊之上。
那裡有位頂級喇嘛,那時他還年輕,曾慧眼獨識所謂「五○年紅光異象」。他說,當時天空有一陣接一陣的轟隆聲相繼而起,一道怪異的紅光,從爆破聲源方向的天空射出。整個西藏,東到四百英里遠的昌都,西南方三百英里外的薩迦,幾乎全藏的人們,都看到這個異象。多年後他詮釋道:那次不只是一場地震,而是一個預兆,這種異象,超乎科學,屬於某些真正神祕的領域。
預兆什麼?原來站在世界屋脊的這位雲端高僧,俯瞰東亞,乃至整個歐亞大陸板塊,窺見其大部分地域將陷入殺人如麻的世紀之禍,只是這雲端的神祕預言,令青藏高原之下的所有家國族群統統惘然不知,如南麓印度支那半島,古稱安南交趾一帶,六○年代墜入人間地獄,戰爭之後留下一片滿目瘡痍的土地,一百萬孤兒、二百萬寡婦、五十萬殘疾人。高棉為禍最烈,竟有一個現代魔王波布(波爾布特),幾年之內殺掉三百萬人,境內骷髏遍野;赤柬統治時期,四分之一的國民,死於木棒爆頭之類的酷刑,大量逃出來的高棉人,都患有衰弱憂鬱症、創傷壓力症、睡癱、家暴、過敏恐慌、失語、凡事冷漠龜縮,自殘、心理病延禍三代人。
這個世界屋脊,終於也被「鐵鳥」鐵蹄蹂躪、信眾不惜自焚抗爭;毗鄰的西域回疆更難逃厄運,竟被軍管以「集中營」統治;整個東亞,綿延到中南半島,中國、朝鮮、越南的現代史,皆達至文明解體之境,暴虐史無前例。喜馬拉雅北麓的膏粱之地,億萬漢人膜拜「紅太陽」並聽其「關門殺人」四千萬,又任憑「設計師」屠城掠奪豪取,再容忍三代後嗣糜爛華夏葬送山河,以至於生靈賤如草芥,存亡已成兒戲,沉淪失去底線。一個徹頭徹尾的魔幻之境,全民噤聲竟無人追問:世道天良何至於此?
明末顧炎武作《日知錄》,分辨「天下」「國家」為二者:「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所以六○年「大饑荒」那會兒,中國就「亡天下」了,當年連劉少奇都對毛澤東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中國三十年「民族主義」高歌猛進,八○後以降還知道這點歷史的已是鳳毛麟角。
顧炎武之「亡天下」,還有更深一層,他是在講人倫防線、文明底線的大問題,他說朝代興亡更替,是無所謂的小事,但是假如一個民族突破了人倫防線,它就死了。中國的文革,是一場「多數人的暴政」,最後出現了霍布斯所說的「人與人的關係」倒退到「狼與狼的關係」的蠻荒境地;到這種境地,還能限制暴行的,只剩下每個人自己心裡的人倫防線。我們今天才驚訝地發現,那時的大多數中國人心裡根本沒有這條防線。這就是文革後巴金老人萬分痛苦的一件事,他問自己:孩子們怎麼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狼?
人倫防線是一個文明最原始的成果,也是它最後的底線。這條防線在中國文明中是由儒家經歷幾千年逐漸建構起來的,卻在近百年裡被輕而易舉摧毀了。摧毀的明證就是文革;「吃人」更赤裸裸地發生在廣西文革中。我們無法確定,究竟是中國傳統的人倫防線,不能抵禦如此殘酷的政治環境,還是它早已不存在?可以確定的是,中國人除了這條傳統的人倫防線,再沒有其他東西,如西方文明中人與基督的溝通。
中土的滅頂之災,早在上個世紀初就有沉痛預兆,即王國維沉昆明湖之殉難,此文化中人勘破大難臨頭,而億萬眾生尚沉睡不醒。陳寅恪詮釋道:「凡一種文化,值其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陳寅恪悲唱「巨劫奇變」,尚在五○年代,又幾十年逝去,中國才真真「劫盡變窮」,乃是穿越了一個「全球化」、攀附了一個「經濟奇蹟」、搭上了大江山川、賠上了千性萬命。尤其後三十年,中國的這個極權制度,穿越三道生死關隘─「六四」屠殺合法性危機、市場經濟、互聯網社會,不但毫髮無損,反而被淬煉得前所未有的強大與邪惡,以致近現代以來西方學界積累的「專制集權」知識,皆無力解釋這個「東方不敗」:它如何可以一場飢餓接一場文革,然後要救「亡黨」,卻再來一場大屠殺,便迎來二十年經濟起飛、貧富崩裂、階級對立和道德滑坡,有誰寫過這三十年的狂瀾、污濁、驚悸、血淚?又有誰梳理過思潮風俗、世態百媚、幽史穢聞、精靈魍魎?更有誰追問過它的肇始?
這已經亡掉的中國,還在「劫盡變窮」,卻直接銜接到「歲月靜好」,在一個油膩膩的「盛世」裡,連「思想也變成內褲」,加上不准「妄議」,巨嬰們把順口溜玩到了「後現代」水準,還人人具備了「馬桶精神,按一下,什麼都乾淨了」;孩子們也「變不成狼了」,因為「喝水不達標吃食品有毒,蓋學校危房,校車沒錢,教育沒錢,醫保沒錢,社保沒錢,環保沒錢」……… 中國「亡天下」之後,再添「魔幻」歲月,莫非「鬼推磨」耶?
這場劫難的機制,又跟中華民族的近代恥辱,來了個徹底顛倒:舊式堅船利炮的西洋,數點著人權紀錄來簽訂單;往昔「反帝仇外」的黨中央,每一屆「核心」都是第一站去華盛頓報到;士大夫兩千年的浩然之氣,已愀然滅絕,神州好似被一個「外來政權」統治,一半靠的是知識界自動繳械;歐美貪婪中國廉價勞力,不惜讓渡諸多價值和信守,乃至昏昏然扶持了一個「韜光養晦」的極權對手,悔之晚矣。
還有北鄰的蘇俄。當年毛澤東要從農民嘴裡摳下糧食來,去跟史達林交換一個「工業化」,不惜中國餓死幾千萬。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都是那邊「一聲炮響」輸送過來的,而今卻顛倒了,二○○六年普丁作「國情咨文」稱俄羅斯面臨人口減少的危機,一是大量移民,二是嬰兒出生死亡率高,兩者似乎都是某種信號:俄羅斯大地經過七十年暴政,已成一不適宜人類居住地,只剩下豐富的石油,挖來賣給東南穿金戴銀的小兄弟。
在世紀末的今天,中國的精神貧困更遠在物質貧困之上,這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一九九四年以研究歐洲中古文化史著名的俄國史學家古烈維奇(Aaron I. Gurevich)在談到蘇聯解體後俄國的一般思想狀態時指出:官方意識形態長期壓抑下俄國民間文化的多層積澱,在極權體制崩潰之後,突然爆發了出來。無論是政客、史學家、學人對此都毫無心理準備。與此同時,數十年來宰制了史學思維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完全失去了信用,留下來的則是一片「哲學空白」(philosophical void)。而填補這一大片空白的便是神祕主義、「怪力亂神」(occultism),以至侵略性的沙文主義等等現成的東西。
幾年前我初讀此文便印象很深,今天我更感到中國精神的貧困還遠在俄國之上,因為俄國在極權時代仍存在著東正教的根荄,更重要的是文學的反抗傳統始終不絕如縷,有一些作家和詩人即使在史達林統治下也不肯在思想上作一絲一毫的妥協。我們只要一讀伯林(Isaiah Berlin)的那篇訪談錄便可見其大概。今天中國一般人民的精神飢渴所達到的深度和廣度,真可謂史無前例。
上引史學家余英時所言,他在上個世紀就曾「發生一個很深的感慨」,轉而不啻又成他的預言,哲學空白、神祕主義、怪力亂神、侵略性沙文主義,這些「精神貧困」,都在中國一一降臨了。
一個突然崛起的經濟大國,又獲得升級版集權方式,乃是二十世紀都未曾出現過的奇觀,然而這恰是中國之亡。余英時的第二層意思,又比較中俄知識分子,中國「士大夫」亡得更徹底。這個階層在古代輕易不向暴君低頭,哪怕千刀萬剮,而四九後最著名的大知識分子們,群體性向現代極權臣服,並以其知識的權威協助極權,彷彿整個中國文明死去,坊間過去有「京城四大不要臉」之謂,後來又釀成「盛世」裡文人名流「賽著不要臉」之競爭,令這半個多世紀,極權得以施行人文大殺,何嘗不是一部中國讀書人的恥辱史?
一年前資中筠與友人書稱:「京津滬三大城市,可謂烈火烹油之勢,錦繡繁華之鄉」,令她絕望!若論這個民族至今大夢不醒,還在明末清末,並不真實,民間無社會,底層求生活,令吃瓜大眾尚無政治含義;經濟起飛雖創造了一個富裕的中產階級,眼下卻只有外逃衝動;知識階層被徹底邊緣化,在金錢至上利益驅動的社會裡,不僅是權力的婢女,也是娛樂的丫頭,其政治上的含義甚至是負面的;黨內「改革成分」缺氧化、臨終化、僵化,比知識階層更加遁形;政治上的真實是,人大代表們居然是百分之百擁護專制。中國已經到了世事不堪聞問的地步,西洋也在衰退,世道黯然之下,梳理這三十年,得一部《鬼推磨》,或為一個大哉問,以饗讀者。
?
二○一九年八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