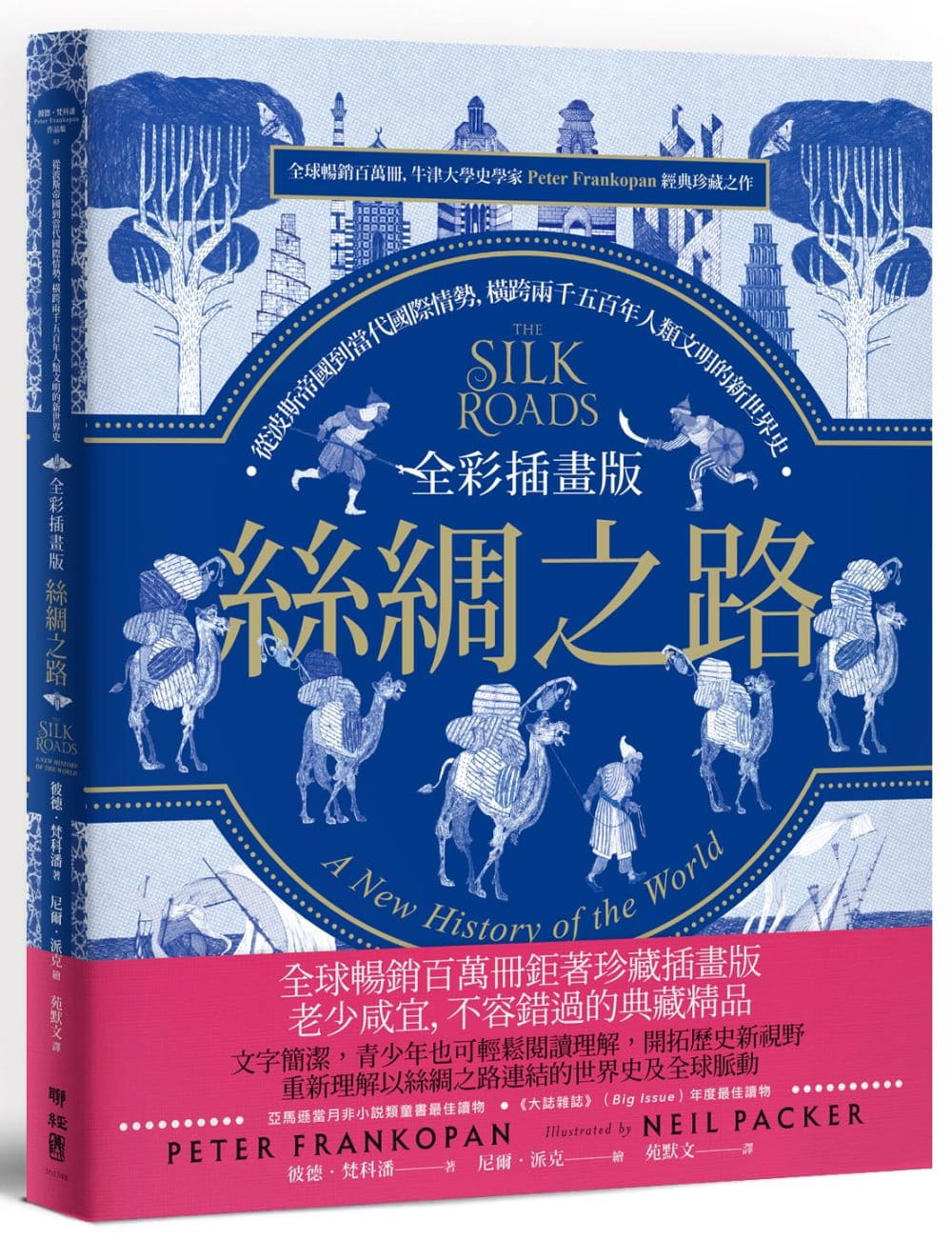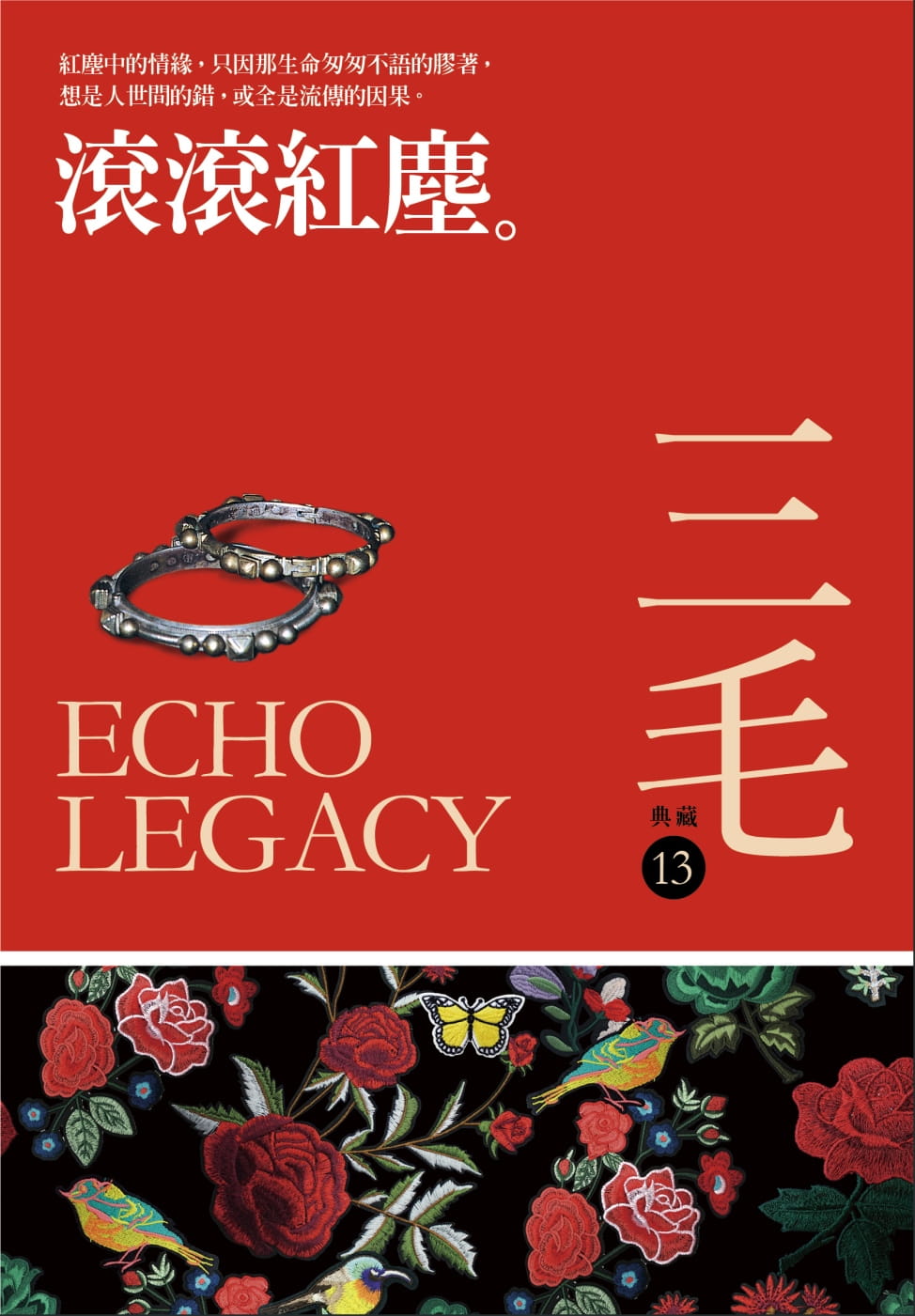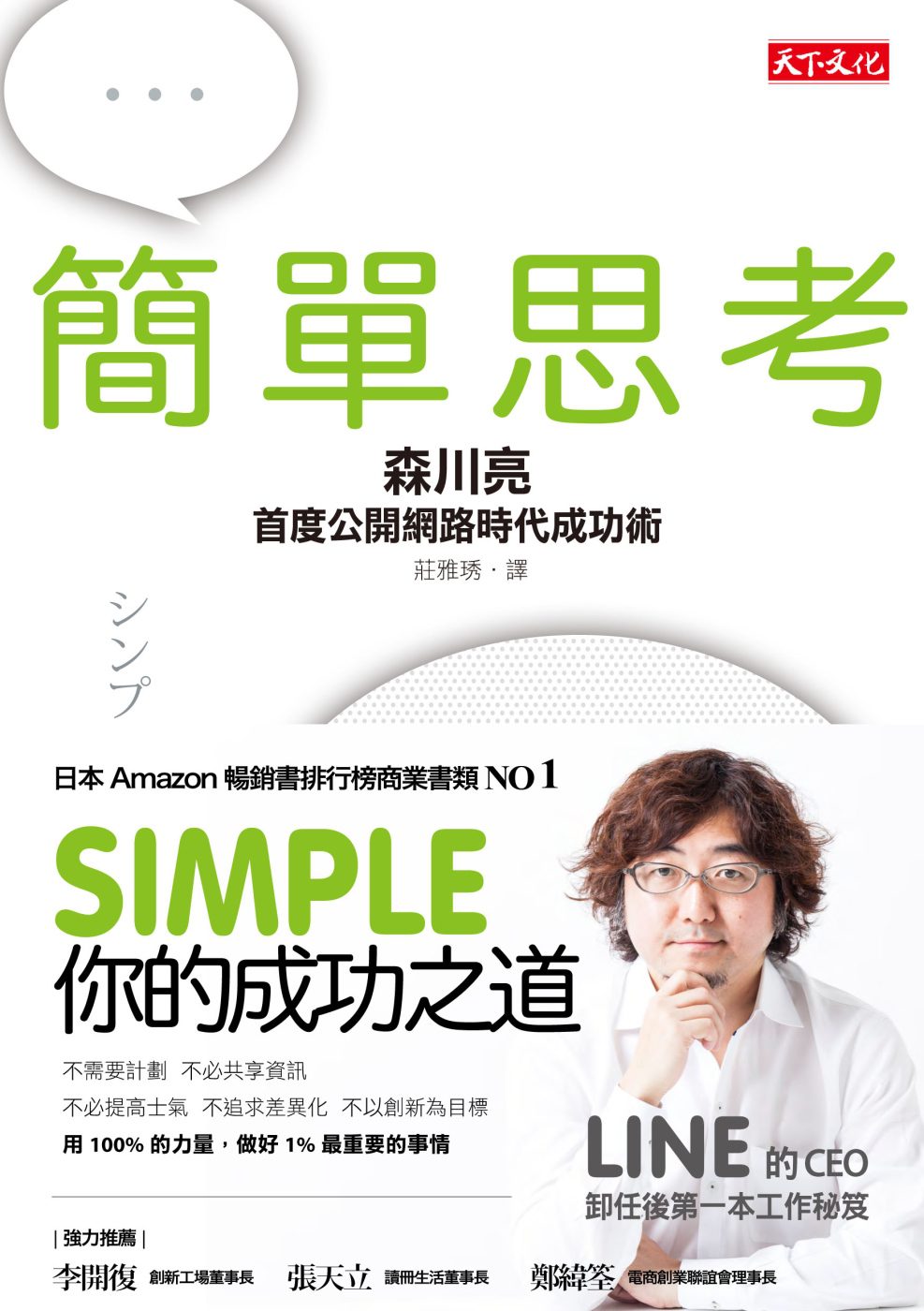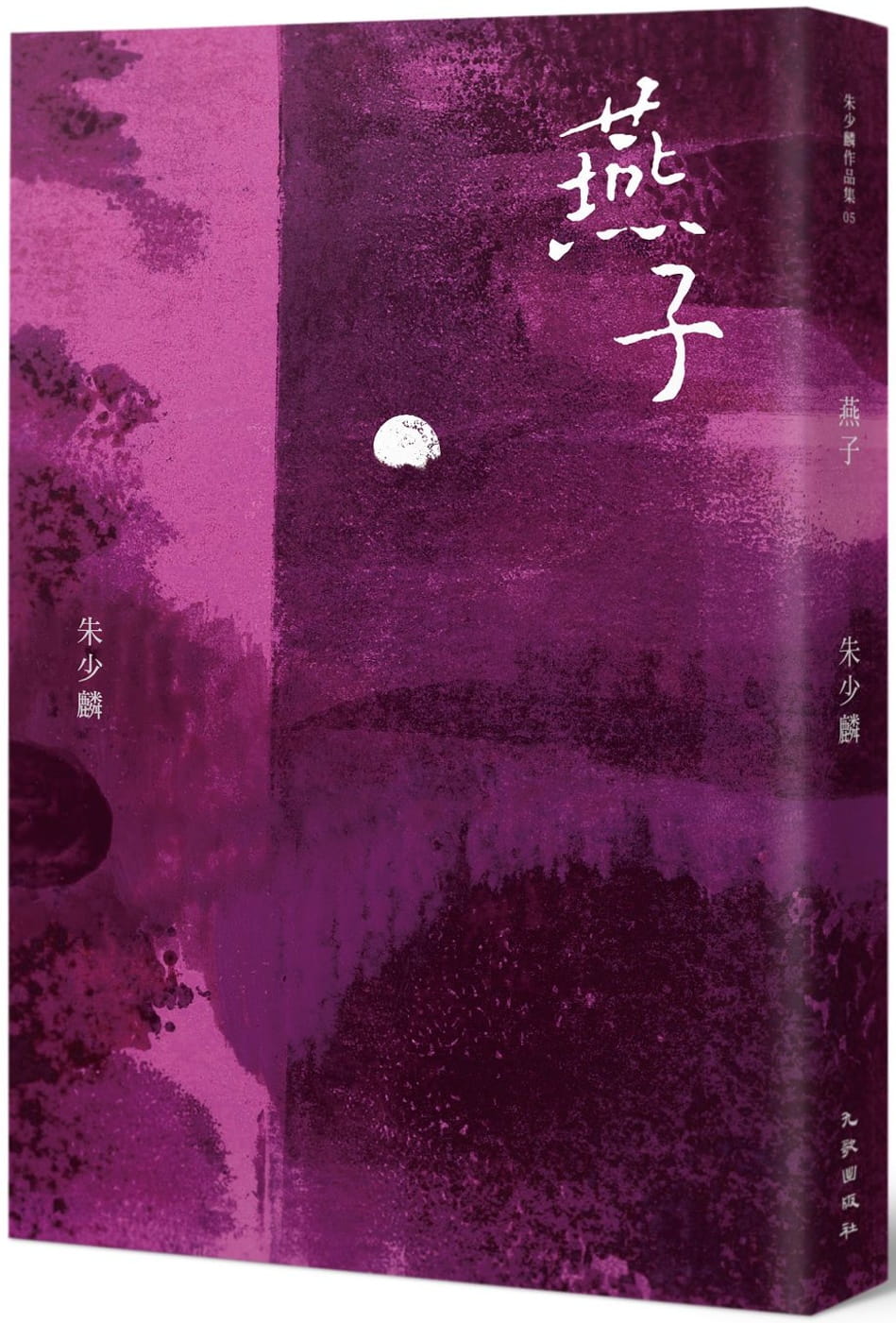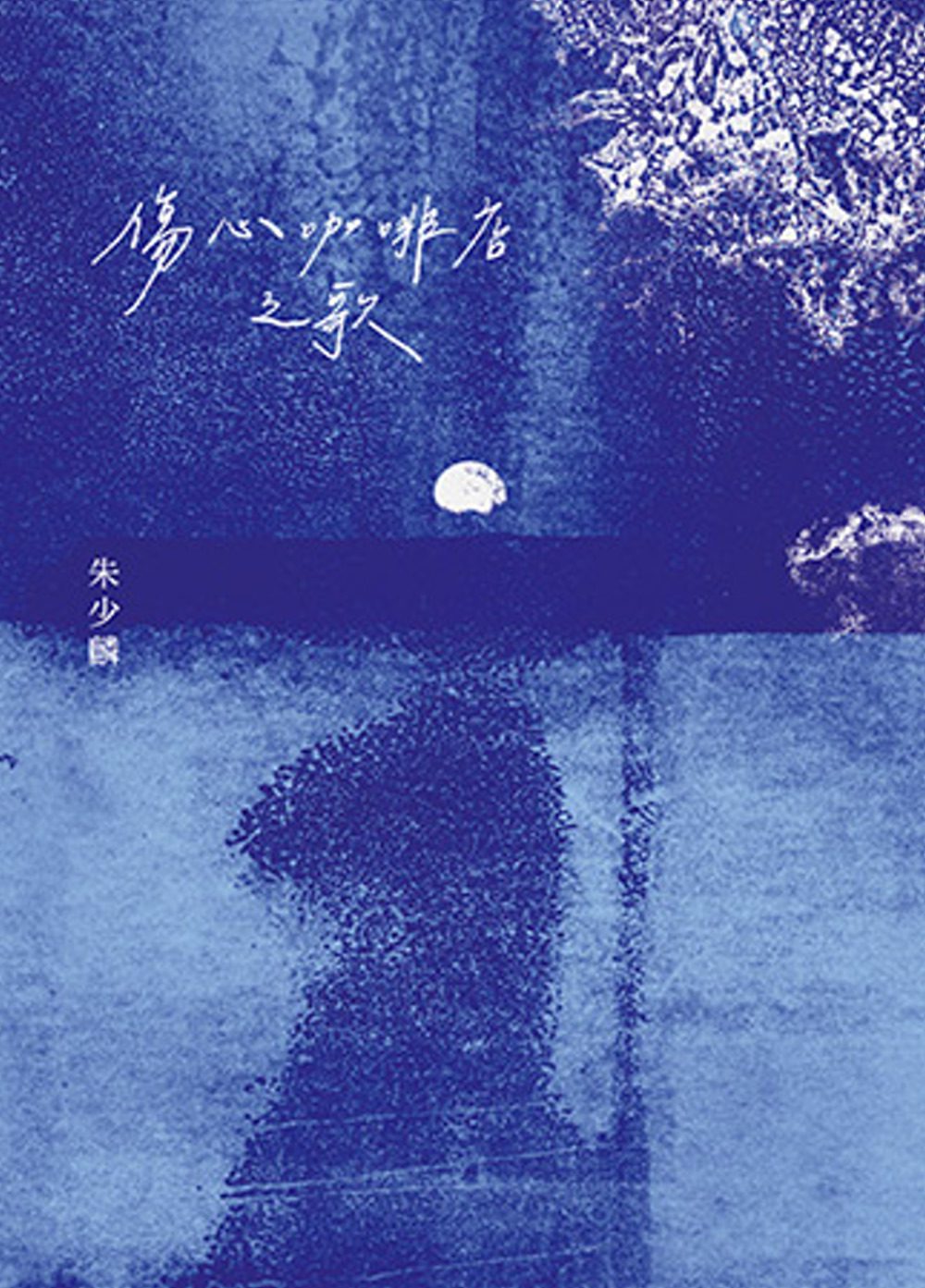推薦序
導從人類最古老的傳染病談起……
劉紹華(人類學家,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隔離 樂園》是一本主題稀罕的好看故事書,有著青少年對大人和周遭環境的細膩觀察,也充滿探索熱帶世界和大海的冒險精神。更特別的是,這本故事書具有科普意涵,以太平洋菲律賓島嶼上的麻風病為切入點,講述一個很古老、卻能帶領我們認識當前新冠病毒疫情世界的傳染病。
「我發現大人常常看見事情的陰暗面。」
書中的小主人翁亞米,這樣形容她得了麻風而受盡奚落排斥的母親,那位對麻風病人不友善的修女,還有那個細心殺死美麗蝴蝶好把牠們製成標本的病態科學家。
在亞米的心裡,可怕的並不是麻風病人,而是沒有生病的人對於疾病的無知與莫名恐懼,以及他們對待病人的各種不人道反應。
本來,像亞米一樣的青少年,不會在這樣的年紀就看見疾病的痛苦與歧視。就像今天生活在臺灣的多數青少年,因為很少經歷或觀察過嚴重的傳染病,通常就不大注意人們對於疾病的恐懼和汙名。
不過,這樣的情形,最近應該起了一些變化。
二○二○年橫掃全球的新冠病毒,讓所有人,包括青少年在內,或多或少都體會了傳染病的重大負面影響。
新冠病毒讓所有人都看見了莫名傳染病對於身體與生命的威脅;看見了社會對於被感染者的恐懼、歧視與排斥;看見了病毒可能從動物身上輾轉傳給人類的事實。
看見這些現象,對於正值青少年的你來說,可能是全新的認識。不過,我們從人類的傳染病與社會史來看,這些現象其實已經存在很久了,久到超越了你所知道的歷史。
麻風,就是人類最古老的傳染病,也是由動物輾轉傳給人類的最久遠的傳染病。
造成麻風病的細菌,最早可以追溯到兩千萬年前的非洲大陸,那是人類的起源地。大約十萬年前,當人類的始祖遠離非洲時,這個細菌也就隨著人類的遷徙傳到世界各地。之後,不論是在《聖經》還是《論語》裡,在世界各地的古籍中,你都可能找到關於這個傳染病的紀錄:被感染者的處境、社會的歧視與排斥,或者如耶穌和孔子一樣的聖人對於被感染者的憐憫哀嘆。
《隔離 樂園》這本書,透過小主人翁亞米,講述的則是二十世紀初菲律賓麻風病人所遭遇的故事。因為那是一個世紀前的歷史,所以書裡的用字是「痲瘋病」。但是,今天,全世界都已經認識到了人類曾經對於這個疾病的誤解和莫名恐懼,也反省了以往對於病人的歧視和不人道對待。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痲瘋」(leprosy)這個字,世界各地就陸陸續續的不再使用了。如今,即使仍使用中文提到「痲瘋」時,也都去病化了,改為「麻風」兩個字。
這個人類最古老的疾病,今天的正式名稱叫做「漢生病」(Hansen’s disease)。國際醫學界採用當年發現麻風桿菌的挪威醫師漢生(G. H. Armauer Hansen, 1841-1912)的名字,作為疾病的科學命名。
用「漢生病」取代「痲瘋病」,正是因為國際社會已在反省,人們對於疾病名稱和汙名的關聯應該要更為謹慎,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歧視和排斥。對於新冠病毒引發的肺炎疫情,我們也應該記取麻風病帶給人類的深刻教訓。
書中的主人翁亞米,因為沒有感染麻風,被迫與她的娜娜(母親)塔拉分開,母親留在隔離麻風病人的庫利昂島上,她則被送到另一個科隆島上的孤兒院。亞米和母親已經生活在一起十二年了,並沒有受到感染,但是母女倆還是被迫分離,而且不准待在同一個島上,彼此探望的機會渺茫。為此,亞米和朋友一起冒險造舟渡海,開展了好多故事。
其實,醫學知識後來已經證明,麻風是很不容易傳染的疾病。這個非常古老的麻風桿菌,它的感染力早已在漫長的演化中式微了,所以絕大多數的人都擁有免疫力。也就是說,即使被感染了,大概也只有百分之五的感染者會發病,而且不難醫治。
只是,科學的醫學知識,不一定能夠改變人們的既定偏見,還是有很多人不必要的害怕、歧視或排斥麻風的感染者。
就像在故事書裡提到的許多人,像是那位不友善的修女或病態的蝴蝶收藏家,他們很害怕觸碰病人,有病人在的地方就不敢大口呼吸,以為麻風病人一定是面容毀損、手足斷缺。其實,這些都是誤解。
重症麻風患者最大的生活困擾之一,就是神經可能受損,而失去最重要的自我保護機制,也就是痛覺。一旦如此,患者即使被燙傷、甚至夜半睡覺時被老鼠咬掉手指、鼻子,都可能沒有知覺。一般人因為常見患者身體殘缺,便誤以為罹患麻風就會造成缺手斷足,實際上並非如此。
當人無法感受到疼痛,就不會知道要迴避傷害。痛覺,其實是造物主送給人類的寶貴禮物。只是我們很少珍惜它,以為疼痛不是好事。
亞米長大後,追尋父母生病前的回憶,而成為一位意想不到的專家。亞米的故事,不一定只是存在故事書裡的童話。
你聽過甘地嗎?一位全球知名的印度聖人。甘地很關心麻風病人。一九九五年,印度政府設立了「甘地和平獎」,很多影響世界的重要人物都曾榮獲這個獎項,包括不少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二○一五年,一位像亞米一樣的麻風病人後代,菲律賓的阿圖洛醫師(Dr. Arturo Cunanan),獲得了「甘地和平獎」的榮譽。
阿圖洛醫師正是在庫利昂「隔離島」上長大的孩子。他立志讀書,成為世界上最了解麻風病的醫學專家之一,如今擔任庫利昂島上醫院的首席醫師。
我見過阿圖洛醫師,他有著一張看盡人間苦難後昇華而成的笑臉,溫暖、親切、悲憫,充滿了為麻風病人服務的熱血與行動力。知道他的成長背景後,我更能理解他的眼神與微笑,為何那麼令人感到溫暖與信賴。
在阿圖洛醫師和許多人的努力下,如今的庫利昂島,非常美麗,保留了許多古蹟和值得世人反省的歷史。
「有些地方你不會想去」,這本故事書是這樣開始的。
但是,今天,那些原本很多人不會想去的地方,你可能會有興趣拜訪了呢。如果一個社會已經反省了過去對於疾病的不必要恐懼、對於患者的不人道對待,那麼,留存下來的「隔離島」或「麻風村」裡,除了可能有些身障但笑容仍掛在臉上的老人家外,還有就像書裡描寫的「樹上長滿水果」的幽靜風景。
你看過宮崎駿的卡通《魔法公主》嗎?國際大導演在構思這個動畫故事時,經常在住家附近的「多摩全生園」散步,那是以前日本隔離麻風病人的地方。當年,由於人們對於麻風的誤解,這裡除了病人和醫護人員之外,人跡罕至,所以大樹成林,風景優美,成為《魔法公主》裡的森林場景。
許多以前隔離麻風患者的地方,如今都有類似的宜人風景,大樹、自然、幽靜。臺北也有,叫做「樂生療養院」,就在捷運新莊線的「迴龍�樂生」站,當年也是隔離麻風病人的偏僻地方,充滿了傷心與動人的故事。
有機會,你可以去樂生拜訪老人家。如今的他們,可能在門前種上花草蔬菜,也可能騎著電動摩托車,倏忽出沒在院區裡蜿蜒的坡路上。看見他們,記得打招呼,他們會給你一個微笑或招手,甚至可能幫助你認識疾病和社會的複雜糾結,一個屬於台灣隔離島的歷史故事。
推薦序
在充滿被遺棄者的島上,也有光輝的人性
李博研(神奇海獅,歷史作家)
一段故事之所以精采,可能因為它深刻的刻畫了人性,也讓讀者反思自己:如果我是書中角色呢?我也會這樣做嗎?《隔離 樂園》就是這樣的故事:作為當權者,為了拯救多數人的性命,我會選擇犧牲少數人嗎?為了消滅疾病,我會把病人全都隔離到一座孤島上,造成家破人亡嗎?更讓我震驚的是,這段故事竟然有真實的歷史架構。
《隔離 樂園》場景位於菲律賓中部的庫利昂島(Culion),這裡擁有美到難以言喻的景色:蔚藍的天空與海幾乎交融在一起,只有遠方雪白的雨雲分隔了兩者。這座島如今已經成為菲律賓著名的觀光景點,觀光客們不遠千里而來,就為了觀看海下壯觀的珊瑚礁和魚群。然而許多人並不知道,這個遺世獨立的人間仙境,上個世紀竟然是全世界最大的痲瘋病隔離區。
在西方世界裡,痲瘋病(leprosy,現代稱為漢生病)一直擁有特殊的地位。染上這種疾病後可能造成失明、耳聾,甚至是鼻梁塌陷、獅面、四肢潰爛等毀容的症狀,所以在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裡,痲瘋病被認定為「不潔淨」的。
在中古基督教世界觀中,有幾種方式可以治療痲瘋病(然而,聖經的痲瘋病不完全等同現代意義的痲瘋病,但這並非本文重點,故不討論)。第一種方式,就是遇上耶穌基督本人。馬太福音》、《馬可福音》與《路加福音》都曾記載:有一名染上痲瘋病的患者去找耶穌,說:「主若肯,必能叫我潔淨了。」
「我肯,你潔淨了吧!」耶穌摸了患者說道。接著,患者的病馬上就消失了。
就因為耶穌基督本人擁有治療的能力,之後的教皇、國王只要宣稱自己是受神之命統治世界的,都要有點救死扶傷的本領。從十世紀開始,英、法就開始流傳一種「國王神蹟」──只要被國王觸碰,病患就能夠不藥而癒。
然而,這些觸碰畢竟不是真正的治療。過去只有一種方法能夠有效防堵這種疾病,就是隔離。在《舊約聖經》裡,一旦確診了痲瘋病,他就必須「獨居營外」。到了中世紀,歐洲各地也成立許多痲瘋病院收養這些「活死人」。而最大的痲瘋隔離區,就是小說裡的庫利昂島。
二十世紀初,美國從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賓時,總共大約有四千名痲瘋病患者。隨著病患人數迅速增長,美國發現只有隔離一途,才能澈底遏止菲律賓境內的痲瘋病繼續蔓延。因此在一九○六年,美國選定原本就居住許多痲瘋病患的庫利昂島,建造了全球最大的痲瘋病隔離區。這座島上有超過四百棟建築,包括一個戲院、一所學校、一間市政廳,患者甚至擁有自己組建的法庭和貨幣。
小說描述的,就是這段幾乎已被世人遺忘的歷史。主人翁亞米的母親是痲瘋病患者,在懷孕期間被送到庫利昂島上。所以打從出生起,亞米從來不曾離開過這座美麗島嶼。直到有一天來了一名政府代表,帶了一紙命令,未患病的亞米與患病的母親就此分離:母親留在庫利昂隔離區,亞米則被送往遠方的科隆島孤兒院。
在分離之後,亞米才切身了解到自己所愛的家鄉,是外界眼中的「萬物盡頭之島」,是外人絕對不想靠近的活死人禁區!儘管亞米與其他庫利昂島的小孩已經接受專業的醫學檢驗,確認沒有感染,卻仍然被孤兒院的孩子認為是疾病的化身。其他小孩紛紛耳語,不能靠近他們、不要使用同樣的水源,最好不要呼吸同一種空氣!
在故事中,政府代表薩莫拉先生是一個近乎偏執的專業工作者。他毫不掩飾對痲瘋病患者的偏見,為了維護自己的潔淨,他會洗手洗到皮膚破皮;他唯一的愛好是搜集蝴蝶標本,在亞米的眼中,這項嗜好也顯露了他對生命的看法:他培育、呵護自己的蝴蝶,不讓牠們受到任何一點點風吹雨打,只是為了在最後把牠們殺掉,好獲得一個完美無瑕的蝴蝶標本。
隨著故事的進行,讀者會看見作者傳達的訊息:人會因為種族、財富、外貌、疾病等條件,將人群區分為「我們」與「他們」。一旦將某個族群標籤化了以後,種種的偏見、歧視也就隨之誕生。在這種劃分的過程裡,人們往往忘記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你始終擁有一個選擇──打破藩籬。那種區隔「我們」與「他們」的東西看似是一座高山,但當你走近,可能會發現那其實只是一層薄膜。我們會在接近彼此的過程中,在他們身上看見與自己相似的歡喜與憂傷。
作者的話
當虛構的小說以事實作為核心,故事有時能夠呈現出最理想的內容。菲律賓的庫利昂是一座真實存在的島嶼。在西元一九○六年至一九九八年間,它確實成為了全世界最大的痲瘋病隔離區(使用「痲瘋病」這個詞令我反感,因為當我與許多居住在這類隔離區的人交談時,他們都視為禁忌,如今普遍稱漢生病)。
在一九八○年代研發出藥物並廣泛使用前,漢生病曾經在亞洲、非洲和歐洲傳播了數千年,至今仍有數十萬的病例,不過大多已經治癒。漢生病受到普遍且嚴重的汙名化,經常與骯髒和罪惡連結在一起,但事實上,它只是單純的細菌感染,而且傳染力不高。
光是一九○六年到一九一○年,就有五千三百○三名男人、女人、小孩被送到庫利昂島。強制施行的移居政策造成無數的天倫悲劇──每個人都有自己原本的生活和家庭,還有想念他們的人。因此,我決定寫一個故事,透過亞米──被帶離母親身邊,想找到回家路的女孩──的眼睛,引領讀者身歷那樣的現場。
如果能在完全的事實之中找到歪斜的縫隙,適度摻入一些想像力,有時能有更好的故事。所以,我把事件的時序、名字,甚至是部分地理位置,都當作是創作上自由發揮的空間。但是,我忠於人物本身的塑造,並試圖呈現「人」絕不會只有一種面向:壞人可能創造美麗的東西,好人可能犯下嚴重的錯誤。
提議將庫利昂變成隔離區的人們並不邪惡,但他們確實先將島上的居民視為痲瘋病人,然後才將他們看作人類。當你將一個人的某種特質不斷放大──無論是種族、宗教,或是他們所愛的人,而不去觀看這個人的全貌,你會輕易的把活生生的人當成非人來對待。
現在,你可以造訪庫利昂島。您會看到鷹、教堂、醫院,雖然病人早已不在了。這裡可能曾被稱為活死人島,不歸島,或者如我所說──位在萬物盡頭的島嶼。但是對於我,以及亞米來說,這座島嶼也是一切的開始。
基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