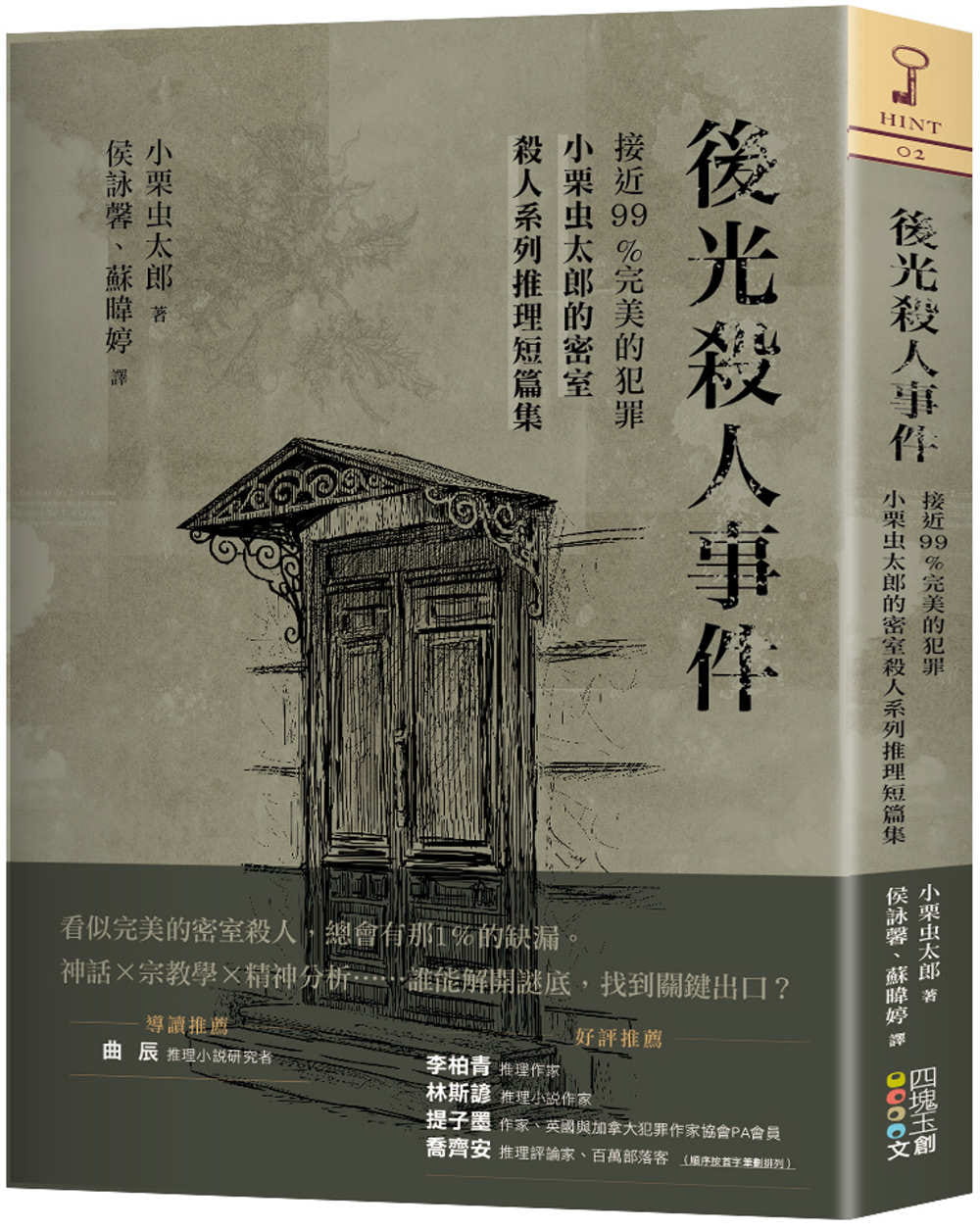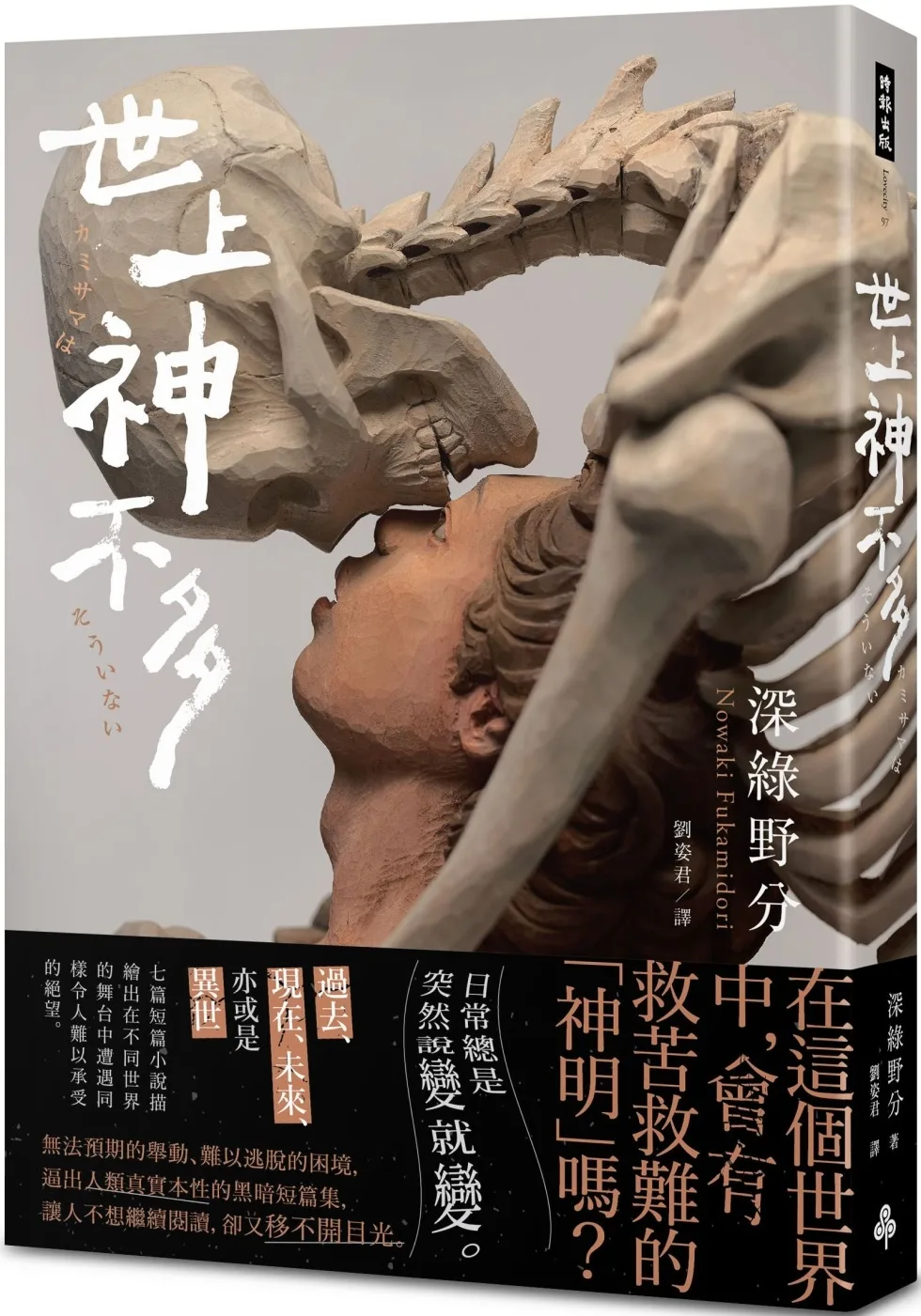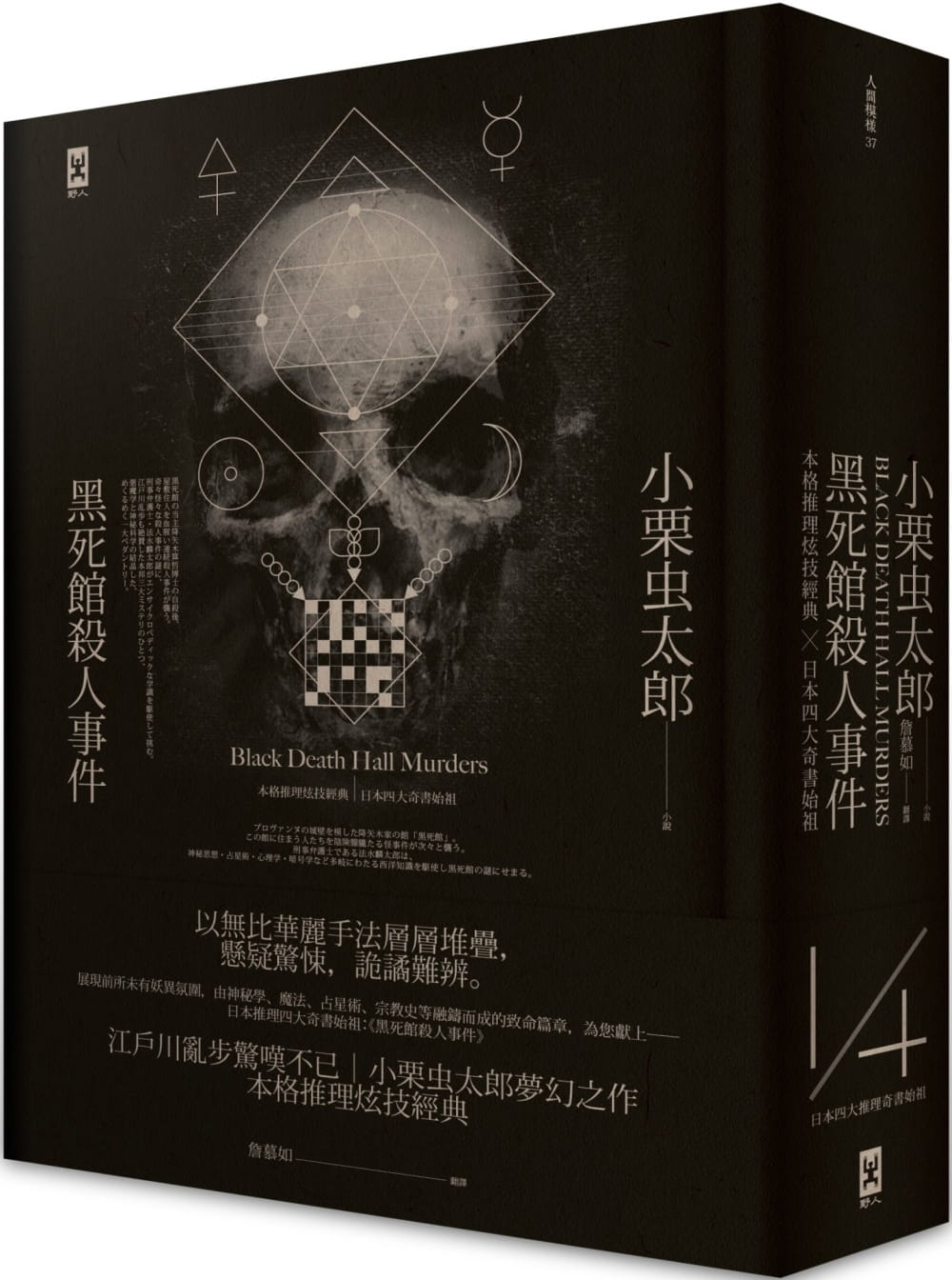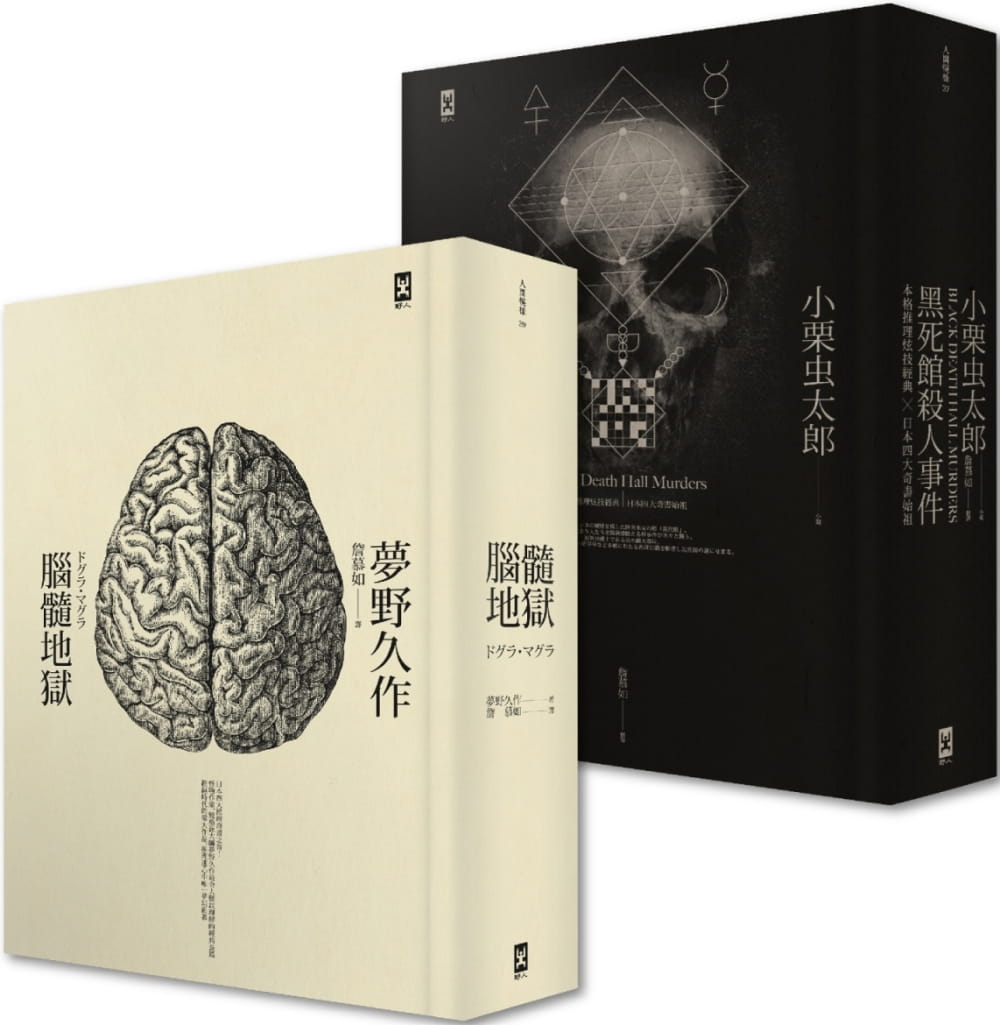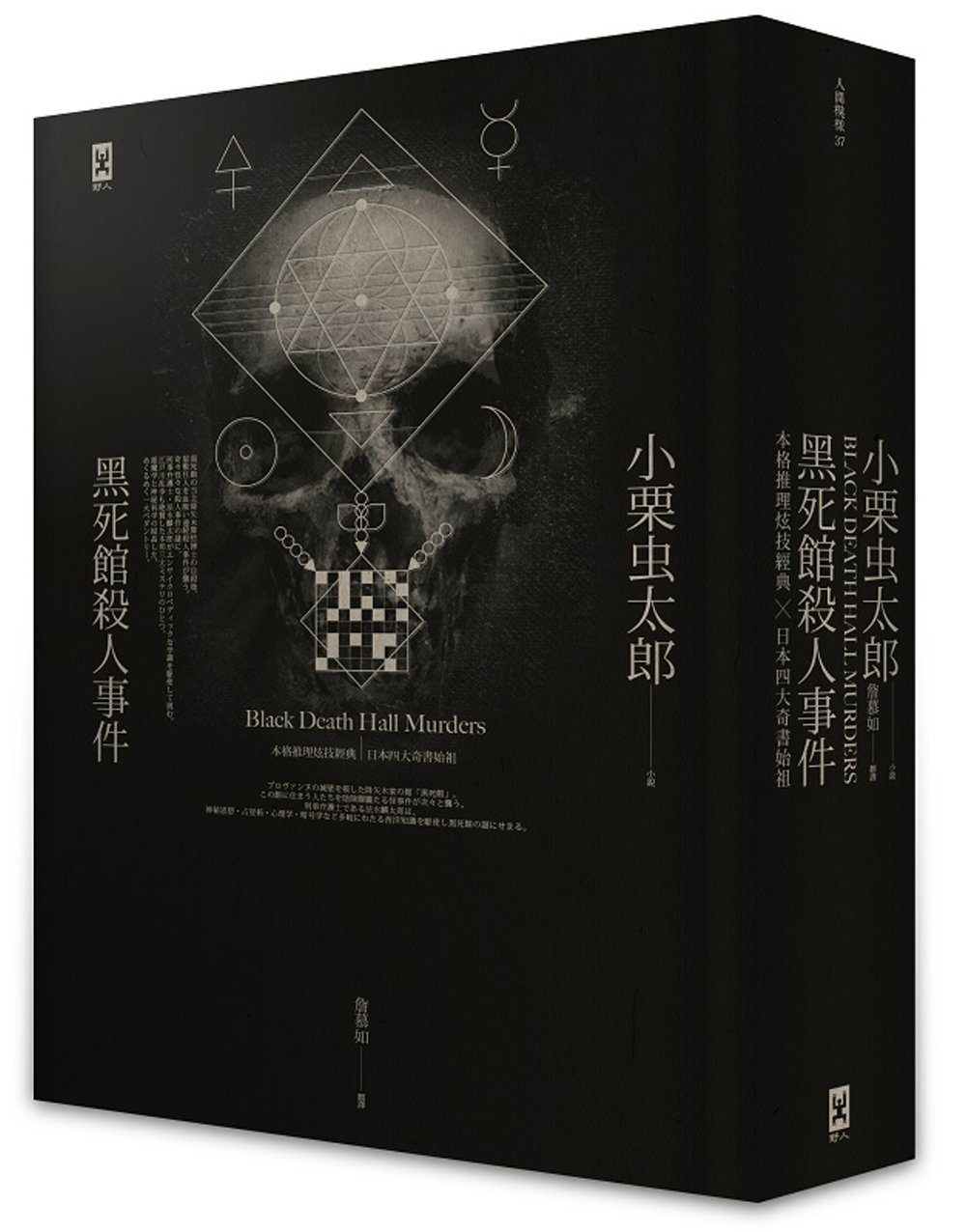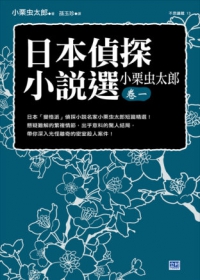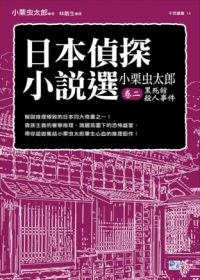導讀
以知識構築迷宮,以迷宮隱喻世界──小栗虫太郎的「推理小說」
一個試圖召喚出小說潛藏的世界樣貌的大眾文學研究者。相信文學自有其力量,但如果有人能陪著走一段可能得以看到更清晰的宇宙。並希望能回復每個跨越時代的作者本來面貌,好讓大家能夠知道該如何保持距離理解並重新看待自己。
綜觀文學史,我們發現,能決定一個作家是否成功的要素,除了才能之外,最重要的恐怕就是「經濟能力」跟「機緣」了。
前者決定了一個作家的「蟄伏期」,能夠用多長的時間去打磨自己成為能被人看到的材料,並且在應付柴米油鹽之餘心靈能夠保留多少餘裕,足以富饒到展現給他人看,都是經濟能力在背後支撐的表現,如果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太太沒有存錢,或是卡夫卡(Franz Kafka)沒考上公務員,他們能否以文學作品為世人所知恐怕都是未定之天;後者則是決定了一個作家的「能見度」,特別在網路還不存在的時候,你遇到什麼人、以及你的東西被誰看到,都直接的連結到你的作品可不可以獲得媒體的青睞,進而出道。
而小栗虫太郎,在這兩項上都可說是占了不小的便宜。
一九○一年出生於東京神田的他,家裡是代代相傳三百餘年的酒類批發商,曾經是江戶幕府的御用商人,即便父親在他十歲時去世,他仍靠著老家房產的出租收入以致生活不虞匱乏。
因為受到自己同父異母的哥哥的影響,虫太郎熱愛讀書,特別是獵奇或異端宗教思想一類的書籍。同時,他從小就展現優異的學業成績,不僅數學表現相當好,就讀正則英語學校高中部時還自修了法文,後來更陸續學了義大利文、馬來文。就算成績良好,但小栗虫太郎並沒有去念大學,而是靠著自己的語言能力,進行大量的閱讀,成為有名的自學雜學家。
一九二二年,小栗虫太郎用父親的遺產在小石川開設印刷廠,但根據小栗宣治(虫太郎之子)的說法,因為虫太郎根本不工作,整天只會構思並創作自己的偵探小說,因此才短短四年印刷廠就被迫收掉了。而後虫太郎乾脆專心在家閱讀、寫作,真的活不下去了就靠賣自己爺爺留下來的古董度日。這段生活對作家本人似乎是很重要的蓄力階段,看來輕鬆實際上頗為刻苦,這讓兒子顯然有些怨言:「我父親是個不能自己剪指甲也無法自己剃鬍子的人,如果不能用小說來揚名於世,幾乎就是一個沒用的人。」
但,用小說揚名於世的機會,就這麼到了。
一九三三年春,機緣巧合之下,小栗虫太郎遇到了國中學長甲賀三郎。當時甲賀三郎早就發表了他的代表作《支倉事件》(一九二七),並以嚴苛的評論成為推理小說界重要人物。儘管兩人並不相識,但藉著這次機會,小栗虫太郎將他在無業時期寫的〈完全犯罪〉交給甲賀三郎,獲得其高度評價,還寫了封推薦函。同年五月,虫太郎拿著這張推薦函,去拜訪了二、三○年代可以說是推理小說最重要的雜誌《新青年》的主編水谷準,再度以獨特的風格讓水谷準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時,發生了一件大家都沒想到的事,原本一九三三年七月號(六月出刊)的《新青年》早就說好要刊載橫溝正史的〈死婚者〉,並且是長達一百頁的中篇作品,但本來就有結核病的橫溝忽然吐血病倒,完全無法動筆。時間緊迫,又不可能臨時找作家寫新作的水谷準,就決定用小栗虫太郎篇幅差不多的〈完全犯罪〉作為代打。
這篇小說迅速地引起同時代讀者與評論者的喜愛,甚至被懷疑是早就成名的作家用新筆名發表的作品,小栗虫太郎成功地以作家身分出道,並站穩腳跟,成為日本推理史上幾乎不可能忽略的人物。
這段出道故事還有後續,根據橫溝自述,過幾年他跟虫太郎在新宿喝酒時,虫太郎對於橫溝抱持著感激之意,認為要不是橫溝生病給他機會,他是不可能那麼快出道的。橫溝則回以「與我的病情無關,你是一定會被世人所看到的」,後來還追加了一句「下次如果是你出了什麼事,我會代替你的」。孰料一九四六年,要在雜誌《???》(Lock)上連載〈惡靈〉的小栗虫太郎因為腦溢血而去世,同時正在《新青年》連載《本陣殺人事件》的橫溝原本想拒絕代打的委託,但顧及是小栗虫太郎的關係,便決定以《蝴蝶殺人事件》填補空檔,成就了一段文學史的佳話。
但,如果在毫無心理準備的狀況下,讀過小栗虫太郎的小說的現代讀者,內心恐怕會立即浮現兩個問題:為什麼要把小說寫成這樣?為什麼會獲得那麼多人的讚賞?
畢竟,他的小說往往始自一個華麗的謎團,無論是現場做為一個密室狀似孔雀明王乘坐著巨大孔雀以四隻手扼死僧人、或是明明應該是痛苦至極的死法但死者卻保持平靜甚至以禮拜姿勢直到僵化為止,都可以看出其充沛的想像力;但同時,這些殺人案件還纏繞著大量的知識,從神話學、比較宗教學、語學、遺傳學、精神分析、犯罪學、異端知識、博物學等等應有盡有,往往剛拋擲完一個學術名詞,馬上以另一個專有名詞開啟新的解謎。小栗虫太郎以知識為路標走出了命案建立的迷宮,卻又成功地用知識架構出另一個迷宮,吾等讀者只能在這中間來回擺盪,始終找不到關鍵的出口。
或者我們甚至可以說,作者對於炫學的欲求,幾乎就像是某種強迫症一樣,毫無節制,並且漫無體系。
對於第一個問題:「為什麼要把小說寫成這樣?」同為推理作家的?口安吾有個稍嫌武斷但又有其可能的評論,他認為炫學的理由其實是為了掩蓋作者腦中偵探小說題材的匱乏,炫學並非一種知性的表達,反過來卻暗示了文化的匱乏,「只有自學者才會想炫耀自身在語學上的知識,但語學既非學問也非知識。」換句話說,他在暗示虫太郎的「不知世事」,知識對他而言只是一種語言上的遊戲,其背後毫無對於知性或是理性的追求。
當然?口安吾似乎有些刻薄,但他卻很清楚的指出一件事,也就是看似華麗的炫學的背後,僅僅是毫無深度的穿插交織,每個學說或知識系統,以一種單薄的樣態互相支撐,但都只是紙做的支架罷了,毫不實際,也無法經受起外來的考驗。
然後我們才能回答第二個問題:「為什麼會獲得那麼多人的讚賞?」
大正時期(一九一二─一九二六)可以說是二十世紀日本第一個黃金時代,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努力的學習歐洲,進行現代化改革,長久的積累終於在大正時期開始看見茁壯的可能,政治風氣鬆綁,各種思想如雨後春筍出現在這個東方的島嶼上。同時,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打,遠離戰場的日本免於災禍,卻又享受了戰爭紅利,自身的工業與經濟規模靠著為戰爭國打工而建立起來。當時局勢大好,一切看來都朝著好的方向前進。對日本人而言,科學是好的、理性是好的、現代是好的,一切的問題皆有解決的可能,所有的謎團都有著明快的解答。
但一九二三年關東大地震、一九二七年昭和金融恐慌、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以及直接受此影響的一九三○年昭和恐慌),歲月不再靜好,問題看來只會愈來愈多,而沒有解決的可能。這種種都讓民眾無法對自身處境感到樂觀,因此在文學審美上也從理性知識當道,轉而成為以感官情緒為主的「???????????」(erotic, grotesque, nonsense;煽情的、怪奇的、荒誕的)。原本一直以理性為美的推理小說,也開始被挖掘出另一種可能,當我們將「死亡」視為一種遊戲,所有的傷害都被化約為數學公式的時候,推理小說的殘酷便以「獵奇」的方式被表現出來了。這就是為什麼,虫太郎小說會以一種夢幻的口吻,訴說再殘酷也不過的殺人場景,那是人的極端值的放大,無論是否令人嫌惡,仍然是我們的一部分。
在這種狀況下,知識的存在引來了新的挑戰與質疑,為了要解釋這個部分,又避免暴雷,我試著用以下這個小故事來當例子:在劉向的《說苑》中,曾經提到春秋時期的翟國曾經有過「雨穀三日」、「雨血三日」、「馬生牛,牛生馬」等等在過去會被認為是「國之將亡」的怪象,卻被解釋為「雨穀三日是因為龍捲風將穀物捲來、雨血三日是鳥在空中打架、馬牛相生只是因為他們沒有被分開圈養罷了」。
這段故事常會被用來做為中國古代早已具備理性思想的例證,只是如果細究,到底龍捲風該有多大才能捲來下三天穀雨的分量、鳥群又有多大足以下到三天血雨、而牛跟馬難道沒有生殖隔離的問題?這些解釋之所以可以成立,是因?這些解釋都只存在於語言之中,當不涉及真實世界時,語言可以任意涉入概念世界,決定我們相信或不相信的,並非是其操作可能性,而是那個相信「萬事皆有一個理性解釋」的信念。
這也就是小栗虫太郎所揭示出的推理小說的局限,推理小說終歸是在概念世界中運作的(想想〈莫爾格街凶殺案〉中不同國家的人指證出的不同語言、想想有多少推理小說建立在巧合或「練習」上),因此純粹的知識語言可以介入概念世界,只要不需要著地,那誰會在乎它們究竟是不是空中樓閣?
誠如亂步說的,小栗虫太郎的小說就是「在非歐幾里德的世界中以歐幾里德的語言來描繪出充滿激情的紙頁」,它也見證了人類想像世界的極限值,這或許也就是如今我們閱讀他們的意義了。
那是人的極致表現,期間限定的極致表現,錯過不再。
?
曲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