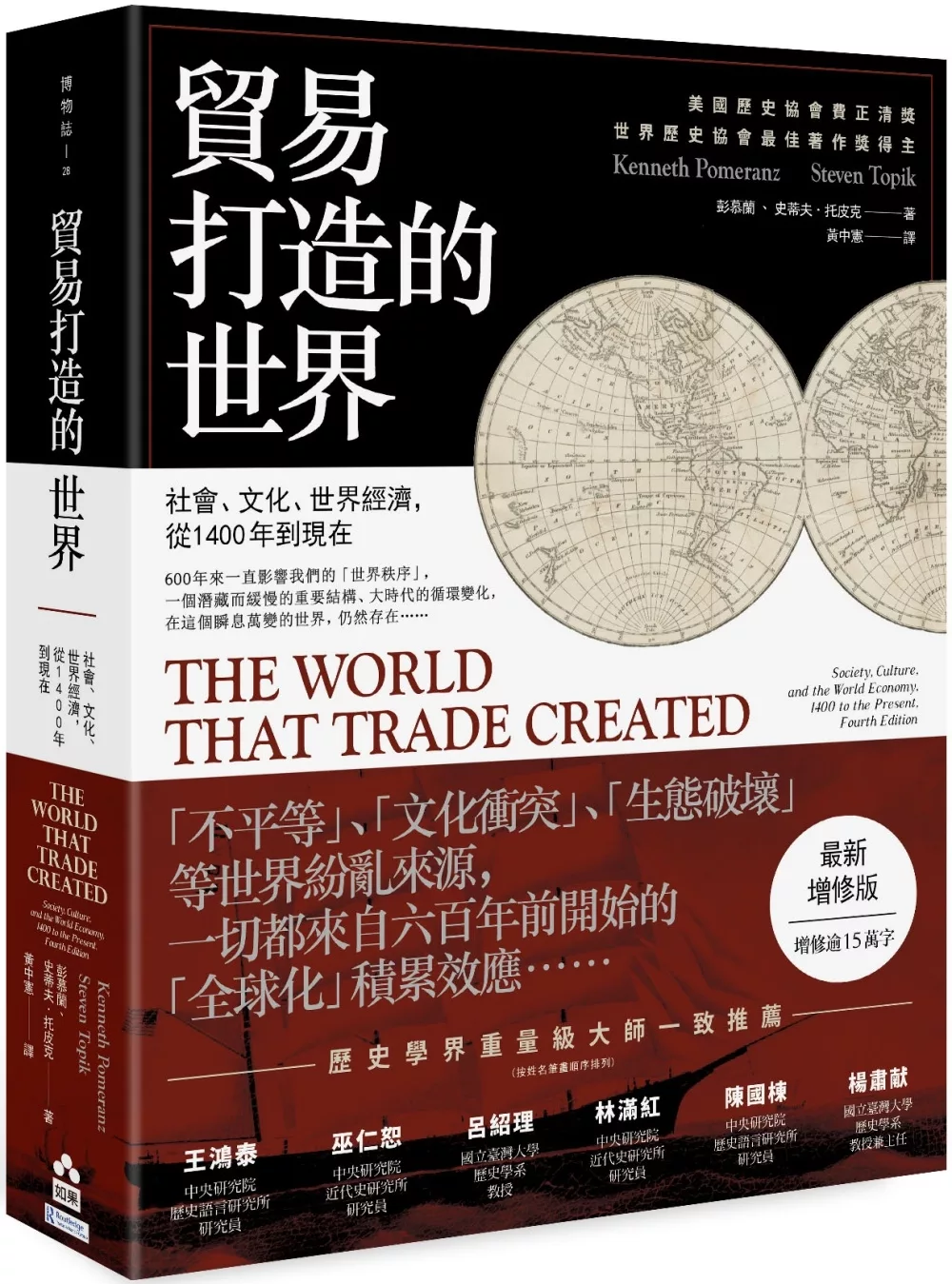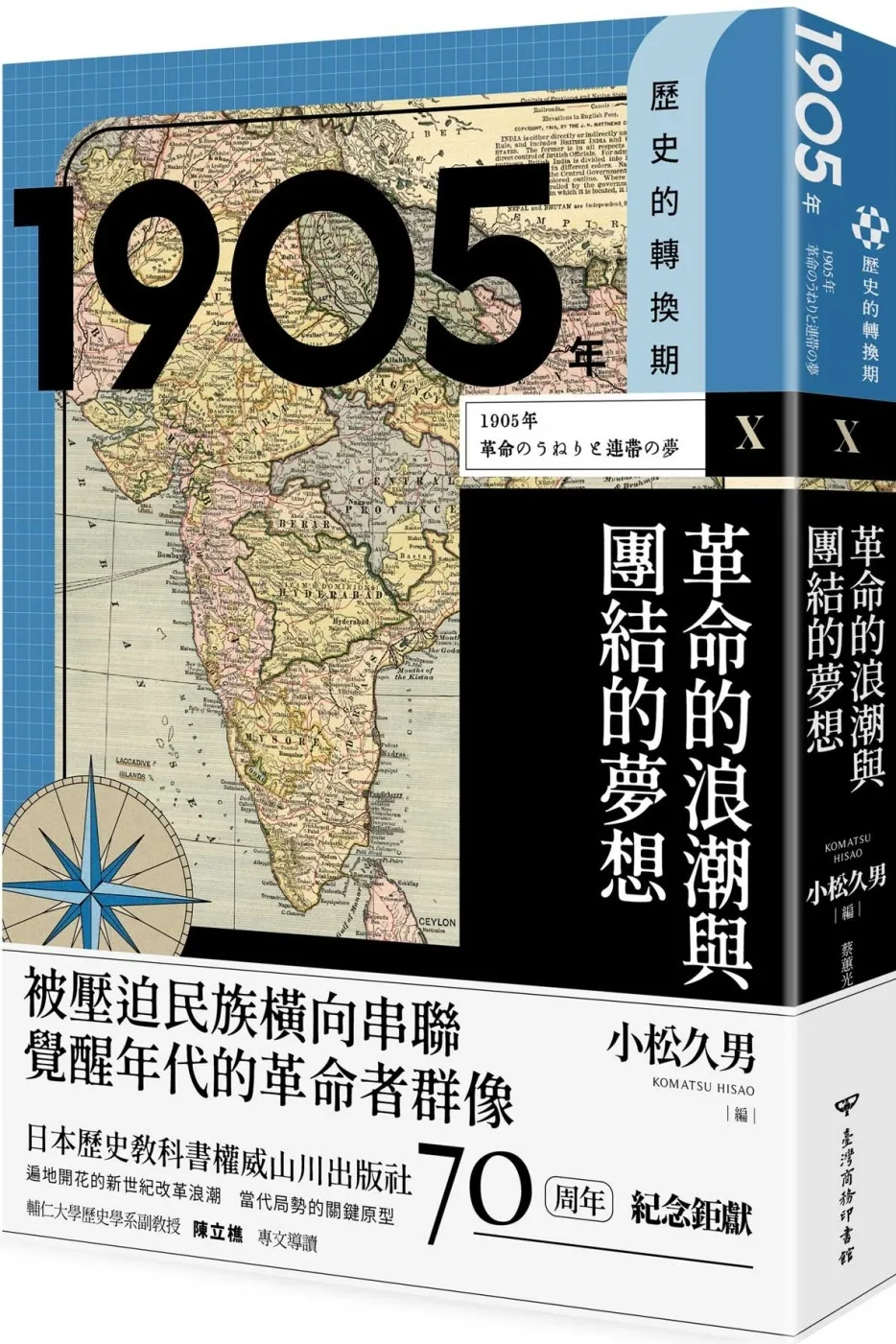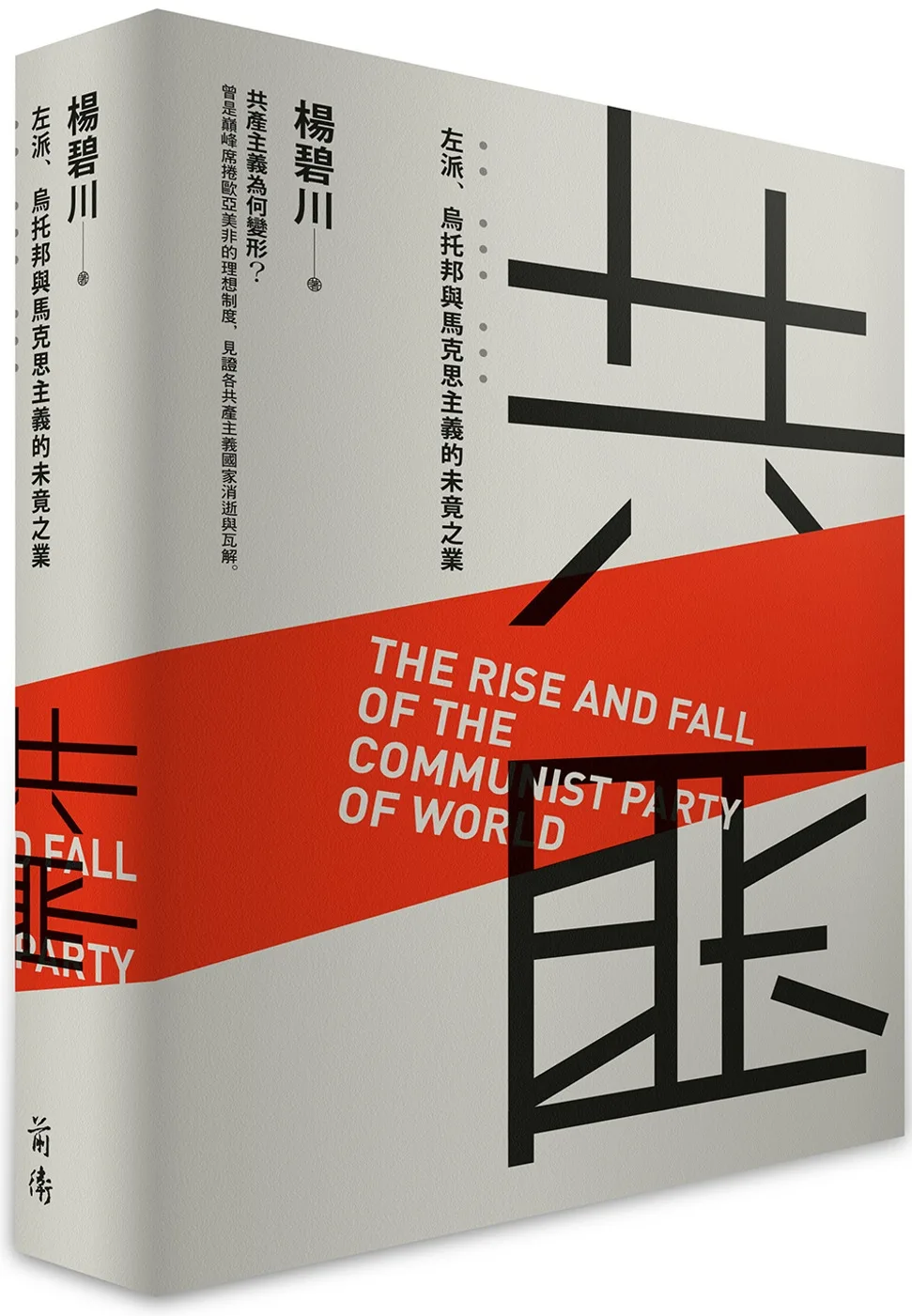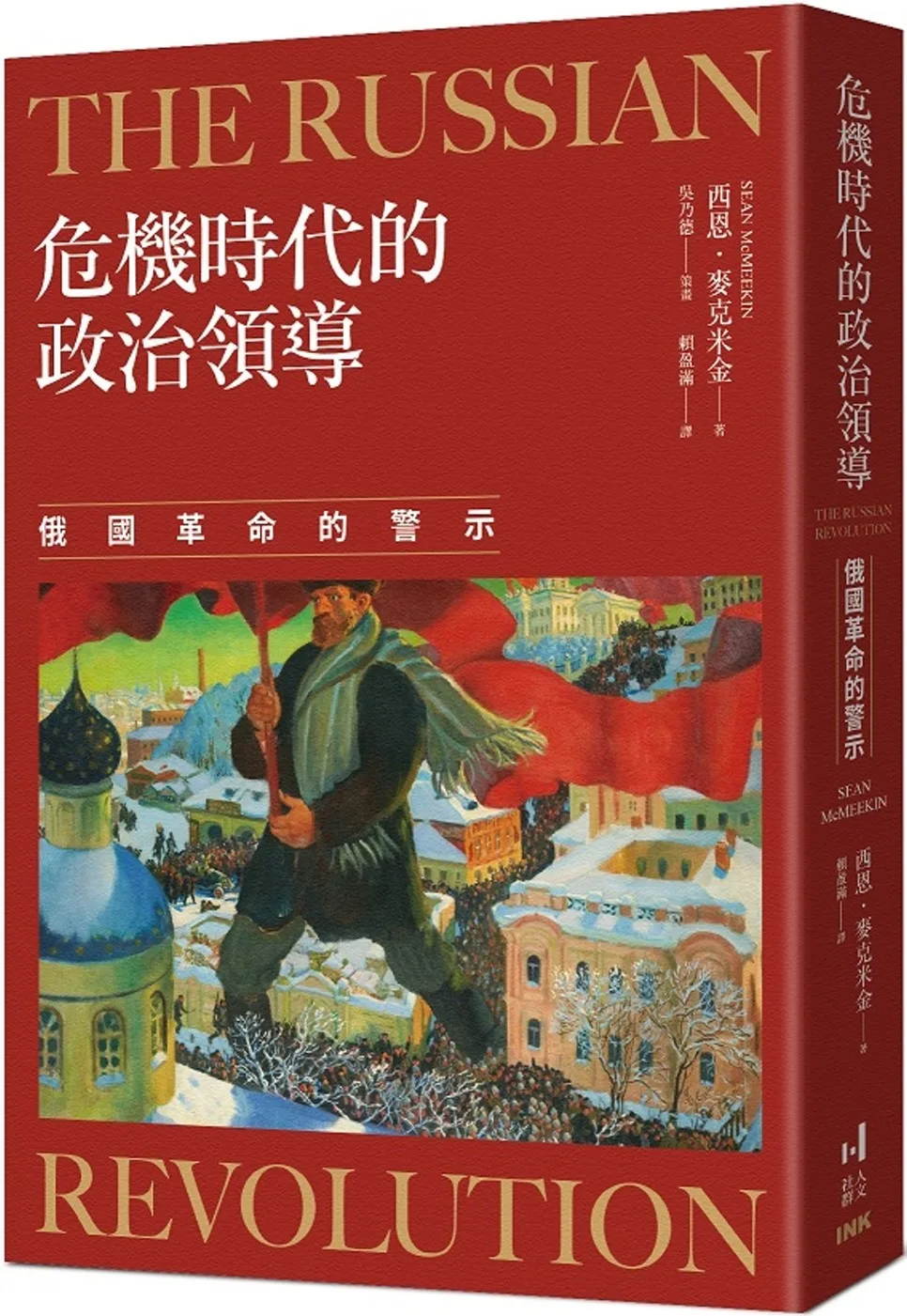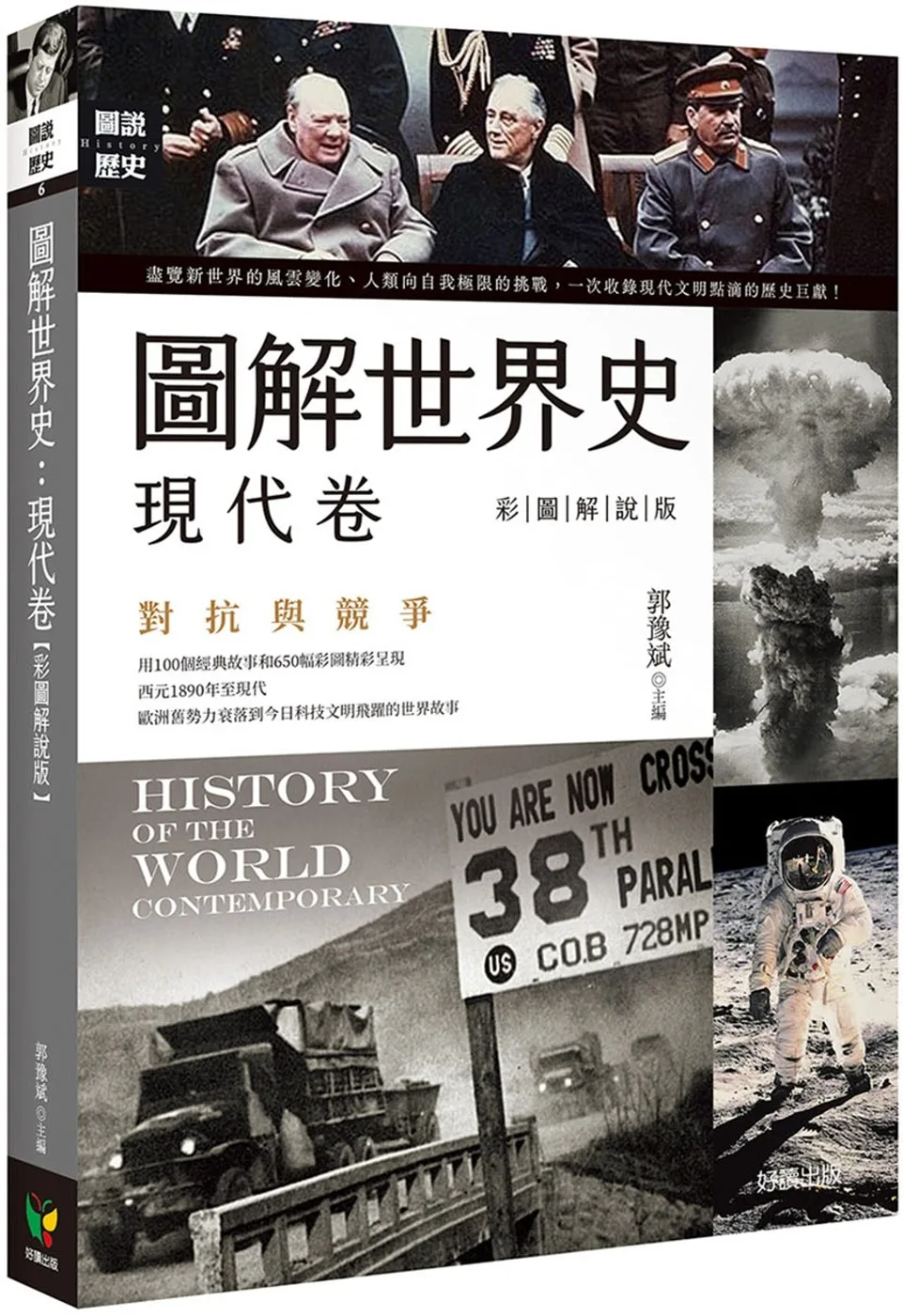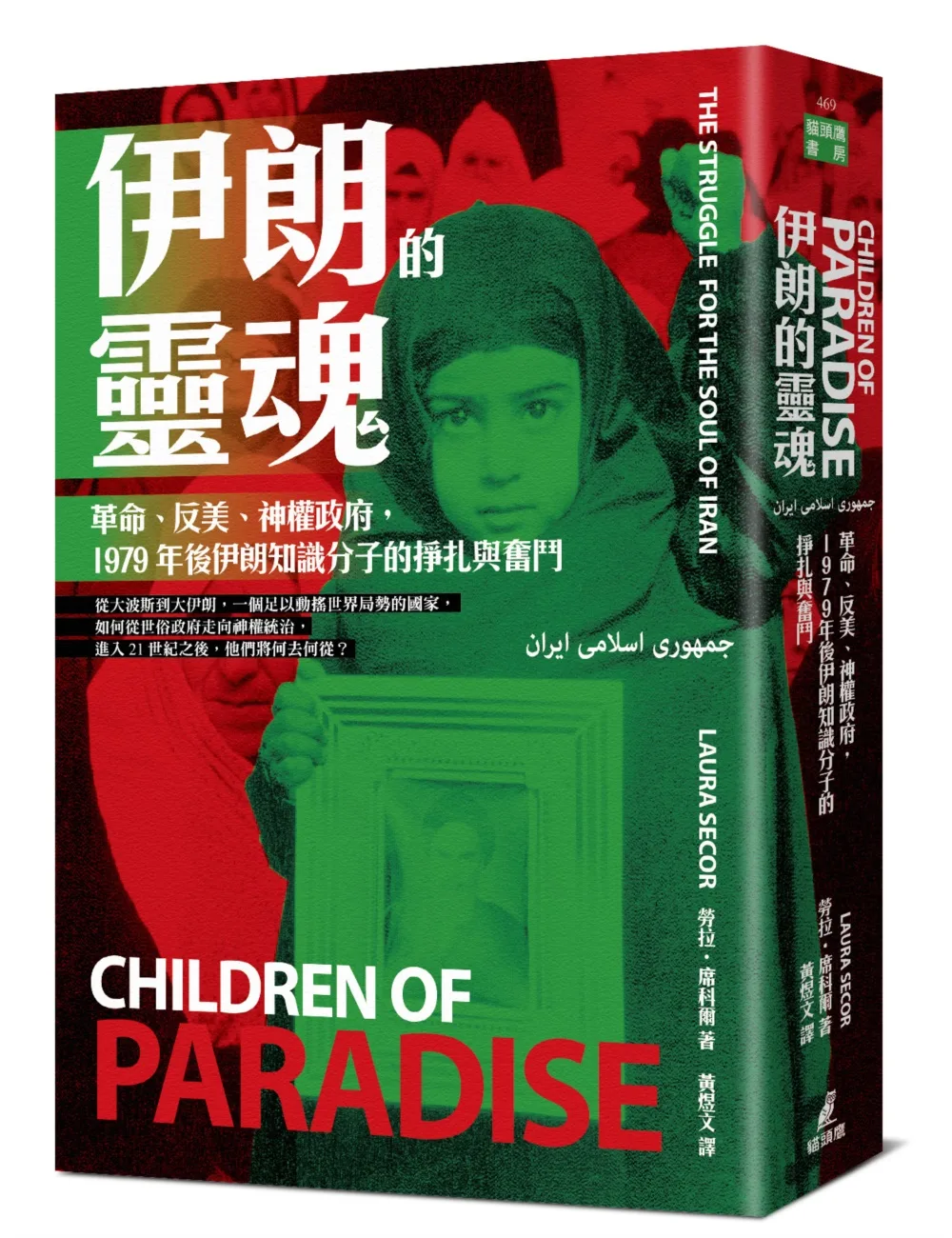前言
很高興能為最新增修版《貿易打造的世界》的中文版寫序。史蒂芬.托皮克和我開始在雜誌上撰寫日後會成為此書核心內容的文章時,並沒有想到超過二十五年後,還會有人讀其中的任何一篇;此外,其中許多篇文章,最初是為一家幾乎只有美籍讀者的雜誌而寫。除了多年來常參與學術辯論,過去我們兩人的確常在自己的其他工作上為美國境外的讀者撰文;隨著我們的文章集結成書,隨著此書受到好評並被我們不時修訂,我們開始更有系統性地思考如何向跨國的讀者介紹此書。但在那些原始文章裡,想必有一些東西不只打動了對跨國經濟活動感興趣的美國人,也打動了其他地方的人。
當然,本書能得到讀者青睞,初版問世以來二十年的世局演變,幫了大忙。這段期間的演變讓人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清楚看出,金錢、人員、貨物、觀念大於以往的跨國界流動,乃是當世最顯著的特色之一──對那些流動的反應(和往往反對)亦然(如果說有什麼主題比這些流動更值得大書特書,大概就是我們的經濟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也是貫穿本書的主題之一)。這段期間的演變也一再表明,成長始終是個複雜過程,從中既產生贏家,也產生輸家,表明一新產品、科技或市場關係所帶來的結果,可能隔了五年、十年、二十五年,或五十年就大為改觀。
與此同時,我猜本書的吸引力,有一部分來自史蒂芬和我都非以「世界」歷史學家身分起家,更別提以「全球化」歷史學家身分起家一事。我們兩人最初都專攻特定地區──他專攻拉丁美洲,我專攻東亞。這使我們更加相信地區的特殊性很重要,即使在地區外的連結愈來愈多之際亦然。從某些方面來說,自成一體的地區,其重要性或許甚於數十年前。
拿大家稱之為東亞的這個地區來說。一九八○年代初期我開始讀研究所時,理所當然地認為這類地區是重要單元;從日常角度來看,它們似乎在某些方面比「世界」還要真實──儘管或許不如國家單元那麼真實。但那時,中國大陸與日本或韓國,或者中國大陸與台灣,接觸甚少。台灣與韓國在幾個方面與日本拴在一塊,儘管就這三個社會來說,它們與美國這個地區外國家的連結,比它們彼此間的連結重要得多;不管從政治、經濟連結的角度來看,還是從學生移動等之類「較柔性」流動的角度來看皆然。簡而言之,那時的東亞地區以知性建構物的身分存在,以地緣政治對立的場域的身分存在,以我們能指出過去影響力之重要流動的地方的身分存在;但如果一「地區」是靠內部連結與相互影響結合在一塊的空間,那麼今日東亞就比那時遠更稱得上一個地區。如今東亞的內部連結比以往任何時期稠密,但那些連結朝四面八方流動──不只是從北京、東京這兩大中心往外流動。如今約有一百萬的台灣人住在中國大陸;大陸境內的外國留學生以韓國人為最大宗,韓國境內的外國留學生則以中國學生為最大宗。二○一七年,香港是中國最大的境外直接投資來源(但老實說其中許多投資來自數個地方,包括從中國大陸本身經香港流入者);新加坡、南韓、日本在這方面都超越美國,而台灣(當然比美國小了許多)也只稍遜於此。音樂、電影等大眾文化朝四面八方流動,包括二三十年前即使沒有政治壁壘,也會是不可思議的流動(例如從韓國向日本的流動)。不管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最終結果為何──如今預料其結果還為時太早──此倡議肯定會創造出更多地區性連結,同時不會創造出真正全球性的基礎架構。
因此,不管日增的網絡規模和密度有多重要,若認為這些網絡都指向一個無縫連結的未來,那將是大錯特錯。非洲史學者佛雷德里克.庫珀(Frederick Cooper)說得好:「全球化」這個概念有兩個問題,「全球」和「化」。就我的理解,他的觀點是:如果我們把全球化當成指導概念死抓著不放,我們就是在認定照當前趨勢走下去,不管人是否想要一個世上每個地方都彼此相連的世界,最終必然出現那樣的世界。其實我們必須切記,凡是網絡都包含某些地方,而將其他地方拒於門外;網絡的結構由人的自主選擇,而非由不可抗拒的過程決定。
此外,即使某些網絡的確幾乎涵蓋整個世界,若以為這使其他規模的網絡或身分認同變得無關緊要,那就大錯特錯。許多美國人誤以為美國或由美國主導的「西方」是世界的中心,誤以為全球化就意味著其他每個人都日益接近(且愈來愈近似)那個中心,因而有時似乎未能理解這個道理。但這是個重要的道理,而且是從頭至尾貫穿此書的道理。
此外,放眼歷史,凡是適用於地區與世界的道理,也適用於國家與世界。全球經濟與民族國家在數百年間同時出現。它們往往彼此衝突,但也往往互相強化,一如兩者往往是在與多民族帝國、民族離散網絡和其他社會單元、空間單元的有益性緊張關係中建立起來。事實上,本書闡明,典型的民族國家建構故事,描述一個從自己國民取得稅收、軍人等打造有成效之國家所需之資源的政府,但新興的國家政府倚賴其他人的肯定和協助也是司空見慣(尤以二十世紀為然)的:外國放款機構、付出的礦物開採權使用費可能(如在某些波斯灣國家所見)比國內稅收高出甚多的外國公司、外籍勞工、提供安全保障的大國等。透過外部連結取得重要資源的政府往往能在不需自己人民同意下倖存,乃至壯大,因此這樣的過程會產生令人不樂見的結果;但即使如此,它們作為歷史現象,其真實程度未因此稍低(當然,由國內力量推動的國家建造,往往也有其醜陋的一面)。
對身為觀察者的我們來說,這表明全球層級的分析雖不可或缺,但光是這樣的分析並不夠;藉由肯定國家、地區和其他層級之歷史的重要,我們也肯定了特定文化傳統賡續不絕的重要性。事實上,我們一再強調,從特定時間、地點的視角,出於客觀效用的考量,而似乎能直接以可測量的物理特性為基礎的東西,大多更複雜許多:使白米比糙米更受青睞者,使寶貝貝殼成為恢復財富的有效工具者,或者(舉個極端例子),使馬鈴薯成為某些人即使在飢荒時都拒食的「奴隸食物」者(一七七○在那不勒斯就出現此情況),乃是社會、文化過程。因此,把拇指般大小的蠶繭抽成約五百公尺長絲線的女人乃是「非專門技術」工人一說,也絕非客觀說法,儘管晚近幾百年她們一般來說被歸類為這樣的工人。價格反映了社會等級和文化價值觀,因此,有些歷史,必須予以理解,而非只是視為理所當然。
當各有自己之等級體系、價值觀體系的不同社會以新方式相接觸時,那些歷史有時會變得特別複雜且有趣;有些社會,其成員除了透過某些物品,與別的社會之成員少有接觸,從而大體上不清楚左右另一端之供給和�或需求的因素,而當物品在這些社會之間移動時,也會發生上述變複雜且有趣的情況。不管是在上述哪種歷史情況裡,價格和市場都會變動,資源會被重新分配,而做某些事所能得到的回報或許會徹底改變,從而使人的生活改頭換面。簡而言之,貿易不斷改造世界,往往透過彌合較地方性價值觀體系間的歧異來改造;但同樣真實不假的,多元且先前就存在的世界,提供了某些信號,讓人得以知道什麼是值得拿來交易的東西。撰寫此書時,我認定分析形形色色的例子──有些例子為任何讀者所熟悉,有些則是讀者所不熟悉──或許有助於人們思考這兩個道理,把這兩個道理用在他們自己會經歷的事情上。如果其中某些故事能讓你會心一笑,那就再好不過了。
彭慕蘭
芝加哥,伊利諾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