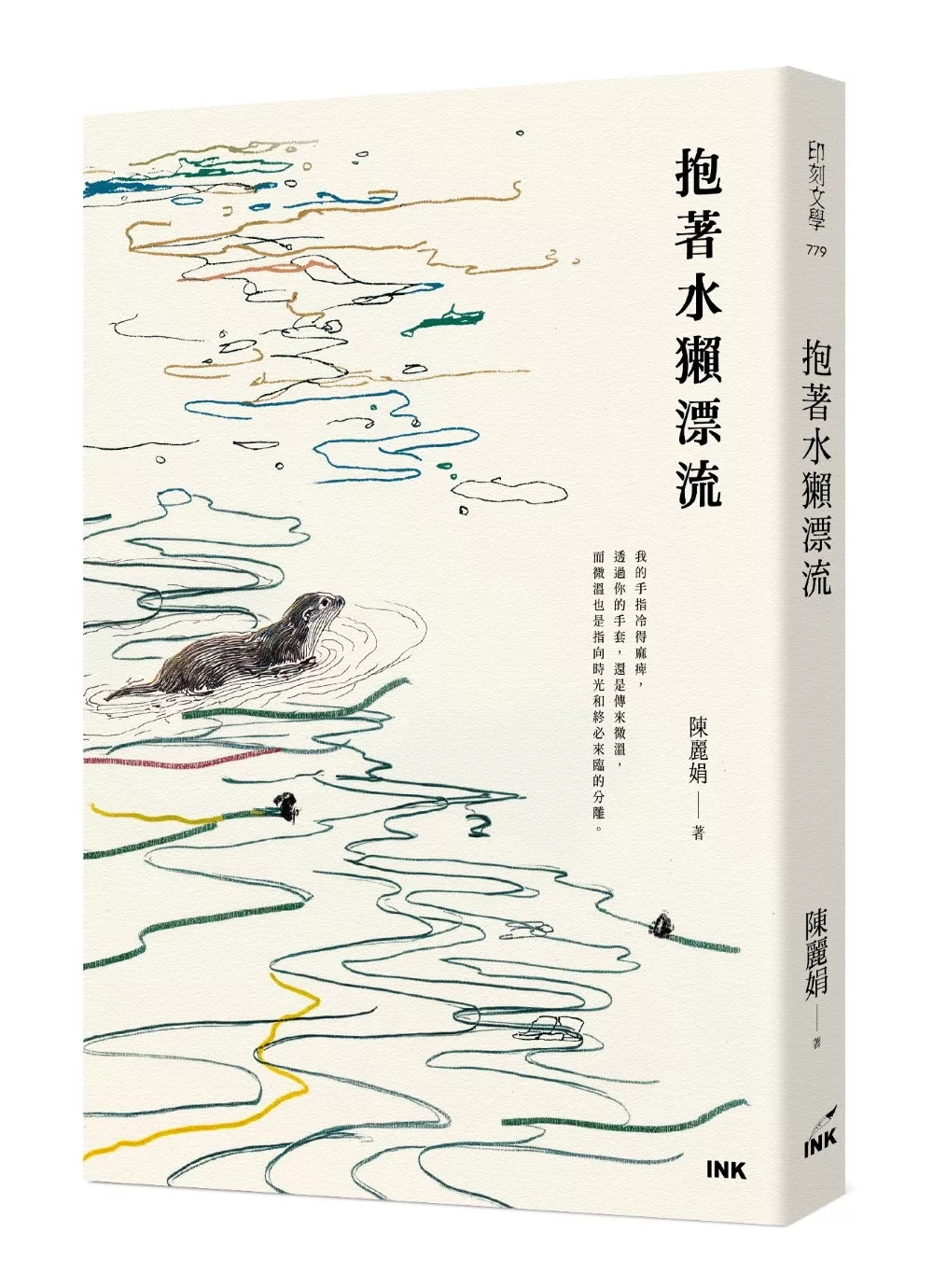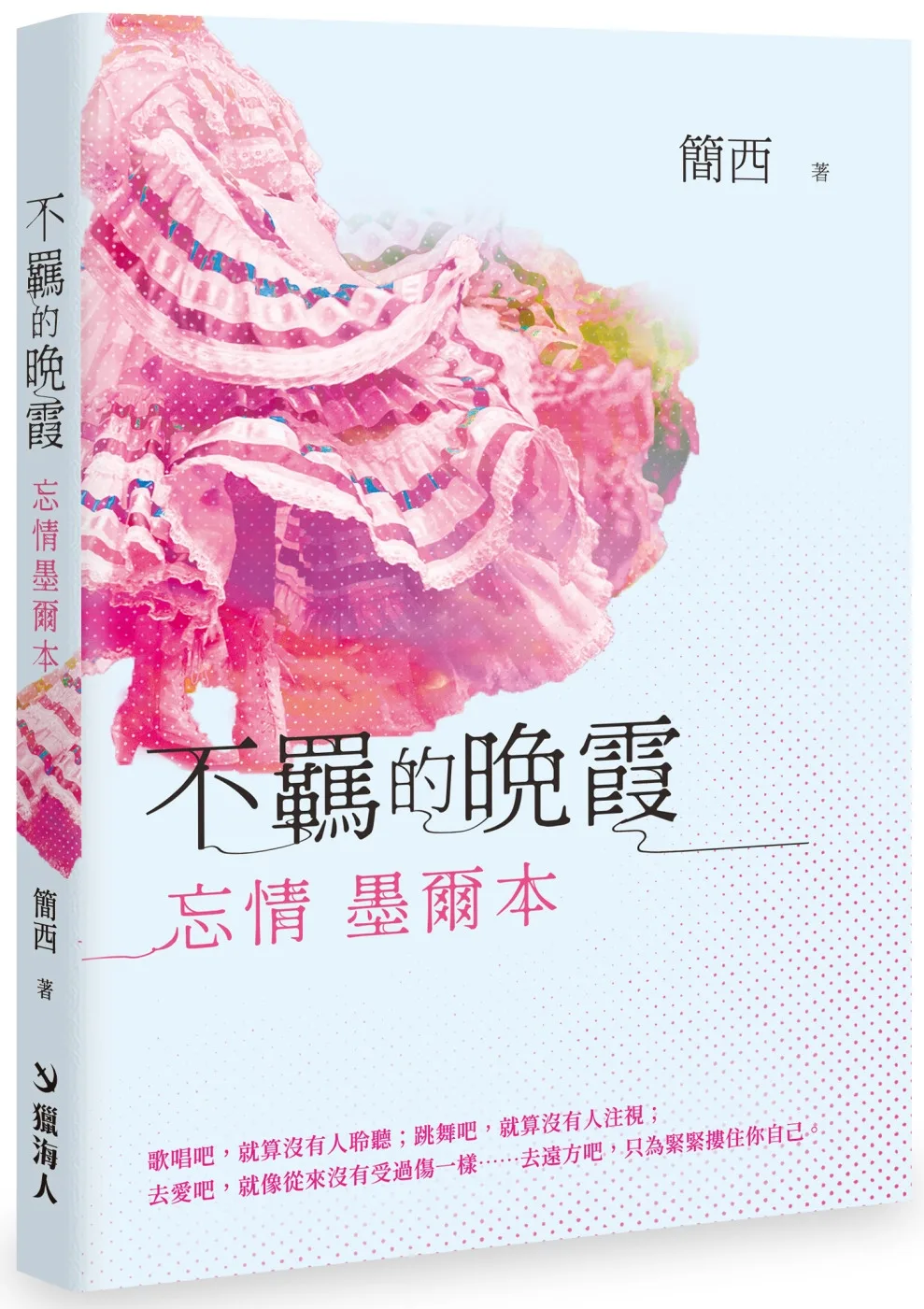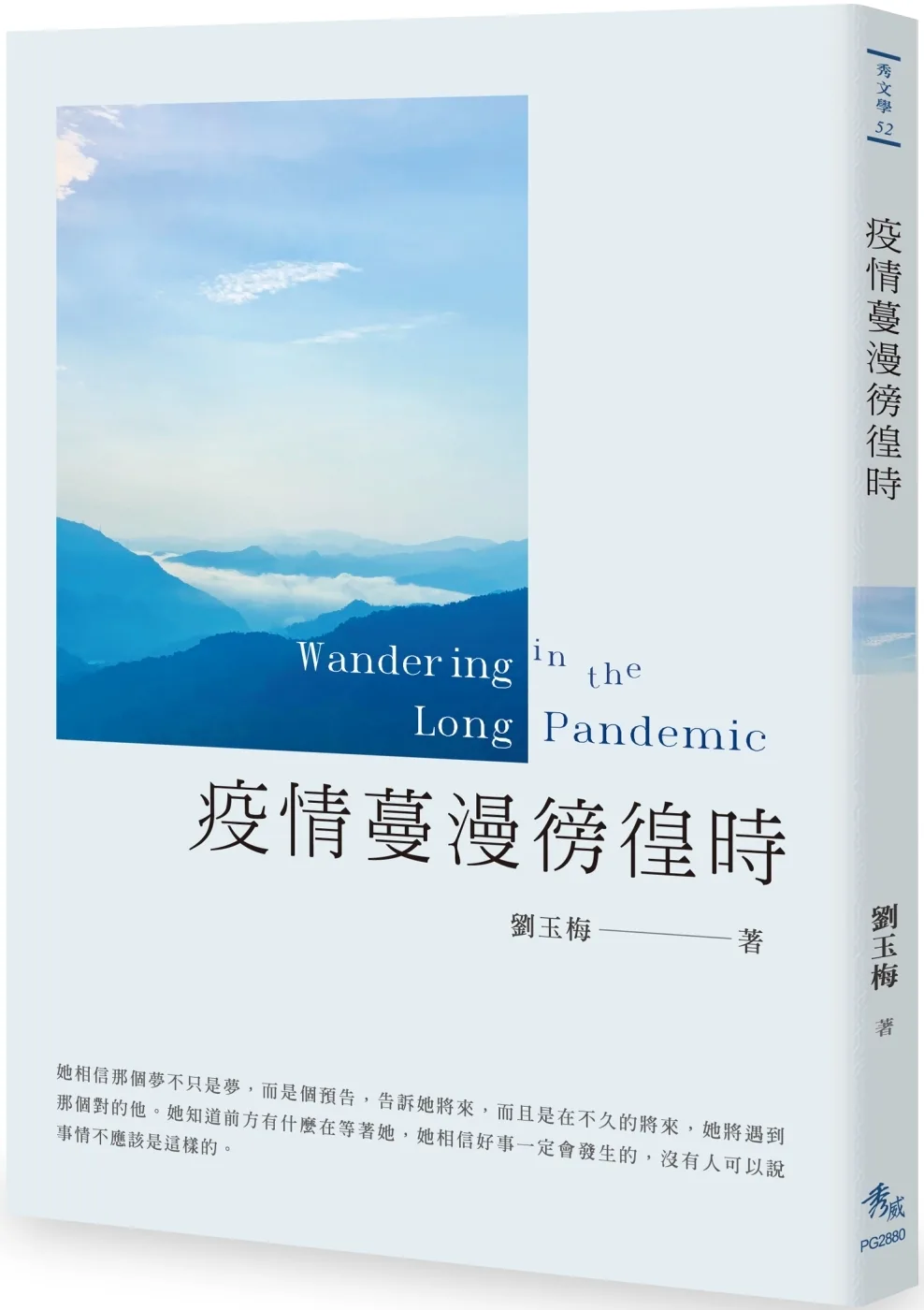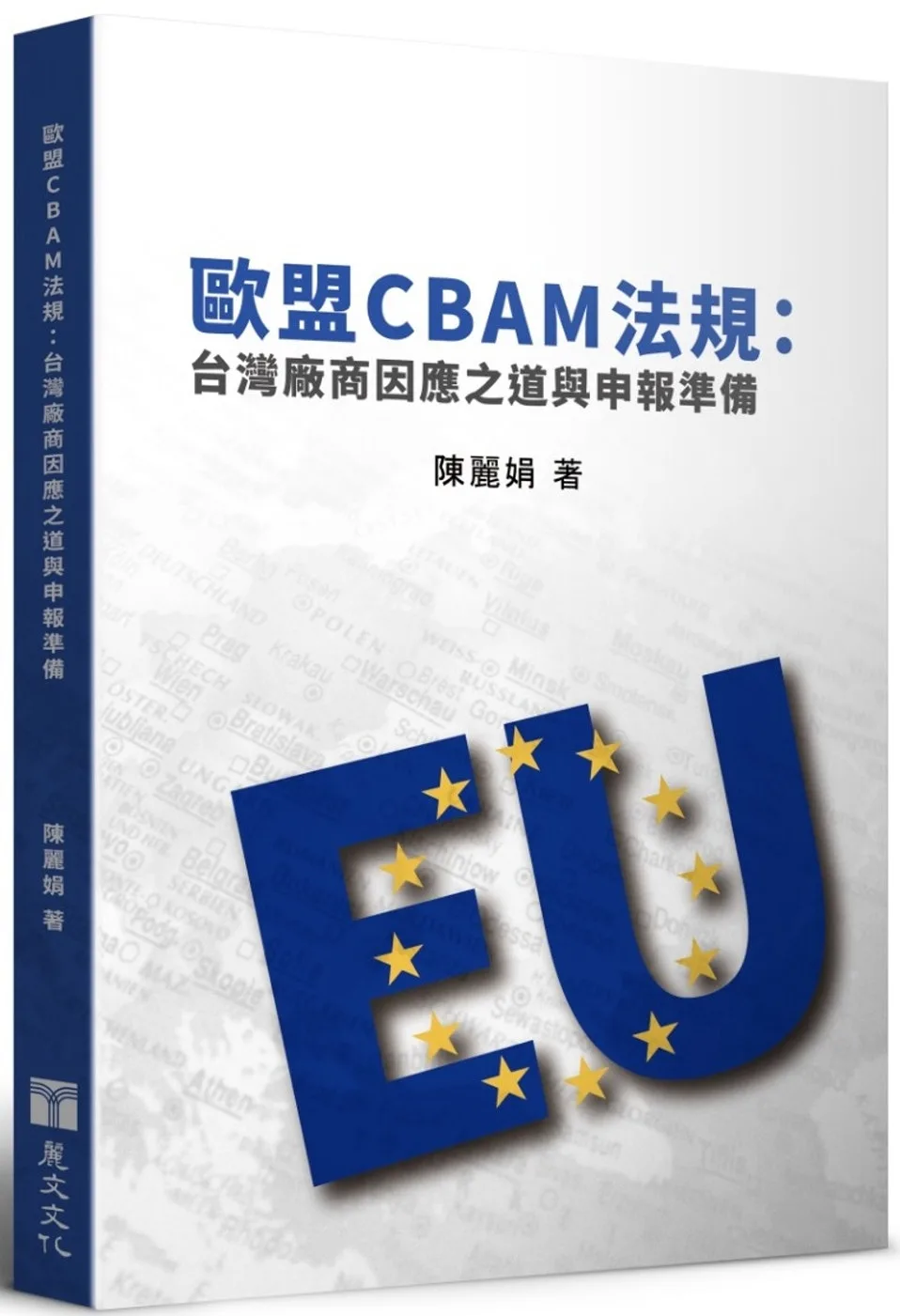●節錄自〈尾聲:浮舟〉
我把各種身分證明書影本、學歷影本、申請表格、請大學院長和教授給我簽署的推薦信及保證人書、創作履歷、作品選輯——一一用彩色的索引標貼標示好,用大型文件夾夾著再放進布袋裡,在一個雨天下午把它緊緊夾在腋下,搭捷運到台北巿的移民署。
?
到達廣州街的移民署——其實我已很熟路,因為留學身分的居留證每年都要來續領一次。我一進去就搭扶梯到負責港澳、大陸事務的地下一樓。我跟守在電梯口的志工阿姨說,我要申請專業移民。她說:「這個要在網路上辦啊。」我跟她解釋說不是那樣啊,她還叫我到樓上用這裡的電腦。在我堅持下她才去問櫃檯裡的職員,一會兒後讓我進去辦理。
?
櫃檯裡面的職員仔細翻看我遞上的文件,有些表格已改版就給我重填。明明還算順利,但在她檢查文件時我卻不停流汗擦汗。完成遞交後我拿到收據,接著開始漫長的等待—到底我這個肉身何去何從呢。這時候先放鬆一下,走路去西門町吃蜂大咖啡。
?
在努力融入台灣社會的當兒,單單寫字這個事情,讓我無時無刻感到自己是個外國人。我看到臉書上很多這樣子的留言,說「台灣人不會說XX」、「這不是台灣用語」。例如不可以說「舉報」,要說「檢舉」,因為「台灣沒有人說『舉報』」。那麼「立馬」、「軟件」也不能說,因為是「支語」。我,一個寫作的人,被嗆過文筆很不行、要回去好好學中文。
?
但我納悶,在公開平台上,留言者除了台灣人,也可能是世界各地的華人,甚或學過中文的各國人,那麼他們的用語自然會有若干差異。現代漢語不是豐富而多元,本身就包含不同省藉和國藉「中文」使用者的各式辭彙嗎?香港人寫的書面語,不也是中文嗎?對於字面上可以理解,但不習慣的用語,為什麼不能就上文下理,望文生義呢?這時候我覺得自己好像沒有毛的地鼠,皮膚特別薄、特別敏感,一切刺激都令我渾身癢痛。不過我後來了解到,大家的焦慮來自被巨大勢力侵略的反應。我這個語言背景十分混雜的人就很容易中槍。
?
*
?
他們,我的朋友,都叫我現在就進去商業、藝術機構或畫廊做行政。但我還未寫好畢業作品,而且人家要的是由企畫到接送倒茶無上限加班的全能小妹,快五十歲的我——一直流汗——真的能勝任嗎?香港朋友T說,她曾任職大企業做慈善活動的崗位,每年請一個小妹,沒日沒夜瘋狂催逼她,用壞了(過勞大病),翌年再請一個新的。我當年做了七年多的表演節目行政,那時候案頭的電話不停不停地響,我根本無法好好做手上的事情。離職在家後幾個月來每天都作
夢還在上班。而直到今天,我聽到無論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電話鈴聲,都會心跳加速,緊張不安。
?
藝術家朋友A告誡我,妳怎麼會在這裡虛度了三年,沒有組織人脈、建立事業,妳要去畫廊看展、寫藝評,打卡,tag 對方讓別人知道你會什麼技能。我啞口無言,我連畫廊在哪裡也不知道。
?
我跟W說:「現在還有一個學期就要畢業,朋友們開始告訴我,妳要怎樣怎樣。」
?
我以為她會懂我。W被長年服務的公司辭退後,也經歷過一段迷失的日子,很多人叫她要怎樣怎樣,但那些都不是她想做的。不料她對我的問題反應十分大,說一直很擔心我的生計問題,但怕我接受不了,不敢問起。她一口氣說她怎樣辛苦才在異鄉找到工作,不知道的事情也要逼自己知道,要在不想做的工作當中做選擇。她本來過的生活是隨著出差,不斷去世界各地遊歷,但現在要呆在同一個地方硬著頭皮工作。「妳一定要做,除非死掉。雖然我知妳聽不進去。」人要維持低限度生存、交租,要努力做自己不喜歡的工作,這也滿諷刺。來自X的金援早已斷,現在除了零星的接案子,就是吃存款。
我來到台灣,在藝術大學漫遊了幾年,是時候畢業,也是迷惘的開始。這是最後一個學期。畢業、迷惘。這不是二十二歲的人才面對的問題嗎?幾個月後,我就五十歲了。生日後就要五十歲了;我現在就五十歲了;我已經五十歲兩個月了;我……。
?
學生簽證是一個甜蜜溫暖的避風港,我以為它會一直保護我,但即便是最耐放的罐頭也有保質期。一旦這張棉被被踢開,我就像蠶寶寶那樣裸露在吃人的現實中,一下子就會冷死。在這個學期內除了完成畢業作品,也要想辦法把自己留在台灣——回香港的話房租太驚人,存款很快便見底。近來我經常想像到這個畫面:藍天碧海,我一個人在小艇上,漂流公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