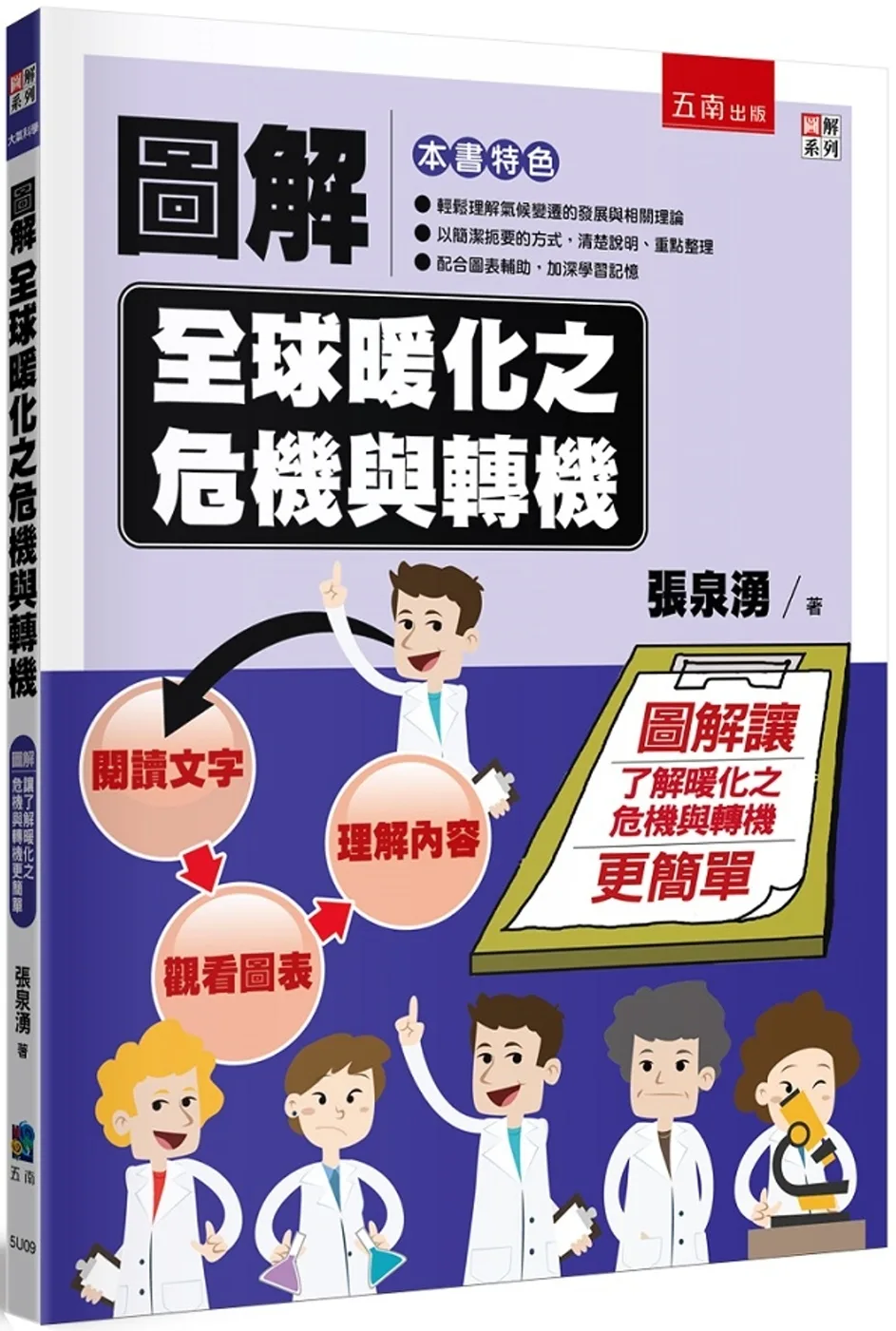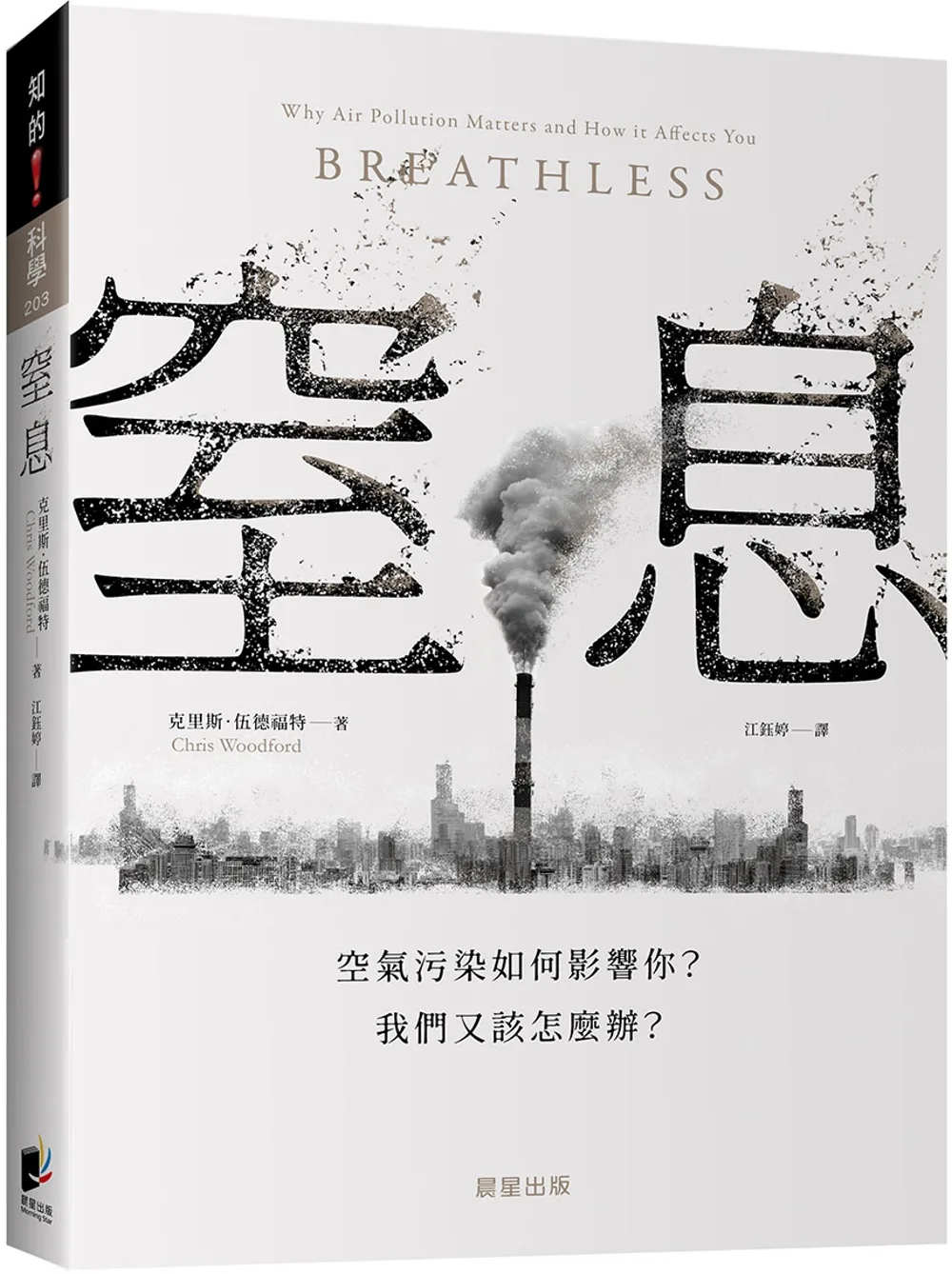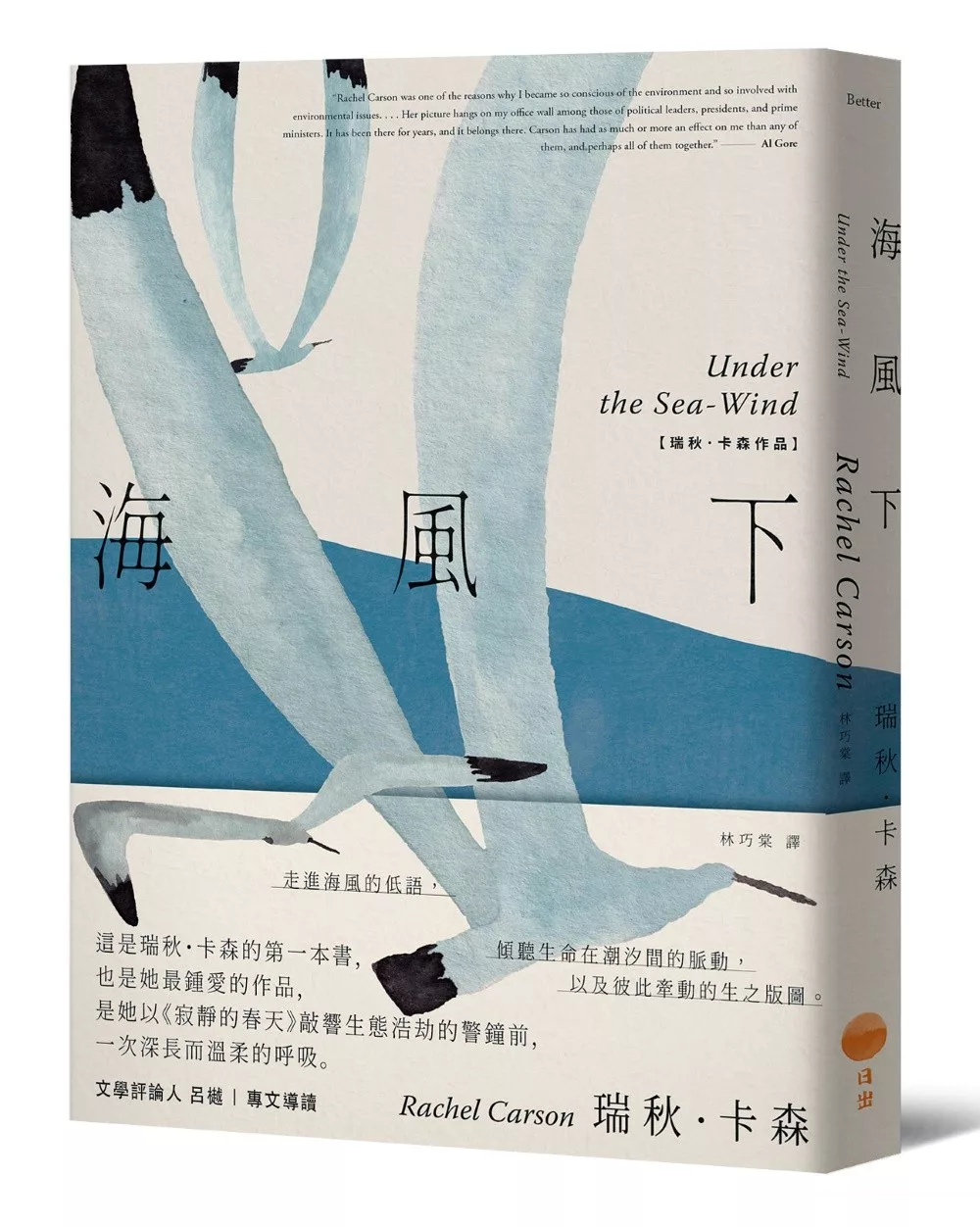導言
?
生命之網的編織者:瑞秋.卡森的整體環境實踐
文�呂樾(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文學評論人)
?
?
一、回望:作為「經典」的瑞秋.卡森
當得知自己將為新譯版《寂靜的春天》(
Silent Spring)與《海風下》(
Under the Sea Wind)撰寫導言時,心中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瑞秋.卡森(Rachel L. Carson)的影響顯然未隨時間淡去,仍有人願意相信這兩本經典在當代依舊蘊含意義。懼的則是,為經典撰寫導言意味著必須直面自書籍出版以降,排山倒海而來的豐厚歷史。尤其如今《寂靜的春天》已然被視為
美國現代環保運動的濫觴,其不只被《發現》(
Discover)雜誌選為「史上最偉大的二十五本科學書籍」之一,更同時被蘭登書屋(Random House)選入二十世紀「一○○本最佳非虛構創作」名單。而卡森本人則在一九八○年被授予美國最高的平民榮譽:總統自由勳章。美國郵政局甚至發行了一枚「偉大美國人」系列郵票來紀念她。如今我們早已慣於以「經典」之姿理解卡森及其作品,但作為一篇導讀,究竟如何在眾多論述之間開闢出一條路徑,串聯起這兩本橫跨二十年的經典之作?
?
二、以毒物將萬物編織在一起
出乎意料的是,在重讀《寂靜的春天》與《海風下》時,人類學家湯姆.范.多倫(Thom van Dooren)的警語始終縈繞我的腦際。他曾在《飛行之道》(
Flight Ways: Life and Loss at the Edge of Extinction)中指出,人們往往將滅絕理解為最後一個個體的逝去,但對他而言,滅絕應被視為一張緊密交織的生命之網逐步鬆脫的過程。此一崩解早在最後一個個體死去之前便已展開,且在此之後仍持續擴散。在多倫筆下,生物從來都不只是孤絕的個體,而是整體關係網絡中同時「影響他者」並「被他者影響」的動態節點。
若說多倫將對滅絕的詮釋由單一個體的死亡,轉向至整體關係的消逝,那麼對我而言,稱卡森為「生命之網的編織者」絕非誇大其辭。她在《寂靜的春天》中透過多年的研究扭轉了大眾的認識,指出了DDT表面上是針對害蟲的殺蟲劑,卻成為了在時間與空間上均具有廣泛影響的整體生物滅殺劑。此一「毒性書寫」以一種反向的方式將人與其環境中的諸多事物重新連結起來,引領讀者看見了DDT的毒性如何流竄於整個生態系中。
這種整體性的環境觀,如今似乎已成社會大眾的常識。我們已然非常容易地想像人類如何棲居於整體環境之中,我們的行動不僅影響環境,也回過頭來影響身處其間的自身與其他非人群體。在這個意義上,「環境」乃是由人與非人共作而出的普遍空間。然而,在《寂靜的春天》問世的一九六二年時,這種帶有整體意涵的「普遍環境」(The Universal Environment)概念尚未成為主流。反而是隨著《寂靜的春天》所引發的一連串社會運動,以及論述推進、理念倡議與法規制定等具體的實踐過程,這一帶有整體性的環境想像才逐步落地生根。換言之,《寂靜的春天》所揭示的「人類共處於同一個有毒的環境中」的觀念,不只促使美國社會正視DDT的危害,並從而間接催生出了一九六九年訂定的「國家環境政策法」(NEPA),更深刻改變了環境運動者對「環境」的理解方式。誠如環境史學者艾蒂安.本森(Etienne Benson)所言,自《寂靜的春天》後,社會運動不再僅關注特定物種、族群或生態系統的具體環境,轉而描繪「所有人類共享的環境」,並由此延伸出「整體生命共同體」的環境想像。
?
三、海風下的生之版圖
卡森的整體思維並非僅限於其科普作品,若我們將目光回溯到其寫於一九四一年的《海風下》,可以發現其書名也已隱隱地暗示了一幅彼此相互交織的生命全景圖。《海風下》的原始面貌並非是一本書,而是一本政府漁業手冊的十一頁序言,名為〈水的世界〉(
The World of Waters)。但當卡森的主管艾爾默.希金斯(Elmer Higgins)讀完後,卻立刻建議卡森將其投稿到當時最富聲望的文學雜誌《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Monthly)。後來發生的事情應證了希金斯的眼光確實毒辣,《大西洋月刊》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將該文更名為〈海底之下〉(
Undersea)後予以刊登,而後卡森更將其擴寫為如今我們所看到的《海風下》。
若將〈海底之下〉與《海風下》並置閱讀,即可發現卡森如何一步步地帶領讀者轉換自身的尺度,改以更為整體性的視角觀看世界。如其在〈海底之下〉的開頭寫道:「若要感知那由海洋生物所熟知的水之世界,我們必須拋卻人類對長度、寬度、時間與地點的知覺方式,設身處地地進入一個由水滲透萬物的宇宙。」此一海洋視角的書寫,在《海風下》中被進一步拓展。除了海洋之外,卡森亦將海岸、天空也予以納入,全書開篇即透過採取了「宏觀」與「微觀」兩種不同尺度的視野的對照,以營造了數學家曼德布洛特(Benoit Mandelbrot)口中「無限長的海岸線」。如書中所言:「這是一個小到海鷗只需振翅十幾次便能飛越的島嶼」,然而當我們把觀察的尺度微縮,可以在上述空拍視角下一眼望穿的海岸線,在微觀的視角下卻如此生機盎然。相較於《寂靜的春天》中反向連結的「毒性書寫」,《海風下》則透過了「伶巧」、「銀條仔」等海鳥、鯖魚「史康波」與鰻魚「安圭拉」三種不同的微觀視角,帶領觀眾體會他們出生、成長、遷徙的動態過程,以及圍繞在他們生命周遭,彼此牽動的生之版圖。
?
四、在地回聲:瑞秋.卡森與臺灣自然書寫
不過卡森所編織的生命之網並非僅限於美國的語境,更以一種伏流之姿影響了臺灣的自然書寫與環境運動。《寂靜的春天》自一九六九年在臺灣《中央日報》副刊分章連載,但在當時並未引起過多的關注。但到了一九七○年代末,陸續有社論引用該書回頭討論臺灣公害現況,並直接、間接地啟迪了諸多臺灣自然書寫者。如臺灣環保運動的先行者林俊義教授,即透過《寂靜的春天》在美國的迴響,作為臺灣環境運動的參考目標。而在《我們只有一個地球》(1983)中,馬以工亦援引了卡森關於「生態平衡」的呼籲作為恆春半島候鳥保育行動的訴求對照。另外,當張系國在為該書撰寫導言的時候,盛讚《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有別於當時報導文學見樹不見林的空洞形式,反而透過生態議題的倡議,提出了一個「整體宇宙觀」。雖然我們無法確認《我們只有一個地球》是否直接受到卡森的影響,但有趣的是,由此可以看出《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如何透過了「整體環境」的勾勒而隱隱與《寂靜的春天》相互呼應。
另外,劉克襄也曾在訪談中指出,由於受到了卡森的影響,以及九○年代引進臺灣的深層生態學影響,認為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那種孤僻、疏離的接觸自然方式已無法說服自己,故轉往更為現實且平民化的生態問題。同時,《海風下》與《海的故事》也促使其思考自己作為一個自然寫作者,究竟與世界的關係是什麼。
吳明益亦曾指出,直至《寂靜的春天》被翻譯來臺後,臺灣才逐漸出現結合自然科學、生態學、環境倫理與文學的「現代自然書寫」(modern nature writing)。而在《家離水邊那麼近》(2007)中,吳明益更揣想卡森會如何回答「海洋是否擁有記憶」的問題,並詩意地寫道:「她(卡森)會說,海的記憶是一種集體記憶,留在地質變動與演化的每一項細節上;留在魚族、軟體動物、海流,或一枚石頭上。」
誠如吳明益所言,如今的我們多半早已將《寂靜的春天》(或也包含其本人?)視為一個「經典」來理解。然而,若以更微觀的角度重新切入卡森的思考與實踐,會發現她為我們留下的遺產,或許遠超過文字本身,且至今仍餘波盪漾。卡森揭示的,不僅是毒性的蔓延與生態的觀察,更展現了一種理解世界的方法論,即從局部通往整體,並從具體的生命觀察抵達倫理與形上學的思考。而若要選擇一個在當今回望卡森的理由,或許並非將她與其作品封存為經典,而是學習她編織生命之網的姿態,並謙遜地學會如何棲居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