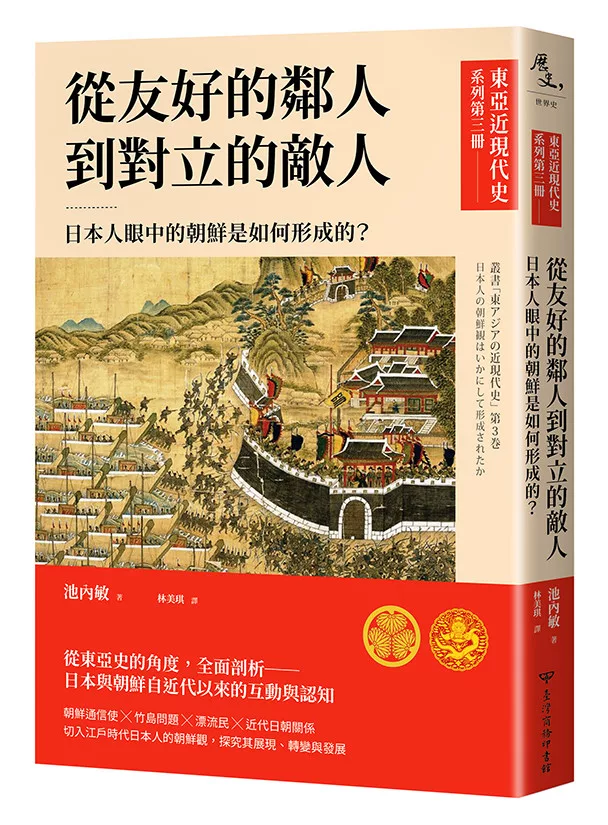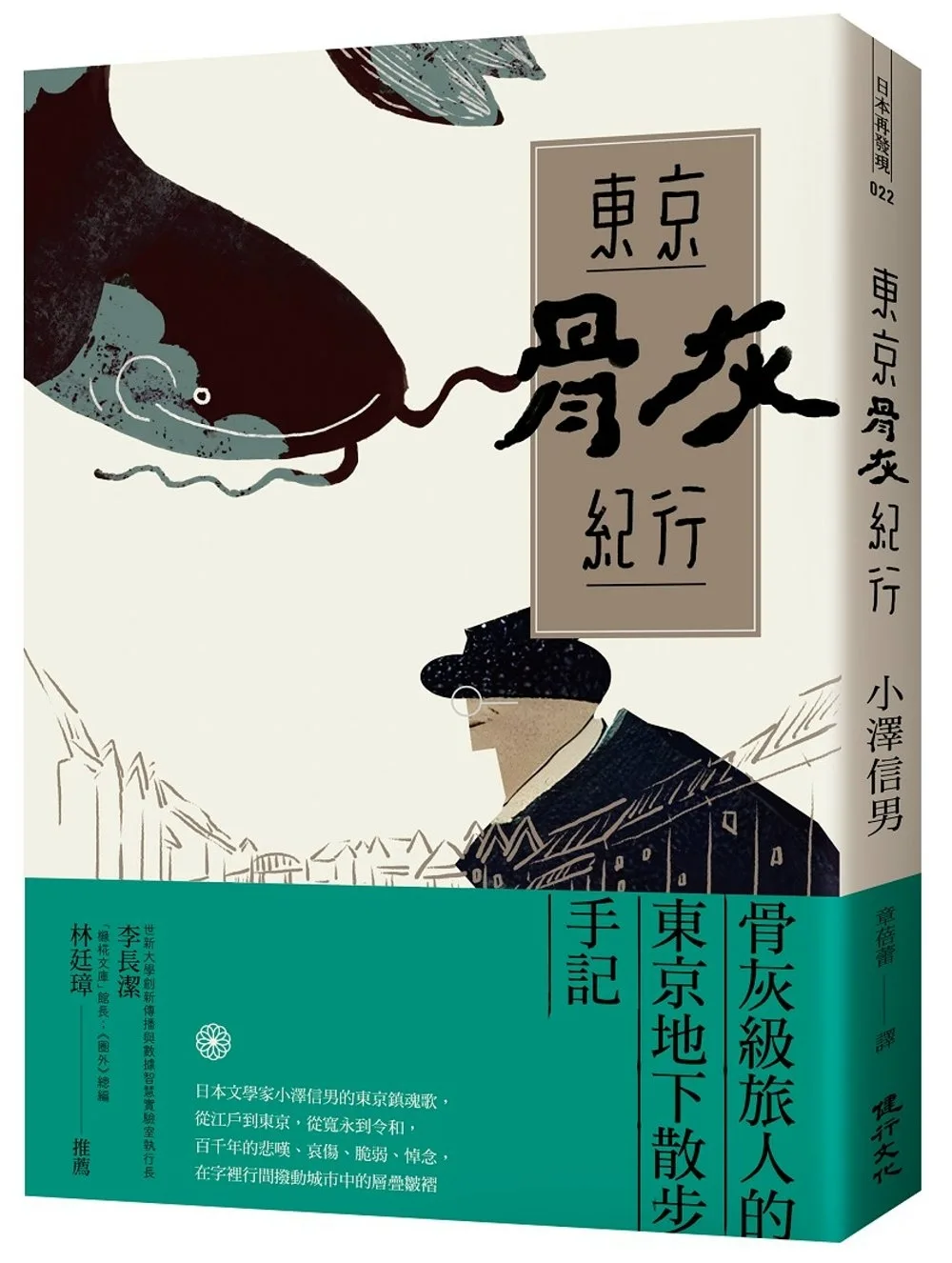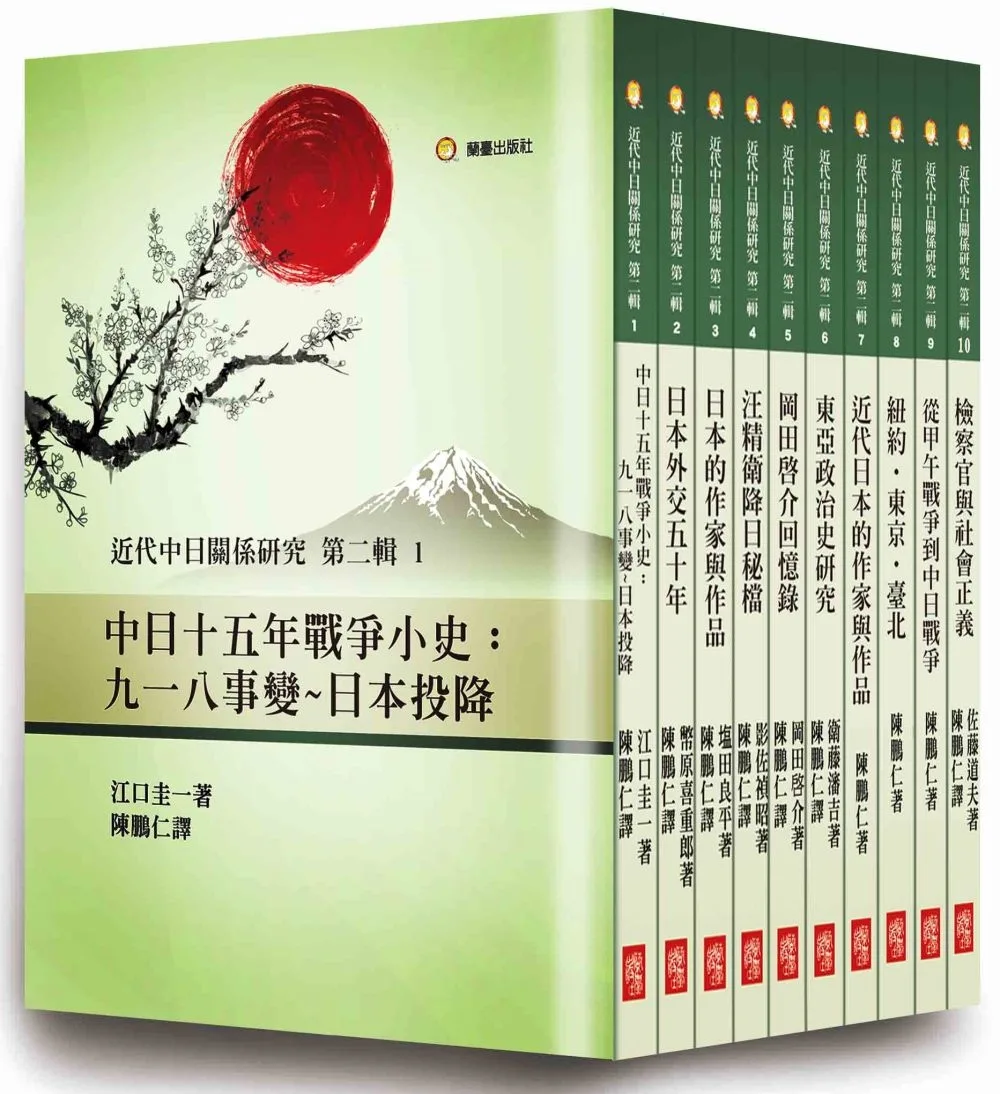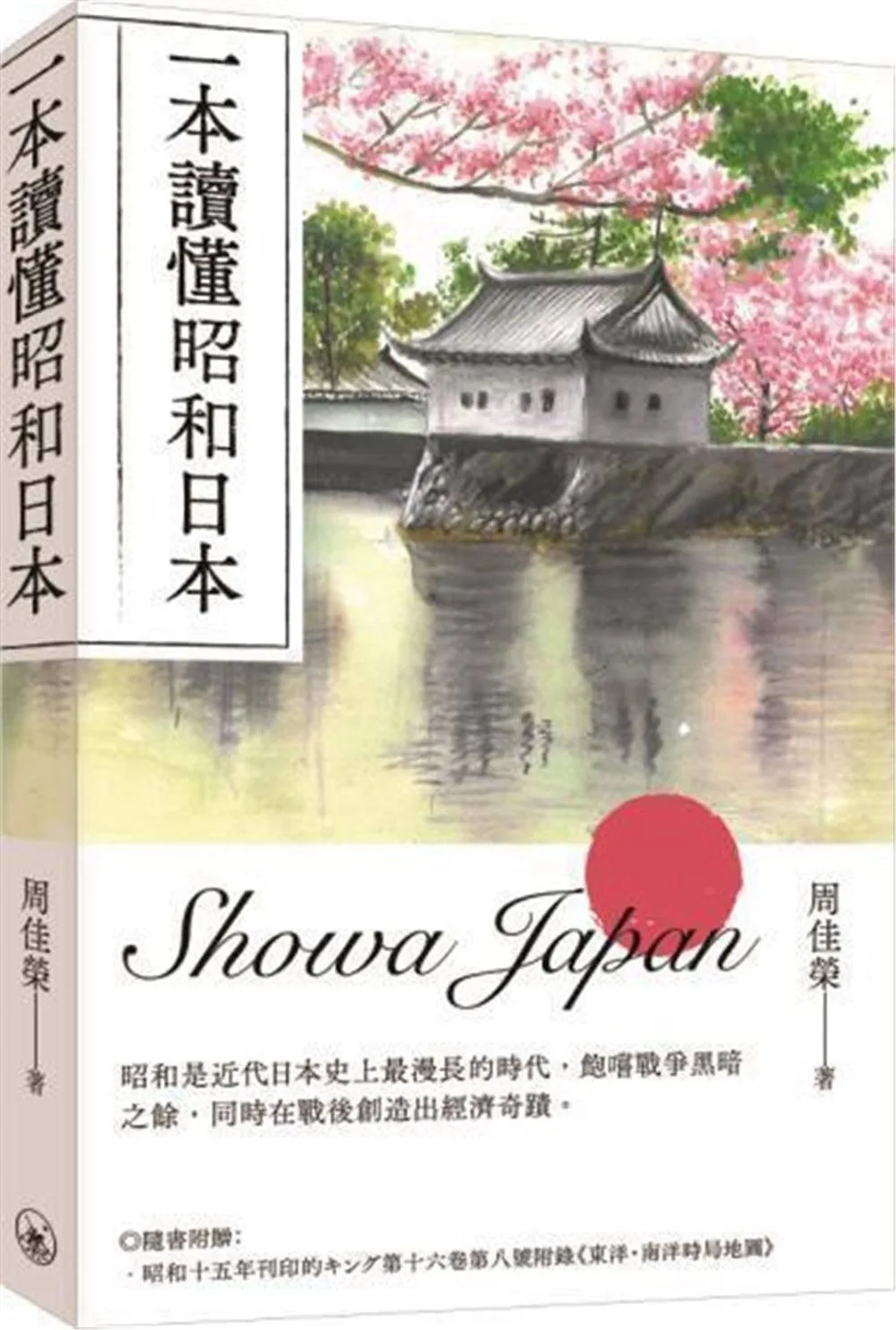?前言
「鮮人」與「朝鮮人」
「北鮮」、「南鮮」以及「鮮人」這些詞彙,常被視為對朝鮮與朝鮮人帶有蔑視的用語,即所謂的「蔑稱」。這些詞彙曾被認為是在一九一○年韓國被日本合併之際,由統治者所創造出來的「支配者語言」。於是,像「滿鮮」、「渡鮮」等用法,也可解讀出某種鄙視之意,進而以是否使用這些詞語,來衡量一個人是否帶有歧視朝鮮的觀念。
另一方面,在整個殖民統治時期,即使是「朝鮮人」、「韓人」這類看似中性的詞語,也往往帶有蔑視意味。我們不妨看看以下這段文字(畫線部分為引用者所加,若無特別註明,以下皆同):
?
某日,我難得有了空閒,在星野的帶領下走進韓人街。幾乎家家戶戶都是朝鮮人開的小店。忽然,我看到一家店門口,有日本小孩與朝鮮小孩正在用半日語半朝鮮語交談玩耍。仔細一看,那其實是家日本人經營的小店,店裡陳列的東西也如同朝鮮人的店鋪般貧窮破舊。不過商品擺設比朝鮮人還來得整齊些,略顯不同風味。店內坐著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子,穿著髒兮兮的日式衣服,束著細細的腰帶。她左手拿著一面小鏡子,右手則用梳子整理沾滿灰塵的頭髮,那是個髮根垂下的「蝴蝶髻」。星野皺著眉頭說:「變成這樣的話,日本人反倒被朝鮮人化了。」但我環顧四周,在這個朝鮮小城,無論所見所聞,全都充滿朝鮮風情。日本人也過著與朝鮮人一樣骯髒貧困的生活,然而他們仍穿著日本服裝、綁著日本式髮型,在灰塵滿布的環境中梳整頭髮。因此,我並未完全相信星野的說法。
?
這是高濱虛子於一九一一年在《大阪每日新聞》等報紙上連載的小說《朝鮮》中的一段。文中雖反覆使用「韓人街」、「朝鮮人」、「朝鮮語」等詞彙,並未出現「鮮人」,但即使僅從這段描寫中,也能強烈感受到一種高高在上、俯視朝鮮與朝鮮人的態度。小說中「朝鮮」的假名標註為「????」(teusen),而星野所說的「朝鮮人化」則標註為「???」(yoboka)。這裡的「??」(yobo)也是當時日本人對朝鮮人常用的蔑稱。
此外,歷史學者喜田貞吉於一九二○年前往「京城日出小學」演講前,曾接到一項提醒:「請盡量避免使用『殖民地』或是『朝鮮人』、『鮮人』等詞彙,因為當地人會反感。」(喜田貞吉《庚申鮮滿旅行日誌》)。山田昭次也指出,農民詩人遠藤源一郎在一九二○年代後期的詩作與日記中,選擇使用「朝鮮之人」這種說法,避免使用「鮮人」與「朝鮮人」,這是因為他已意識到這些詞語蘊含的歧視意味。詩人秋山清也回憶道:「過去一直把『朝鮮人』這個詞當作侮辱來使用,然而戰後朝鮮獨立,本應理所當然要稱呼為『朝鮮人』的時候,我卻做不到,不小心說成了『朝鮮的人』。」因為這件事,他曾被中野重治嚴正指責,要求他應當正確地稱作「朝鮮人」。此外,在一場題為「日本文學中的朝鮮觀」的座談會中,四方博表示:「我們在戰前盡量避免使用『朝鮮』這個詞」、「即便戰後初期,說出『朝鮮人』時仍會感到抗拒,但如今已能毫無偏見地使用這個詞了。」這些談話,都清楚地呈現出戰後初期日本社會對「朝鮮人」一詞的使用抱持著某種猶豫的氛圍。
前面提過的山田昭次也曾指出:「『朝鮮人』這個詞原本並非歧視語,但在近代日本,它卻轉化成了歧視性用語。」而中野重治的言論也同樣明確指出,「朝鮮人」這個詞本身並無歧視意涵。可見,是圍繞這個詞的社會語境,使它最終染上了岐視的色彩。
缺乏對蔑稱的自覺
日本人於殖民地時期普遍使用的針對朝鮮及朝鮮人的稱呼,隨著時間流逝,已逐漸失去了對這些詞語為蔑稱的意識。這種「不自覺的使用」甚至延續到了戰後。有一個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便是經常被人們提起的岩波書店出版的《廣辭苑》所引發的爭議。事情是這樣的:一九五五年《廣辭苑》初版將「北鮮」、「鮮人」列為詞條。後來,由於外界的抗議,到了一九七○年秋天發行的第二版第四刷中,這本詞典修改了「北鮮」詞條的內容,並且刪除了「鮮人」這個詞條。
針對這一修正,有人提出嚴厲的批評,認為:「《廣辭苑》……僅為了從第二版第四刷中刪去『鮮人』二字,竟花了戰後二十幾年的時間。」或是指責說:「(岩波書店)長達十六年來一直在擴散歧視,卻從未試圖承擔責任。」然而,如果考察實情,對這個問題反應最快、也最為敏銳的「日本朝鮮研究所」,是在一九七○年7月才對岩波書店提出抗議,而岩波書店也在同年秋天的第二版第四刷中進行了修正。從時程上看,岩波書店的應對其實不算是怠慢。此外,日本朝鮮研究所對這個問題的察覺,似乎也不是早於一九七○年很久以前就已經開始關注的。既然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年間,無人察覺《廣辭苑》存在這樣的問題,也無人提出抗議,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責難若只單單指向岩波書店,恐怕並不公平。
事實上,整個一九六○年代中,即便在日本朝鮮研究所發行的《朝鮮研究》期刊中,有論文使用了類似「鮮人」這類「蔑稱」,也從未引起問題或爭議。除了極少數例外,對朝鮮人蔑稱的敏感與關注,其實是從一九七○年代才開始逐漸浮現的。這股關注風潮的開端,應可追溯至一九七○年齊藤力所發表的兩篇文章:〈稱呼「北鮮」者的真面目〉以及〈《廣辭苑》所列「北鮮」詞條的錯誤〉。緊接著,內海愛子於一九七四年發表〈關於「鮮人」這個詞〉一文,延續這一波的反思與批判。
此外,一九三七年出生於高知縣的在日韓國人姜琪東(又作姜基東),曾於加藤楸?主編的俳句雜誌《寒雷》發表一句作品:「鮮人敲著火盆,悲泣起來」。隨後作家李恢成致信指出:「使用『鮮人』這個詞並不恰當,即使字數超過了限制,也應寫作『朝鮮人』才對。」這首俳句刊載於一九七一年5月號,可以推知李恢成的批評也是在那個時候提出的。像這樣針對用詞的質疑與提醒,若非進入一九七○年代,是不太可能被公開提出的。包括「北鮮」、「南鮮」、「鮮人」,以及「滿鮮」、「渡鮮」這些詞語在內,曾在殖民地時期用來貶抑朝鮮人的歧視意涵,一度被人遺忘,直到一九七○年代才被「重新發現」而揭露出來。
《漂流朝鮮人之圖》
讓我們把話題轉換一下。一九九三年,當時在鳥取縣舉辦了中國五縣總務部長會議。會場選在仁風閣寶隆院,當時擔任鳥取縣總務部長的片山善博(後來成為鳥取縣知事,現任早稻田大學教授)便思索:是否能在寶隆院的「床之間」中懸掛一幅合適的掛軸,為會議增添些許象徵性?片山善博向鳥取縣立圖書館館長濱崎洋三(已故)請教,濱崎洋三便推薦了館藏中的《漂流朝鮮人之圖》掛軸。片山善博採納了建議,將這幅畫掛在寶隆院中。他後來回憶道:「當時鳥取縣正打算以面向日本海的視角,展開環日本海時代的各項發展策略,而這幅畫,正好象徵這樣的方向與精神。」這幅掛軸的內容由三個部分組成:一是描繪文政二年(一八一九年)有十二位朝鮮漂流民漂流至鳥取藩領的畫像;二是其中一位名為安義基的漂流民,寫給鳥取藩士岡金右衛門的漢文感謝信;三是安義基以韓文記述的漂流經過。對此,濱崎洋三表示:「比起單純畫工精緻、藝術價值高的作品,我更希望挑選一件在內容上更適合總務部長會議精神的掛軸來展出。」片山善博也補充說道:「自近代以來,日本與韓國之間的關係一直相當複雜且緊繃。但這幅掛軸展現了日韓交流的起點,我覺得其中蘊含一種將兩國關係引導至更好方向的可能性。」
如今已合併為一幅畫的《漂流朝鮮人之圖》,其實最初是分成三部分流傳的。它首次對外公開展示是在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年)7月,當時韓國皇太子造訪鳥取,這三件作品才被裝裱成一整幅畫,並且首次公開亮相。這些在十九世紀漂流事件不久後所創作的圖畫與文字,原本已被塵封遺忘,直到韓國皇太子來鳥取拜訪才展示出來,之後又再次沉寂,一直到一九九○年代初,才由鳥取縣立圖書館進行修復並收進地下書庫。這段歷史,因為一次總務部長與圖書館長的簡單對話,而重回眾人眼前。這也是「遺忘與重現」的一個具體案例。而這種「重現」,總是需要背後的契機與脈絡。對於「朝鮮」的觀點與想像也一樣,那往往取決於表達者當時所處的背景與立場。換句話說,某種觀點若出現於某個時期,也未必會原封不動地流傳下去。
日韓交流的源流調查
隨著「漂流朝鮮人之圖」重新浮現於世人眼前,一項尋找畫中那十二位朝鮮漂流民後代的調查行動也悄然展開,就是鳥取縣所推動的「日韓交流源流調查計畫」。一九九四年11月,時任總務部長的片山善博與圖書館長濱崎洋三,率先前往韓國慶尚北道蔚珍郡,也就是這些漂流民的故鄉,展開實地調查。此後,相關地區的資料調查也陸續進行著。濱崎洋三回憶這項事業的起點時曾說:「如果感謝狀上的收件人岡金右衛門與安義基船長的後代能在鳥取重逢,不僅會讓這幅掛軸的價值大增,更將象徵這件文物牽起跨越一百八十年的相逢,有助於深化今日日本與韓國,甚至江原道與鳥取縣之間的情誼。」
一九九六年,濱崎洋三在任上與世長辭。之後在一九九九年,片山善博就任鳥取縣知事,這項事業也由縣政府持續推動,成立了「連結二十一世紀的日韓交流源流探究檢討委員會」,正式延續原有的調查計畫。二○○○年4月,由時任總務部長的平井伸治(現任鳥取縣知事)擔任團長,第三次造訪蔚珍郡的調查也順利展開了。參與這次行動的?本敬司(當時為鳥取縣立博物館學藝員)如此回顧道:「雖然我們這次仍未能確認那十二位漂流民的後代,但一些具體的歷史資料與後續的調查方向已逐漸明朗。在調查過程中,各地民眾對鳥取縣這項努力都表達了高度的關心。我也能感受到,韓國有越來越多人開始意識到日韓交流的重要性。這次的經歷,讓我更加喜歡韓國了。」
本書的視角
本書以江戶時代的日朝關係史為核心,探討自十六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這段時期中,日本人對朝鮮的觀感是如何展現、轉變與發展的。起初,筆者原本是以「日本人對朝鮮觀念的歷史性形成」為構想出發點,但在深入研究後,我認為將前近代的身分制社會下的朝鮮觀,與近現代實現了形式上四民平等後的朝鮮觀直接連接,並不恰當。因此,與其稱之為「歷史性形成」,不如將重點放在探討「不同時代下,其觀點表現形式的差異」。基於這樣的考量,本書的敘述並非嚴格依循時間軸展開,而是盡可能以各章自成一格、彼此獨立的「類專題集」形式呈現。更重要的是,本書不將日本人的朝鮮觀視為一種固定不變的認知,而是當作一種隨時間而變化(被遺忘、又重新被發現)的歷史現象來理解,同時也關注它在不同地域所呈現的差異。這樣的觀點,正是筆者長年研究近世至近代日朝關係史的累積成果所孕育出來的視野。本書也試圖在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重新整理並以「日本人對朝鮮的觀感」為核心視角進行闡述。除了終章外,讀者可從任何一章開始閱讀,並不會影響理解。
近年來,我們時常看到一股風潮,無視歷史學(文獻史學)的基礎方法論,隨心所欲地談論歷史。這種現象的特點是:人們根據自己偏好的劇情來排列史料,並將論點導向他們事先期待的結論。在這樣的趨勢中,往往潛藏著一種錯誤認知:認為不需要經過專業訓練,任何人都能輕易地讀解與詮釋史料。這種對專業性的輕視,也與整體社會對人文學科的輕視相呼應。本書的敘述雖不必然依循時間順序展開,卻是透過歷史學的閱讀與詮釋,逐一確立其內容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