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價99.00元
-
8
折優惠:HK$79.2

|
|
|
|
自由之夏 Freedom Summer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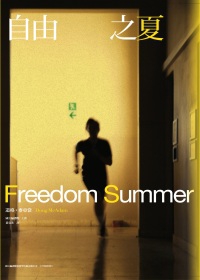
|

沒有庫存
訂購需時10-14天
|
|
|
|

|
|
9789866525391 | |
|

|
|
道格.麥亞當 | |
|

|
|
黃克先 | |
|

|
|
群學 | |
|

|
|
2011年3月25日
| |
|

|
|
167.00 元
| |
|

|
|
HK$ 150.3
|
|
|
|
|

| |
|
|
|
|
| |
|
|
詳
細
資
料
|
* 叢書系列:社會書
* 規格:平裝 / 528頁 / 15*21 cm / 普級 / 單色印刷 / 初版
* 出版地:台灣
社會書
|
|
分
類
|
人文史地 > 世界史地 > 地區史 > 美洲地區 |
同
類
書
推
薦
|
|
|
其
他
讀
者
也
買
|
|
|
內
容
簡
介
|
@本書榮獲1988年Gustavus Myers中心頒發美國非暴力議題最佳書籍獎。
「每一天發生的每樣事對我來說都是全新的。資訊不斷轟炸著我,經驗不斷轟炸著我……而我衰微的精神狀態幾乎要失控了。」
「你感覺自己將參與這歷史性一刻;在一區域中,整體生活模式裡很深刻的某項東西即將要轉變……你正在……創造……歷史。從某些方面來看是全然無私無我的,但(你)也同時發現了自我。」
「它讓我欣喜若狂……第一次這些片段碎塊嵌合在一塊……感覺像我自己……我認為透過它,我們不但成就了些事,也是實現我個人的救贖。」
「它是我人生中最長的夢魘:三個月──一九六四年的六月、七月、八月。」
本書即是詳述這個撼動美國六○年代,歷時不到三個月的「自由之夏」運動(Freedom Summer)。這段期間,超過一千人聚集至美國密西西比州,共同居住在「自由之家」,或寄住在當地不懼種族隔離主義者威脅的黑人家庭中。計劃期間,難以緩解的恐懼、令人苦惱的貧困,以及間或發生的暴力事件,都困擾計劃的進行,最後造成四位自願者被毆打致死、八十位自願者受傷、一百位自願者被逮捕,並有六十七間教堂、房屋及商店被砸毀或焚燒。這個夏天是每位參與者心中難以磨滅的經驗,他們的生命被改變,進而撼動整個世代。
「自由之夏」是美國社運的重要轉捩點,透過它所引發的文化與政治效應,孕生了日後其他重要運動,包括女權運動、反戰運動、學生運動等。自由之夏不僅為六○年代眾多行動主義的嘗試提供了組織基礎,同時也關鍵性地推動這個時代茁生的反文化思潮發展。
作者簡介
道格.麥亞當(Doug McAdam )
現任史丹佛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曾任教亞歷桑那大學社會學系,著有《1930-1970年間的政治過程與黑人叛亂的發展》(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 1982)、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與John D. McCarthy、Mayer N. Zald合著,1996)、Social Movements: Readings on Their Emergence, Mobilization, and Dynamics(與David A. Snow合著,1997)、Making Connections for Africa: Report from a Constituency Builders’ Dialogue(與Imani Countess、Loretta Hobbs、William Minter、William Minter合著,1997)、Dynamics of Contention(與Sidney Tarrow及Charles Tilly合著,2001)、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與Ronald R. Aminzade、Jack A. Goldstone、Doug McAdam、Elizabeth J. Perry、William H. Jr Sewell、Sidney Tarrow、Douglas McAdam、Charles Tilly合著,2001)、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Voluntary Youth Service: The Case of Teach for America(與 Cynthia Brandt合著,2010)。編有How Social Movements Matter(與Marco Giugni、Charles Tilly合編,1999)、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Relational Approaches to Collective Action(與Mario Diani合編,2001)、Social Movements and Organization Theory(與Gerald Davis、W. Richard Scott及Mayer N. Zald合編,2005)、Readings on Social Movements: Origins, Dynamics, and Outcomes(與David A. Snow合編,2009)。
譯者簡介
黃克先
西北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著有《原鄉、居地與天家:外鄉第一代的流亡經驗與改宗歷程》(稻鄉出版,2007),譯有《泰利的街角》(群學出版,2009)、《社會資本》(與黃惠茹合譯,巨流出版,2008)、《客人?外人?遷移在歐洲(1800~)》(巨流出版,2006)、《上帝有個夢》(雅歌出版,2005)。
|
|
目
錄
|
階誧ョ@道格.麥亞當
序:本書對台灣社會(學)的啟示 王甫昌
序 幕 尋找志工
第一章 自由之夏發生前的美國
第二章 參與運動的個人生命故事根源
第三章 自由的高潮:夏季,一九六四
第四章 盤點收穫:自由之夏的立即影響
第五章 應用密西西比所學
第六章 恍若隔世:七○年代及其後
跋 盡情照亮
附錄
原書注釋
參考書目
索引
|
|
序
|
階誧?
道格.麥亞當(Doug McAdam)
按: 《自由之夏》成書於我在亞歷桑那大學任教之初。當時, 我曾與許多有才華的學生一同做研究, 王甫昌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在一九八四到一九八九年間於該大學攻讀其博士學位。甫昌於一九八九年取得博士學位後, 隨即返台在中央研究院內任職。從那時起,他將大多數的研究精力投注在分析台灣自一九八○ 年代起在政治及文化上發生的鉅變, 開啟了令人矚目的研究生涯。由於他研究關注的議題及長期投入的淵源, 所以當群學出版社邀請我為《自由之夏》的中譯本撰寫序言時, 我腦中立刻浮現了甫昌的名字。我提出了與他一同合作的構想, 希望先由我簡要回溯本書的歷史及摘錄其中的主要命題後, 再由甫昌把這些命題應用到台灣近年來的歷史。我很感謝出版社同意了這個較不尋常的提議,同時也謝謝甫昌慨然允諾共同撰寫這序言。
我想研究一九六四年自由之夏計劃的想法是來自我的第一本書《1 9 3 0 — 1 9 7 0 年間的政治過程與黑人叛亂的發展》(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一九八二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我撰寫該書的動機有二。首先,深信當代的民權運動乃是美國歷史上一項重要分水嶺的我,很想了解它的源起及後來的發展,乃至於最後如何劃下句點。其次,我希望藉由這個實例能發展出一個社會運動的一般性理論,也就後來我所謂的政治過程論。然而,在從事研究的同時,第二本書的構想卻開始在我心中成形。在研究民權運動的時候,我很驚訝地發現很多後來在該時期的各種運動(例如女性解放運動和反越戰運動)內擔任要角的領導者,都是在民權運動中經歷了他們的社運初體驗。當時我還不知道這種情況竟是如此普遍。我自問,想了解美國在一九六○年代及七○年代初社運百花齊放的現象,關鍵是否就在理解這群在民權運動中變得基進化的人後來如何把在其中學到的應用到他們認為相關的各類議題上(如美洲原住民、西裔美國人、女性、男女同志及殘障人士的權利)?我便決定在下一個研究計劃裡探討這個問題。
當時面臨的挑戰是該如何找到能有系統地研究該問題的方法,也就是說,我當然可以找到一群曾在民權運動中受過訓練而後成為其他運動要角的人,但這不過告訴我們,這種情況是很普遍的事實罷了。我需要找一個更具系統性的經驗事實來做為這個仍在構思之計劃的出發點。這就是為何鎖定自由之夏計劃的原因。
原本簡稱為「夏日計劃」的自由之夏運動,發生在一九六四年。在那個夏天,有將近一千名, 主要是白人北方大學生組成的志工被招募到密西西比州,從事黑人選民登記、在「自由學園」內任教及──最重要的是──將非裔美國人一直被拒絕享有基本民權的事實給戲劇化地呈現出來。最終, 該計劃在整個夏季成為了全美國各地的頭條新聞。三名擔任志工的學生在計劃開始的第一週就被綁架並謀殺,幾個月後屍體才被找到。總共有四名志工在夏日期間喪命,另有八十位身受重傷。整個夏日期間,有一千位參與計劃的人被逮捕,總共有六十七所黑人教堂、住家及商店被焚燒或炸毀。在這一個充滿不少值得一書的事件的十年期間,自由之夏算是其中最戲劇化的一個。
但是,我之所以選擇夏日計劃並不是因為它這種極具戲劇張力的特質,而是是因為它是許多白人大學生進入社運過程中最早的一段經驗。因此,該計劃即成為了研究民權運動及稍後各項社運之間連結的絕佳起點,但前提是我得先找到一份上頭列有在一九六四年參與該計劃人士的名單,更樂觀的期盼是,這份參與自由之夏者的名單上頭最好也能列出他們當時就讀的大專院校。我計劃透過這些學校的校友聯誼會取得志工們目前的住址。不過要能進展到這一步,前提是得先找到那樣的名單。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與收藏民權運動或新左派文獻資料的各大圖書館或檔案庫連繫。然而,每個單位給我的回覆都是如此:當初這個計劃結束的很倉促,所以來不及集結出一份志工的完整名單。當時, 我幾乎要放棄尋找這份遍尋不著的名單的希望,然而,還是決定到南方進行最後一趟研究行程,拜訪最後幾個當地的研究機構。我的第一站是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市的馬丁路德金恩紀念中心(Martin Luther King, Jr. Center)。那裡給我的答覆基本上與其他地方大致一樣,只有一點是不同的。中心的圖書及檔案庫的主任庫克(Louis e Coo k)告訴我在後面的房間內還放有一些未匯編的原始資料,歡迎我去看一看。在那裡, 我找到了比我遍尋的夢想名單更完美的東西: 志工們在夏日以前所填寫的原始申請資料,以英文字母的順序排列成一疊檔案。更理想的是,除了當初參與計劃的志工的申請資料外,我還發現了另一疊同樣以英文字母順序排列的申請資料, 這些申請者當初提出參與計劃的申請,也被計劃負責人審查通過,但最後因為某些因素而未前往密西西比。事實上, 我竟然無意中發現了這個渾然天成的自然主義實驗設計:五頁的「實驗前」的資料,包含了志工本身以及另一群可被當成理想控制組的未現身者。日後, 在仔細檢視過兩群人的申請資料後,我發現他們彼此之間其實在夏日之前看起來並沒有什麼差異,但一群人經歷了自由之夏,而另一群人沒有。一個雖然看起來簡單但卻很有意思的問題便浮現出來:參與或未參與這個計劃如何形塑志工及未現身者的生命?
如今,眼下的研究問題變為兩個。除了我原先想了解的當代社會運動之間的連結之外,另一個新的關注點則在參與社會運動對個人生命歷程的影響。然而,隨著研究的開展,我們發現這兩個表面上看來不同的問題,實際上卻是緊密地相互關連著。問卷調查及訪談資料都證明了志工們日後的生命歷程中明顯承載了自由之夏經驗的痕跡。他們的生命在夏日之前與未現身者看來並無差異,但在之後卻明顯分道揚鑣。事實上,夏日計劃變成了志工們社運上的「基礎訓練」。這群志工在離開密西西比之際已有所改變,同時因著在該州的經驗而變得極為基進。
然而,以上只是我在《自由之夏》中所暢述之故事的一半。把他們在密西西比學到的付諸實行的同時,志工們也積極地捍衛自身權益,改變周遭的情況。誠如本書中詳細記載的情況那樣,志工們協助美國所謂的六○年代現象遍地開花。他們所做的事中首推在那個年代其他的新左派運動裡扮演主要的領導角色。一些回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的學生決定要繼續支持在密西西比的運動,於是他們在校園裡擺起了攤位來募捐支持該州運動的善款。校方卻威脅學生說如果再繼續這麼做就要逮捕他們; 於是, 言論自由運動應運而生,並成功地催生了全國各地的學生運動。自由之夏計劃結束還不到三個月,有兩位女性參與者寫下了一份匿名的意見報告書,批判了在夏日期間她們所見證到的各種性別歧視現象。這份文件批判的對象正是這群以男性為主的讀者,他們閱讀後莫不報以訕笑及輕蔑。這二位女性──金(Mary King)與海登(Casey Hayden)──對這些反應甚感憤怒,於是又寫了一篇立論更明確且篇幅更長的文章來反擊在運動中的性別主義,這次她們更明確署名。據此,女性解放運動應運而生。最後, 由於密西西比的經驗使得志工們覺察到種族主義無所不在,不少志工回到北方後將分析種族問題的視野帶入了勃興的反戰運動內,更激化原本對越戰不滿的怒火。有位志工曾這麼說:「(在密西西比之後)我記得曾這麼想過,黑人為了白人的利益去打亞洲人,但同時他自己的兄弟卻在家鄉被殺害,這樣的戰爭實在不值得去支持。」(本書英文頁碼 172)
一般對六○年代歷史常見的解讀是將蓬勃之學生運動的濫觴追溯到一九六四年的秋天,然而很多史家卻沒有發現這股風潮與自由之夏計劃之間的關聯。這群返回北方的志工就是失落的連結。基本上,他們開啟了後來美國新左派全面的發展。總結來說,微觀層次的個人轉變以及鉅觀層次的社會變遷之間的緊密連結,正是統合自由之夏這個故事兩條軸線的關鍵所在。只是,這樣的故事在這個時期並非僅發生在美國。每當我們看到一個社會與政治產生巨變的時代來臨時,你可以想見我們也將發現見證個體轉變與社會變遷之間緊密連結的證據。分析到最後,人不但是變遷下的產物,也是締造變遷的行動者。美國在六○年代及七○年代初期見證了這種連結,而台灣也在九○年代及其後經歷了十分類似的情況。六○年代之於美國一如九○年代及二○○ ○年後十年之於台灣,是一個針對台灣社會根本的政治與社會結構進行不斷且影響深遠之辯論的年代。本序言的下一部分正是想將《自由之夏》的分析架構應用到一九九○年後台灣經歷的政治變遷與個人轉變上。
麥亞當(Doug McAdam),二○○九年十月,帕羅奧多市,加州
序
本書對台灣社會(學)的啟示/王甫昌(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麥亞當在《自由之夏》一書中所傳遞的最重要的兩個信息,是一九六四年「自由之夏」計畫的學生參與者,在參加該運動之後,終生在個人生命軌跡上所受到的影響,以及這些參與者後來繼續參與的幾種社會運動(包括「婦女運動」、「反戰運動」、及「民權運動」),對於美國社會產生的深遠影響。
這本著作清楚地說明了,當年這些參加運動的學生並非只是出於「年少輕狂」,而是有相當的自由主義精神為動機;參與之後,也不是「船過水無痕」,反而對他們的生命發展的路徑造成永遠的改變。這項活動經驗給予他們的影響,主要有兩方面,一是他們確立了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二是他們結識了一群曾經一起共患難、志同道合的朋友。這兩項特質在他們在回到原有生活環境以後,逐漸對他們後來的生活走向發生影響。
為了堅持其理想, 許多運動參與者選擇了比較非傳統性的就業型態, 包括擔任社會運動團體的工作人員、較晚進入就業市場、也選擇「人文社會」或助人的行業與工作。由一般世俗的角度來看,他們似乎繼續在為理想付出個人的代價。當然,也有不少參與者將最初對於人權運動理念的堅持,轉移到其他的社會運動,進而成為這些後起的社會運動之核心領導者。
本書最重要的貢獻,主要在於反駁當時美國大眾傳播媒體上,經常刻意強調這些當年的學生運動參與者,在十多年後多半都已經回到社會主流或體制內的角色扮演,以凸顯他們當年因為「年輕的叛逆」而參與運動的詮釋或定位。這種詮釋的重要暗示在於:這些運動參與主要是在解決參與者個人的心理問題,不論是疏離、叛逆,或是代溝,因此其所宣稱或支持的「反體制運動」目標本身並不重要。本書指出這種主流媒體的印象過於刻板化,而且往往忽略了參與者在運動過程受到的啟發與改變。這或許是一般多半專注於探究社會運動的「崛起」,而較少注意運動(或參與者)「發展」的議題,這樣的研究取向,很容易產生的聯想。
更重要的是,透過對於四百多位當年參與者在活動結束二十年之後,所做的有系統性的追蹤訪問(此項研究進行時,受訪者已經散居全美各地,其難度可想而知),再和當年他們在申請參加活動時,所填寫的申請表與政治態度問卷表相比較,本書提供了比凸顯若干個案的新聞報導更為全面而有力的反駁證據。誠如何希特(Michael Hechter,當年也是亞歷桑那大學社會系教授)在推薦這本書時所說的:「我們終於有了一本討論六○年代政治的書籍,是根據紮實的資料,而非只是內省或理論性的猜想而已。」
過去我在開授「社會運動」的課程時,每次都將這本重要的著作,列為討論「社會運動的發展: 參與運動對個人的影響」這個主題時,主要的參考著作。我在回台灣任教後,一九九○ 年春季在政大社會系第一次開授這門課時,正逢「三月學運」期間,台灣大學生在中正紀念堂靜坐抗議的活動如火如荼展開。當時修課的學生有將近半數前往中正紀念堂參與靜坐和觀察; 最後我也在課堂中,特別針對這次的學生運動,讓同學分享與討論其參與的經驗與感想。當時我就已經透過閱讀麥亞當教授這本書,知道美國有些北方菁英大學的白人學生,參加民權運動到密西西比州經歷了「自由之夏」的洗禮後,對其人生的傳記產生的影響。我也藉著介紹麥亞當教授的這些研究成果,提醒修課的同學,特別是運動參與者,不妨開始構思如何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後,追蹤研究這些一九九○年學運參與者的生涯發展。
在往後的教學與研究生涯中,也有一些當年的「學運世代」參與者陸續成為我的學生,其中更有不少走入學術圈,成為學界、甚至是同單位的同事。另外,也有些運動參與者在因緣際會的情況下,走入政治界,成為耀眼的新星。因此,每次在「社會運動」課程中談到這個主題時,我也一定會舉當年參與三月學運的「學運世代」的案例,做為介紹了麥亞當的研究發現之後,一個可資對比的潛在研究題材。雖然由於個人的主要研究興趣不在學生運動,一直沒有對這個研究題目進行探究,但是基於教學與研究興趣,仍然相當注意這個主題的相關著作或討論。不過,到目前為止,有關「三月學運」的著作,主要仍然圍繞在這個廣泛引起社會矚目的學生運動崛起之背景與過程的討論, 而少有涉及後續發展的著作(例如,何金山等著,1990;林美挪編,1990;鄧丕雲,1993;范雲編,1993;碩士論文則有:孟繁忠,1991;林仁傑,2004;郭凱迪,2007)。
唯一的例外,是何榮幸在三月學運十年後,追蹤訪問當年的四十二位參與者而寫成,在二○○一年出版的《學運世代:眾聲喧嘩的十年》。這本在二○○一年台灣中央政權首度政黨輪替的背景下,「學運世代」逐漸在台灣政治圈嶄露頭角後,由中國時報編輯鼓勵作者寫就的書,對於這群人第一個十年的生命史,以「眾聲喧嘩」來描述其「嘈雜喧鬧、活力奔放、成長轉變、多元異質、苦悶焦慮」的整體面貌(何榮幸,2001: 15)。
雖然何榮幸在該書中清楚定義了學運中的四層人:「學運領袖」(各校學運領導者及核心幹部)、「學運份子」(各校學運社團活躍份子)、「學運群眾」(參與靜坐的學生)、「學運氣氛感染者」(同上引,頁12)。但是,局限於該書的性質,書中訪談的對象,大致上仍集中於人數最少的第一層「學運領袖」。這些少數的菁英,當然對於後來的社會與政治變遷有影響力,但是他們畢竟不足以代表整個「學運世代」;如果要真正評估「三月學運」參與的後續影響, 可能不能忽略人數更多的第二層「學運份子」後來的發展。尤其是學運世代成員往往默默地在目前台灣各類社會運動組織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並未受到傳播媒體青睞與報導。在轉型後的民主化社會中,這些倡議型的社會運動組織對於台灣社會變遷的影響,可能不亞於在民主化轉型過程中,投身抗爭型政治運動的工作者。但是,要完成這項評估的工作,可能就需要進行類似麥亞當教授在《自由之夏》這本書中,所完成的廣泛而深刻的追蹤訪問及資料分析了。
不過,前面提到過去研究重視運動的「崛起」多於注意其「發展」的問題,亦出現在討論或研究台灣更早的學生運動的著作中。一九九○年的「三月學運」,通常被認為是一九八○年代台灣大學校園學生運動發展的最終階段(鄧丕雲,1993;范雲,1993)。但是,台灣大學校園內的學生運動並非由一九八○年代才開始。一九五○年代台大校園出現的「再展開新文化運動」、一九六○年代的「青年自覺運動」,以及一九七○年代的「保釣運動」,都曾經掀起校園的風潮(參見丘為君等編著,1979)。其中前兩者屬於自我反省性的運動,對後來社會發展影響較小。影響較大者,當推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二年的「保釣運動」,以及隨後因為一連串的外交挫敗事件(退出聯合國、台日斷交、台美斷交等)引發的「革新保台」運動。後者成為台灣政治民主改革運動的前身或先鋒(陳少廷,1993: 4)。
一九七○年代台大學生運動的核心領導者洪三雄在一九八七年解嚴、一九九○年國會全面改選後, 所目睹的反對政治民主化、本土化之力量崛起後,將一九七○年代初期台大校園內追求民主、以及反對改革的對抗勢力之間的角力過程,出版成《烽火杜鵑城:七○ 年代臺大學生運動》(1993)一書記錄下來。書中提到的學生運動參與者或是反對者,在一九九○年代以後,有不少都漸漸成為台灣檯面上引領風騷的主要政治人物,但是也有不少自此銷聲匿跡,或再也不投入政治領域或公共事務。這些當年的當事者,目前所留下的各種文獻,多數仍然集中在紀錄與介紹當年運動崛起到消失的過程,而較少談到這些參與的經驗,對於他們個人所造成的影響。而這一群被台灣社會學者蕭阿勤稱為「戰後世代」的人,由當年參與保釣運動開始, 到後來因為民族主義的立場不同而分道揚鑣,在一九八○年代以後台灣的民主與政治轉型中,在不同的位置上競爭與互鬥,更成為台灣政治與社會變遷中重要的一環(蕭阿勤,2008)。不過,這一段一九七○年代學生運動的往事,除了上述當事人的一些記錄之外(洪三雄,2003;丘為君等編著,1979),當代的研究者較少注意(比較值得一提的例外是蕭阿勤,2008;與湯志傑,2009)。更重要的是,儘管這些檯面上的政治人物影響力極大,但是一般很少去探究當年的學生運動參與(或不參與)對於他們現在的生涯發展有何種影響。
以上這些,都是我認為這本書對於台灣社會與社會運動研究的啟示。我在一九八四年到一九八九年期間於美國亞歷桑那大學社會學系唸書期間,最初幾年麥亞當教授剛好正在進行這本書的研究工作。幾次在系裡的演講中,聽他侃侃而談,敘述這個研究的緣起,尤其是他提到在「馬丁路德紀念館」意外發現當年「自由之夏」參與者的原始申請表那一段時,聽眾總會發出一陣讚嘆聲(「你這個幸運的傢伙!」)。當時只是覺得這是個有創意而深刻的研究,也以擔任他的助理為傲。後來他擔任我博士論文的口試委員,也給了我最多的建議。返台任教後,因為長年開授「社會運動」這門課, 幾乎每年都會重讀他的幾本著作,而《自由之夏》一直是最讓我感動的一本書。二○○五年夏天,我有機會和台大社會系合作邀請麥亞當來台訪問與演講,並負責擔任其作品的導讀。當時我已經畢業十六年了,多年後再度與麥亞當教授在台灣相聚,當年研究生生涯的記憶一時之間湧上心頭,也才漸漸明白自己在社會學的研究與教學生涯上,受到當年幾位老師言教與身教多麼深刻的影響。特別是麥亞當教授,更是我學習的主要對象。那次在介紹完他的著作之後,我提到自己在亞歷桑那大學念書那幾年所受到的震撼與影響,包括對於台灣社會與社會學研究的重新認識,就彷彿那些當年參與「自由之夏」的大學生在密西西比州所受到的衝擊一般。在某種意義上,出國留學那五年,就是我的「自由之夏」。
很高興這本書的中文本終於問世。希望讀者透過這本書,也能像我一樣幸運的找到屬於自己的「自由之夏」。
王甫昌, 二○一○年一月五日,南港
序幕
尋找志工
每一天發生的每樣事對我來說都是全新的。資訊不斷轟炸著我,經驗不斷轟炸著我...而我衰微的精神狀態幾乎要失控了。
你感覺自己將參與這歷史性一刻; 在一區域中, 整體生活模式裡很深刻的某項東西即將轉變...你正在...創造...歷史。從某些方面來看是全然無私無我,但(你)也同時發現了自我。
在我生命中, 就社會改革的願景來說,它是我將經歷過最有可能成真的經驗...就參與歷史來說, 它也是我將擁有的經驗裡最棒的一次, 但是它...也讓我付出了代價...(情緒上)它讓我受挫...(幸運地是) 我的身體並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因此,至少就肉體層面來說,我...活了下來。
(它)是極具啟發性的。我的意思是,我覺得整件事情...開始去思考身為一個女性,我該怎麼做,還有我該怎麼過我的人生。我要成為一位專業人士嗎?我要去讀法學院嗎?...如今的我,有太多必須回溯到它。我現在所從事的工作,有太多必須回溯到我對那段時期的回憶。
它讓我欣喜若狂...第一次這些片段碎塊嵌合在一塊...感覺像我自己...我認為透過它,我們不但成就了些事,也是實現我個人的救贖。
它是我人生中最長的夢魘: 三個月──一九六四年的六月、七月、八月(Sell ers, 1 973 : 94)。
以上所有人口中所謂的「它」究竟指的是什麼?是什麼樣的共同經歷,讓這麼多人產生了如此分歧卻又深刻的反應呢?這個我們所關注的事件就是一九六四年密西西比自由之夏(Freedom Summer)運動, 或依當時為人所知的名稱, 叫做夏日計劃(Summer Project)。
由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tudent Non-Vio 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以下簡稱SNCC)領頭的這項計劃,歷時不到三個月,自六月初至八月底止。在這段期間,有超過一千人──絕大多數是北方白人大學生 ──啟程前往南方,到當地執行計劃,整個運動由四十四個這樣的子計劃組成。在密西西比的日子裡,這些志工共同居住在「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s),或寄住在那些不懼種族隔離主義者暴力威脅的當地黑人家庭中。平時他們得擔負許多任務,主要是為黑人選民進行登記,以及在所謂的自由學園(Freedom Schools)裡任教。
在以上的概述中,略而未提的部分, 就是那難以被緩解的恐懼、令人苦惱的貧困, 以及間或發生的暴力事件,這些都再再困擾計劃的進行;其加總的效果,也讓這個夏天成為幾乎每位參與者心中難以磨滅的經驗。有三位參與者──錢尼(James Chaney)、古德曼(Andrew Goo dman)及史維納(Michael Schwern er)──甫加入計劃才十天,就被一群由密西西比執法人員帶頭的種族隔離主義者綁架, 三人被痛毆至死。隨後搜索他們行蹤的行動,把許多聯邦調查局探員及數百名記者引到該州。儘管有他們的出現,暴力事件仍層出不窮。另一位志工在夏季接近尾聲之際喪命,還有數百人遭受
炸彈攻擊、被毆打或逮捕。這些志工接觸到了新的生活方式──跨種族的人際交往、共同居住的生活、更開放的性關係──新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及批判美國的嶄新觀點,據此他們經驗了一種自由解放的意識。總而言之,它是這群傑出的年輕人所擁有的一段非凡夏日,其影響持續不輟,不論是對這些志工,或整個國家。
夏日計劃初期,它充分反映美國六○年代早期那種典型自由派理想主義色彩;儘管仍存在某些緊張與矛盾,但這個計劃確實體現了構築該時代進步願景的部分理想,包括跨種族主義(interracialism)、非暴力及自由/左派聯盟(liberal / left coalition)。因此,我們也從這些志工身上看出這些理想。
身處夏日運動開始前夕,計劃參與者所象徵的是六○年代初,旭日東昇的理想主義中「最棒且最光明的一面」。這群極高比例來自菁英學院及大學的志工,朝氣十足,大多學業表現突出,積極參與政治事務,並充滿高度熱忱致力於徹底實現理想主義之價值,他們自小被稱為是美國之根基的那些價值教導。大體說來,他們信奉自由主義,但不走基進(radical)路線;他們是改革主義者,但並非革命家。
然而,不管是志工或這個國家,很快地將經歷一番劇烈的轉變。身為同一國家之民,我們在時間長河裡流轉,自新疆界(New Frontier)的光輝歲月跌落至這個動盪不安的六○年代晚期。如果自由之夏算是六○年代初自由主義的全盛時期,它所仰賴的根基卻在不久之後傾覆。不到一年後,跨種族主義就在黑權主義(black power)與黑人分離主義的呼聲中壽終正寢。在一九六五年華茲(Watts)事件的啟示下,非暴力的主張也廣被仿效,起碼在運動的宣傳上是如此。自由 左派聯盟同樣也無力在這個夏天後延續下去,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為它劃下句點,當時民主黨的中堅人士選擇授予席次給排除黑人的密西西比代表,而不是夏日計劃的挑戰代表。
與整個國家一樣,這些志工也受到當時的紛擾亂象影響。因六○年代中期至晚期的種種事件,讓絕大多數的人都變得更加基進。其中有很多人,在這些事件上皆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實際上,沒有人是不受那些事件影響的。
本書的中心論旨是,若想徹底了解那個時代,這些志工與美國所經歷的劇烈轉變,我們必須認真重新評價這場自由之夏。畢竟,不僅對這些參與運動者的生命,還有整個新左派陣營來說,自由之夏都象徵一個重要的轉捩點。其重要性在於這個夏天發生的種種事件,以及隨後引發的文化與政治效應。這個夏天發生的種種事件有效地再社會化、激進化這群志工,而他們與其他志工所建立的連帶,又進一步為社會運動者的全國性網絡,奠下基礎,此網絡日後孕生了這個時代其他的重要運動,包括女權運動、反戰運動、學生運動。簡而言之,自由之夏不僅為六○年代眾多行動主義(activism)的嘗試提供了組織上的基礎,同時也頗具關鍵性地推動了這個時代茁生的反文化思潮之發展。因此,本書回溯敘述自由之夏計劃,也重新衡量它對志工,及整體美國社會所造成的影響。
本書聚焦之處相當清楚明瞭,但它與七年前我開始這個研究計劃時所設想的,截然不同。當時,我的興趣並非集中在自由之夏運動或參與者身上,而是關注這些參與者與六七○ 年代稍晚的社會運動間的關聯。八○年代初期,一連串的偶發事件驅使我將研究焦點擴大。以下的故事即便只能為本書提供些許背景知識,但我想仍值得一書。
在開始進行本書所關注的計劃前,我曾花六年的時間研究,撰寫一本探討當代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起源的書(一九八二年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的《1930 - 1970年間政治過程與黑人叛亂的發展》〔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 surgency, 1930 - 1970〕)。在研究過程中,我很訝異必須不斷回歸到一群曾在民權運動之組織行動裡被訓練的白人身上,他們爾後繼續在其他六○年代主要運動裡擔任要角。我當時已意識到這些稍後的運動是受了黑人抗爭的影響,但由於我本身已將研究年代設定為六○年代末至七○年代初,因此我僅視這種影響是在戰術策略及意識形態上,而非在人員本身。當然,我所知道的七○年代初的運動者裡,少有曾參與過南方民權運動之組織行動的。然而,投身於社會行動的人數,卻在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年間迅速倍增,因此我們合理推斷日後運動者的主要組成份子, 不太可能來自六○年代初期即很活躍,但人數相對較少的先鋒。
如果人員的影響不是來自於數目上,那麼該從什麼角度切入來談這個影響呢?我覺得這些早期的白人民權運動者的重要性,在於他們為南方的黑人抗爭與在北方及西方的大學校園,搭起了政治與文化的橋樑。他們在這個重要的擴散過程裡扮演開拓者的角色,南方民權運動的意識形態、戰術策略及文化象徵藉此得以被引介給另一群人── 北方的白人大學生,這群人也將主宰後續階段的社運界政治生態。由此觀之,我們將認識到六○年代存在的並非是三或四個不相干的個別運動,而是單一的、涵蓋面廣的社會運動者社群,可確實地溯其根源於南方民權運動,而後延展出個別的分支,成為各種形式的運動(主要有黑權主義、反戰運動、學生運動、女性解放運動)。
要陳述這個論點很容易,但想有系統地研究這些連帶的範圍和重要性,卻有難度。儘管如此,在那本討論民權運動的書完成之際,我已下定決心要在此計劃處理這個問題。
我以為這樣的一個計劃,必須從系統性的基礎上開始著手。光蒐羅一些參與民權和同時代其他運動中個別運動者的軼事及證據,是絕對不夠的。我們知道海登(Tom Hayden)在六○年代末期成為真正的社運明星並為人所知之前,就已參與過南方的民權活動了,然而,這並不能讓我們了解這類現象究竟有多普遍。白人民權運動者裡有多高的比例在後來的反戰運動扮演先鋒角色? 而學運呢?女性解放運動呢?他們早年的民權經驗如何影響日後的選擇?我希望能回答類似這樣的疑問,但想達此目標,必須系統地接觸大批曾積極參與早年民權運動的人。自由之夏似乎就提供了這個管道。驅使我將這個計劃當成研究起點的原因,是因為它是年輕白人大規模參與運動的頭一遭。當然,白人參與民權抗爭已有長遠歷史,除了一些為人所知的特例之外,反黑奴運動的領袖多半是白人。在一九三○年代,由白人占主導地位的美國共產黨已設法支持黑人民權的理念,例如史考茲布洛男孩(Scottsboro boys)事件。其他像安與卡爾.布雷登(Anne and Carl Braden)等人,也曾在那個灰暗的四○到五○年代間進行過成功的抗爭。著名的和解聯誼會(Fellowship of Reconciliation,簡稱FOR)的葛倫.史邁利(Glenn Smiley)等白人,也曾積極參與蒙哥馬利公車罷駛事件(Montgomery Bus Boycott)。自由騎士(Freedom Riders)中有少部分的人也是白人。然而,在以上的所有例子裡,白人參與者的數目都算少。相較之下,來到密西西比參與自由之夏的白人有一千人左右,數目就十分龐大。這個計劃含納的人數如此眾多,確保了我只要能找到羅列所有計劃志工及當時其就讀學校的名單,就能接觸到大量的白人運動
者;我還想到了另一個能幫助我在今時找出這群志工的方法,就是透過他們個別母校的畢業校友聯誼會。
尋找這份名單的工作看起來就像找尋聖杯(只是這杯似乎不那麼神聖)。幸運的是,為要撰寫與民權運動相關的書,我曾多次造訪南方各大圖書館及檔案資料庫,讓我有機會探知究竟這份名單是否存在且身在何方。但不幸的是,圖書館員及運動者都跟我說他們並未留有這樣一份名單,也沒聽說過有這樣的名單。亞特蘭大的馬丁路德金恩紀念中心(Martin Luther King, Jr. Center)給我的回應也是如此,該圖書館負責人庫克(Louise Cook)說從未聽說過這份名單,但很歡迎我來瀏覽有關夏日計劃的各項文獻。她說得沒錯,我想要的那份名單並不在這些文獻裡,然而這些文獻卻讓找不到名單這件事顯得無足輕重,因為裡頭有一份這些志工在夏季以前就填寫好的,長達五頁的原始申請表格,如今它已被妥善地整理與歸檔。更棒的是,這份申請資料不僅包含來參與的志工,還有另外三百位原先報名參加且被錄取,卻不知何故未前往密西西比的人。我已悄然掌握一組自然而然出現的實驗設計。手邊有兩組人,一組是志工,另一組則是被認為在這個夏天以前,帶著十分類似特質的未現身者。前者經歷了自由之夏,後者則否。
原先我關注的是我研究計劃所針對的運動彼此之間的關聯, 但因取得未現身者之資料,讓我必須多處理兩個問題:第一,志工與未現身者在這個夏天以前,有何差異?在這個夏天以前,他們具有類似的特質嗎?還是, 這兩群人是如此不同,以至於我們隨後對其所做的任何比較都毫無意義?假使答案是否定的,那將延伸出第二個問題:假定我們有足夠理由拿未現身者來作比較,他們在這個夏天之後的生命樣貌與那些參與計劃者,有何不同? 最終當研究進展到一定階段後, 我會認為這個延伸的問題將和前三個問題一樣重要。令人感興趣的不只是比較參與者與未參與者,也包括了解男志工與女志工之間的差異。在六○年代初期,養育男女性的方式迥異,因此我們不能直接假定參與這個計劃對他們自己及他人的意義是相同的。據此,第四個問題是:對男性與女性而言,夏日計劃及其後續影響的經驗,有何不同?
過去六年來,我嘗試以各種方式回答這四個基本問題。為此,我首先必須找到這些申請者,愈多愈好,而原本的計劃申請表格讓我不費吹灰之力即可做到,其中一個問題的資訊就包括了申請者當時就讀的大專院校。於是,我可以彙整申請者的名單,寄信給全國約兩百六十九個畢業校友聯誼會。如我所預期的,它是我搜集訪談者住址的過程中最成功的管道。另外還有其他管道,申請參與計劃的人還必須在申請文件填上父母的名字及住址,儘管美國是一個地理流動性高的社會,但仍有近百分之二十的父母在一九八二至八三年間仍住在與一九六四年時相同的地方,他們回過頭來提供給我那些曾申請上計劃的兒女現今的住處,藉此,我獲得了一百零一個地址。申請計劃者還被問到大學時主修的科目,我因此取得了申請者依不同主修排列的名單,在同時比對學院名錄後,我找出了相符的姓名。還有一些地址是透過各種不同的方法取得,一旦我與申請者取得了聯繫, 他們之中有很多人都樂意且有辦法提供其他還保持連絡之人的地址。透過朋友網絡,讓我能與更多的申請者聯繫。至少有兩位後來寫出了自己經歷的申請者,其出版商主動與我聯繫,還有一些人是聽說了我的研究計劃後跟我連絡的,甚至有一回我參加一場派對,席間恰巧聊到我的研究,一位申請者就這麼出現了。
如此多元的管道,最終得到的成功是,在我所擁有的九百五十九份申請資料裡,共確認五百五十六位申請者現今的住址。其中,有三百八十二位(所有申請資料裡的七百二十位) 曾參與這個計劃,另外一百七十四位(所有申請資料裡的兩百三十九位)則在夏季開始前選擇退出。在此即可預先得知兩群人的差異是,在未現身者裡,我所能取得他們的現今住址的比例( 百分之七十三)要較實際參與的志工(百分之五十三)高得多。至於這個差異背後確切的意義,則必須等到開始連絡申請者後才會漸漸明朗。
我與申請者連絡的方式,分成兩種。第一,我會寄給所有申請者一份問卷(請見附件A),內容是詢問他們的自由之夏經驗、參與社運的歷史、其個人或政治生命的大致梗概,及參與自由之夏後的情況。若想要比較我所處理的眾多申請者資料,這將是我唯一可行的方法。
然而,我也知道,若想真正了解我處理的這些複雜議題,我必須至少和兩個群體裡的部分人士進行長時間的訪談。在一九八四年八月至一九八五年七月期間,我在兩個群體裡對所有申請者做隨機取樣後,訪談了四十位志工及四十位未現身者。這些訪談有超過一半是在一九八五年春季,這為期三個月的高峰期所進行的,在這段期間,我足跡遍布全國各地,哪兒有受訪者,我就往哪兒去。誠如我所說的,在這次旅程裡,我跋涉了二萬二千英哩,共訪談四十八人。訪談的時段從兩小時至兩天不等,訪談環境同樣也五花八門。整個訪談過程進行下來,我還參與過科羅拉多的美洲原住民治療儀式、水牛城的猶太教成年受戒禮、華盛頓特區的反種族隔離示威遊行,以及在加州某一社區內見識了正式的日本茶道禮儀。與申請者接觸的過程裡,困惑、欣喜、沮喪、自覺收穫滿滿等各樣感受,接踵而至。
儘管如此,這趟訪談之旅終究如我早先所期望地「完成」了。結束之際,我更加清楚意識到自由之夏對志工的意義為何,以及它如何以迥異於未現身者的方式,形塑了志工的生命。原本在回收的問卷上,兩群人所呈現的淺薄區別,放到訪談對話就變得活靈活現。兩群人原先在這個夏天前,看似如此相似,但我們仍在其間看到他們以很不同的方式出現。這些差異不但重要,同時也在志工的生命,及新左派和後來被稱為「六○年代經驗」的演進過程上,創造出差異。適逢個人生命經歷與歷史產生獨特重疊的這群志工,是首批意識到在這個時間點上有種種可能性的白人學生。當這股政治與文化的巨浪形成且不斷地向前鋪蓋而來,志工中也有許多人登上了浪頭。就一定程度上來看,本書接下來將描述的正是這股巨浪;包括它的性質、演進歷程、創造出它的獨特個人傳記性的條件或歷史環境,以及它在那些曾想嘗試 ──其中許多人至今仍想──乘浪的人身上所留下的痕跡。至於自由之夏呢?即便它並未直接孕生了這股巨浪,但可以確定的是,它賦予這股巨浪動力,同時也協助許多與巨浪相關的特定政治與文化元素得以成形。或許最重要的是,自由之夏創造出了一座重要的橋樑,北方的白人大學生藉此才得以接觸六○年代文化,成為最主要的消費者。自由之夏的志工散發其影響力,成為這項新文化的載體。本書的主旨即在了解他們如何扮演這個角色及其後所產生的影響,不論是個人,或整個社會。
|
|
|
書
評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