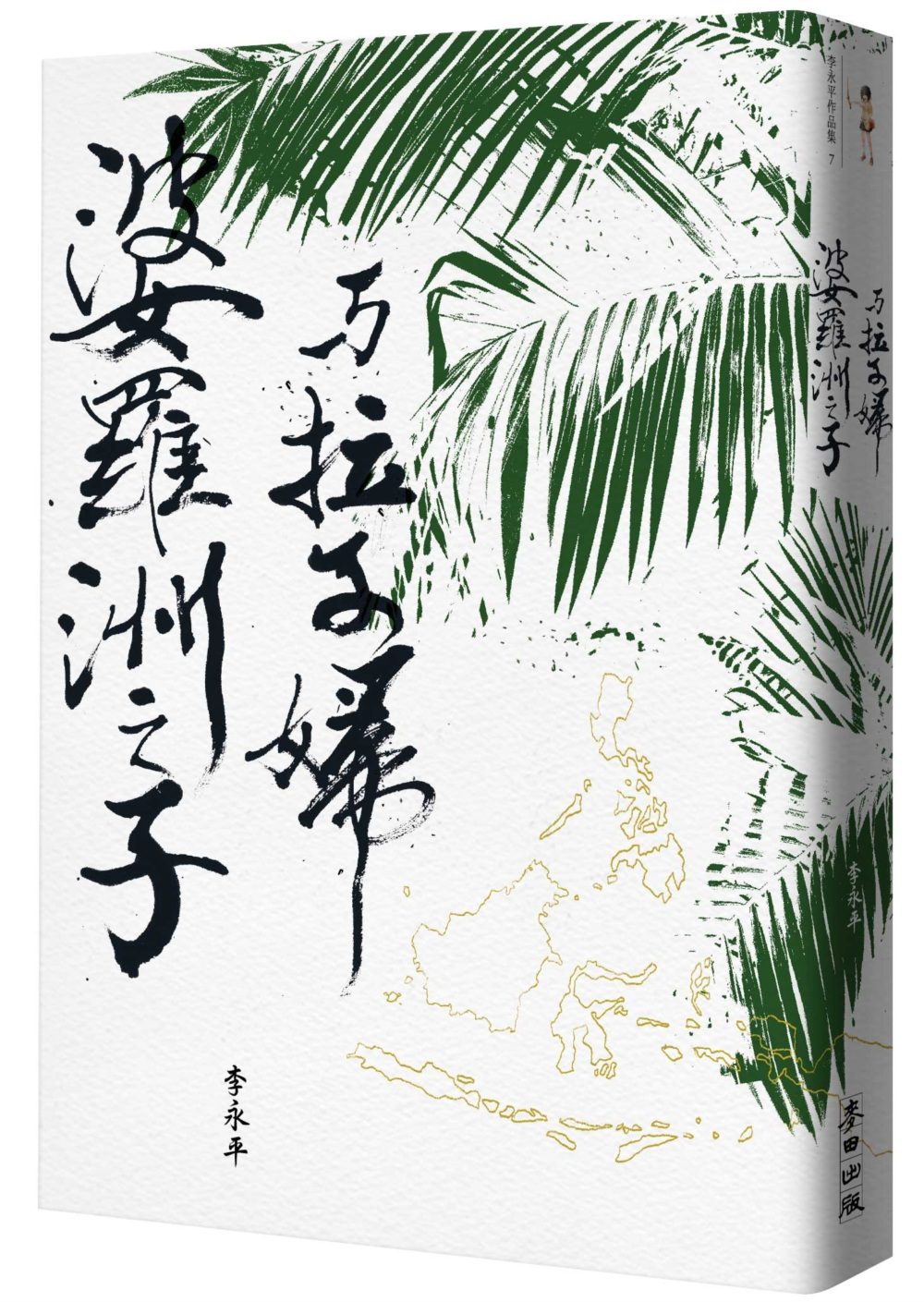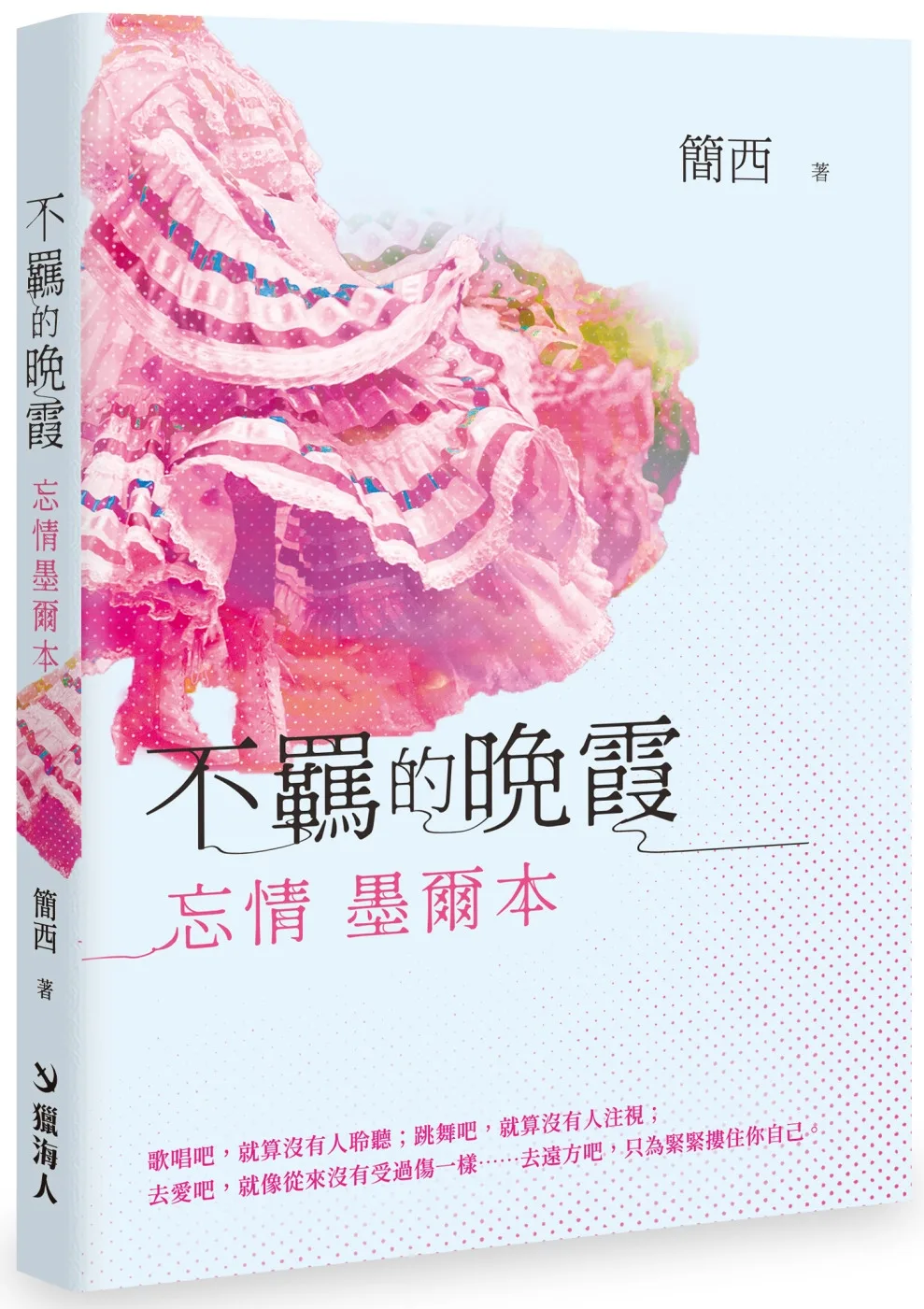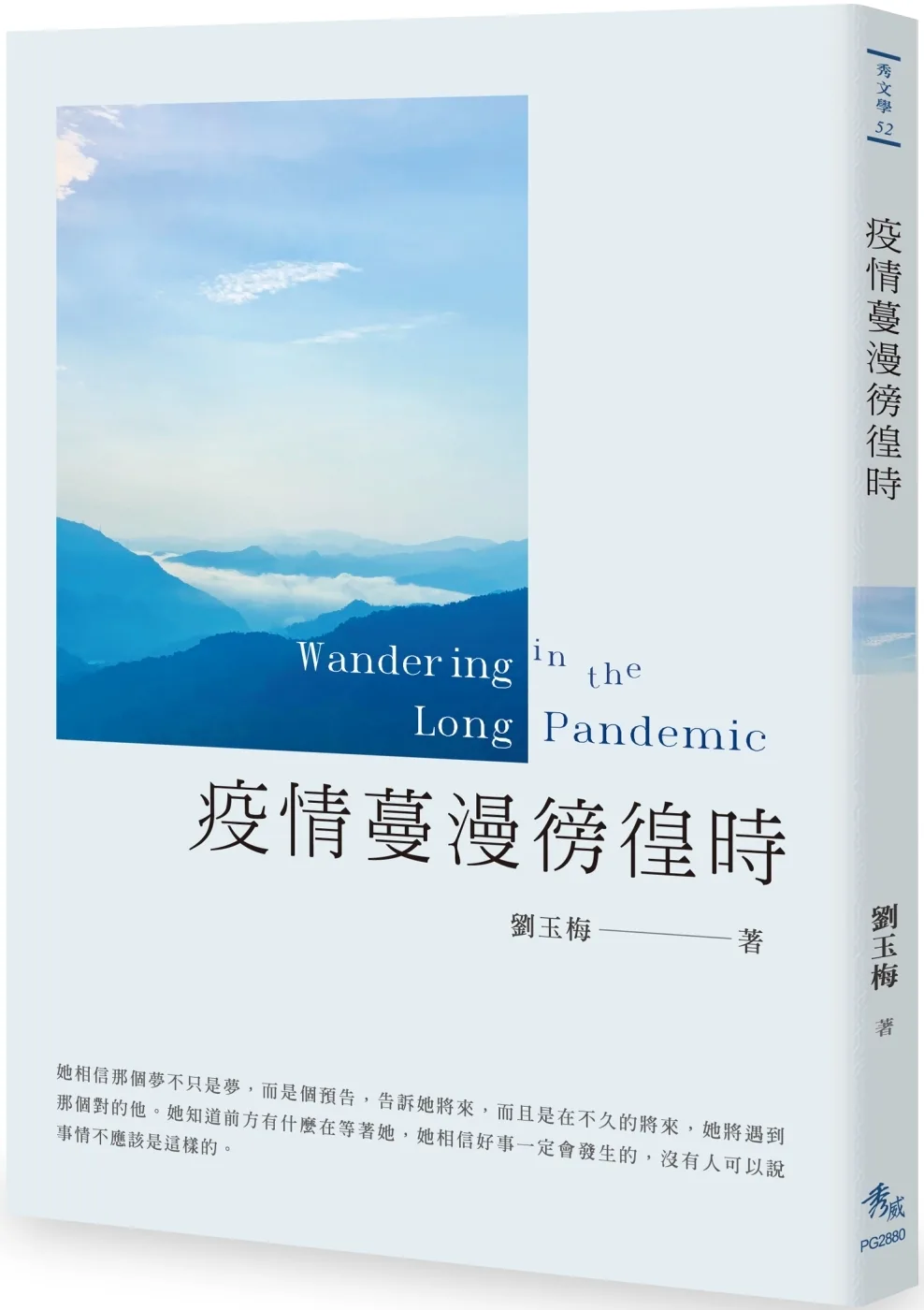?
【推薦序】
早期風格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 Edward C. Henderson 講座教授)
?
一九六七年李永平(一九四七—二○一七)從婆羅洲來到台灣。此後五十年他創作不輟,成為台灣文學以及馬華文學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赴台之前,李永平已經是熱情的文藝青年,一九六六年即以〈婆羅洲之子〉獲得婆羅州文化局文學獎。在台大外文系求學時期,除汲取西方文學資源外,並獲得名師如顏元叔教授等的提攜鼓勵,更加致力創作。一九七六年,李永平第一本小說集《拉子婦》在台灣出版,同年赴美深造。
相較於日後讓李永平聲名大噪的著作《吉陵春秋》、《海東青》、「月河三部曲」系列(《雨雪霏霏》、《大河盡頭》、《朱翎書》)等,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十年間的李永平仍然處於試探題材、磨練風格階段。但這些作品已經隱隱肇動著青年小說家的未來走向。他的性情執念,他的主題風格,甚至人物典型無不若隱若顯。麥田出版公司將李永平這一時期的作品《婆羅洲之子》、《拉子婦》合為一集出版,不僅見證作家個人的所來之路,也為台灣現代主義文學的發展增添重要的面向。
李永平負笈來台時,馬來亞(後為馬來西亞)建國不過十年,華人的地位每下愈況,兩年後五一三事件(一九六九)爆發,馬來人和華人的衝突自此浮上檯面。李所來自的婆羅洲砂勞越地區與馬來半島上的勢力格格不入,至一九六三年才與馬來亞聯合邦、北婆羅洲和新加坡聯合組成馬來西亞聯邦。砂勞越尋求獨立的號召一度甚囂塵上,砂共也成為棘手現象。所謂西馬、東馬是地理的分界,也是政治的對峙。與此同時,中國大陸發生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一九七六),台灣推出文化復興運動。而島上現代主義和鄉土文學運動已經勢不可遏。
李永平的創作是在如此盤根錯節的背景下展開。他對故鄉砂勞越一往情深,但那複雜的人種和人情糾葛卻成為他畢生難解的命題。他嚮往中國,對自己身在異鄉與異族為伍不能釋懷。他在現實環境考量下選擇到台灣就學,卻比一般僑生多一分對中華文化的執著。問題是,僻處海角的台灣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祖國」延伸甚至幻影,反因此更加深他的「想像的鄉愁」。文學創作自不必是作家個人生命的倒影,但在李永平早期作品的字裡行間無不潛藏著他與歷史情境對話甚至搏鬥的痕跡。
李永平的〈婆羅洲之子〉作於一九六五年,彼時作家只有十八?,下筆已不自覺地顯露日後他一再處理的題材。故事中的大祿士是華人和原住民達雅族女子所生的混血兒,不能見容各個族群。大祿士為追求認同與正名,經歷重重考驗,包括殖民與族群勢力的壓迫和誘奸婦女的栽誣,最後化險為夷,完成心願。這篇小說有個過分光明的尾巴,也許代表青年作家的期望甚至文學獎的趨勢,卻反而襯出故事裡的暗潮洶湧,難有解決之道。婆羅洲是蒼莽豐饒之島,十八世紀以來即有大量華人移居。華人與西方殖民者、馬來人及原住民形成此消彼長的複雜生態。許多年後,後殖民學說當道,華人移民被冠上「定居殖民者」的封號,成為撻伐對象。但作為「婆羅洲之子」,大祿士個人華夷夾雜的遭遇可能才更為真實。不論是種族的混血,還是文化、政治的妥協�共謀,其混淆曖昧處哪裡是一兩套政治正確公式所能道盡?
〈拉子婦〉是李永平早期作品中最受好評的一篇,恰恰可以視為〈婆羅洲之子〉的另一版本:〈婆羅洲之子〉寫混血兒子故事,〈拉子婦〉則處理原住民母親的故事。故事中的拉子婦是婆羅洲達雅土著,她與漢人成婚,受盡歧視,終於萎頓而死。李永平表面寫的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的悲慘遭遇,幾乎像是五四以來人道寫實主義的翻版。但骨子裡他的命題更要嚴峻得多。隱身為童稚的敘事者,李永平靜靜的鋪陳一則有關海外移民的寓言。華人移民固然受到移居地上西方殖民者的壓制,但相對於土著,華人已成為另類殖民者。然而「移民」不世襲,移民一旦落地生根,和在地文化與人種混同,年久日深,是否終將淪為夷民?漂流海外的華族,要怎樣維護他們的文化傳統,血緣命脈?拉子婦的下場當然值得同情;她是西方、華人和馬來人多重殖民勢力的犧牲。但換個角度看,她所象徵的威脅—異族的、混血的、繁殖的威脅—隱隱指向漢人移民文化的最終命運。
另一方面,李對拉子婦的同情不以族裔設限,而更及於她的性別身分:她是個母親。這是李原鄉想像的癥結所在。母親—母國,故土,母語—是生命意義的源頭,但換了時空場景,她卻隨時有被異族化,甚至異類化的危險。拉子婦曖昧的身分,還有她必然的死去,因此成為李永平的原罪恐懼。如何救贖母親,免於異(族)化,甚至期望母親回歸到永遠不要長大,不要變老的孩提時代,成為他未來數十年不斷嘗試的寫作核心。而母語—中文—成為他點石成金的祕方。
李永平的孺慕之情在〈圍城的母親〉和〈黑鴉與太陽〉裡有更進一步的表現。尤其〈圍城的母親〉已具寓言意味。海峽殖民地裡的小城,華裔移民的社會,蠢蠢欲動的土著,誓守家園的母親,敏感多慮的兒子,串演出一齣詭異的母子情深的故事。小說中段,母親夜半棄家逃難,「船在水上航行 ,就彷彿在泥坑裡行走一般。從上游不斷漂下一堆堆樹幹樹枝樹葉,也不知道它們在什麼時候才漂到河口,進入浩瀚的大海。倘若他們不斷地向北方漂去,是不是會有一天漂到唐山?」然而母親最後還是決定調轉船頭,回到被圍的城裡去。他鄉已是故鄉,捨此難有退路。飄零域外的華族子弟只能與「圍城的母親」長相左右。
李永平的婆羅洲�中國情結在〈田露露〉達到最高潮。這篇小說刻意營造史詩結構,上溯鄭和下西洋來到婆羅洲、手下大將與島上勃泥王國公主的露水姻緣,以及兩人後裔興國的故事。勃泥公主與漢人大將有緣無分,只能化作當地中國寡婦山的傳說源頭。換句話說,這樣的傳說儼然是個〈拉子婦〉的前世皇家版。據此,李永平來到二十世紀中期西方帝國殖民統治的最終時刻。今非昔比,一切都顛倒了。故事裡的田露露煙視媚行,洋人殖民官員也為之傾倒。但露露只是個英文名字,她的中文名字「田家瑛」才真正喚起她千迴百轉的的故國意識。這個島上日本人、英國人、馬來人來來去去,唯有古老的大明英雄傳奇成為她魂縈夢牽的對象。然而在南洋,在大航海時代的終端,又有誰能訴說自己真正的血統與身世?露露也許是,也許不是,勃泥公主�中國寡婦的後裔。即便是追求她的英國殖民官,竟然也有來自西印度群島土著的血統。人種、血緣、宗主、性別想像、殖民反抗與共謀……〈田露露〉有太多話要說,不能算是成功的作品,但青年李永平對自己身分的反思和鬱結盡顯於此。
李永平的反思和鬱悶百無出路,只能在另一篇〈死城〉裡化為暴力和死亡的意識亂流。這篇作品充滿現代主義色彩,抽去時空背景,唯有華裔主人翁陷入一場詭異血腥的暴動。幢幢鬼影,幽冥難分,這是身分與價值崩裂的時刻,也是敘事邏輯混淆解放的時刻。然而李永平對這種不請自來的魅惑,有著不能自主的好奇。在《吉陵春秋》、《海東青》與《大河盡頭》都有更深刻的表現。
《婆羅洲之子》與《拉子婦》雖是少作,但李永平一生辯證華夷關係、雕琢文字意象,還有尋找女孩作為永恆繆斯的嘗試,都已歷歷在目。薩伊德(Edward Said,一九三五—二○○三)論及作家與藝術家的《晚期風格》(On Late Style: 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 2007)時,認為來到生命盡頭的藝術家和作家,每每不復盛年的嚴謹與魄力,而顯現創痕處處、甚至偏執拮据的傾向。然而他們的老辣與焦灼反而形成另類風格,不容錯過。李永平的創作軌跡似乎反其道而行,他的成長經驗如此複雜,讓他一下筆就是糾結纏繞,而且隨著寫作經驗的深化,變本加厲。《吉陵春秋》寫性與暴力的罪與罰,《海東青》寫洛麗塔式女孩童貞的墮落,《大河盡頭》寫少年欲望啟蒙,無不如此。反而到了晚期,李永平彷彿才找到解脫之道。《朱翎書》描寫被男性白人殖民者褻瀆的亞裔少女在婆羅洲的絕地大反攻,猶如成人版童話。《新俠女圖》則終於回到他的古典中原夢土,訴說俠女的快意恩仇。李永平的題材也許依然沉重,但他的敘事淩空飛躍歷史和地理,展現神話力量。
李永平所思考、銘刻的話題,多少年後才有後殖民主義者、華語語系學者、帝國批判者等,憑著後見之明做出詮釋。但又有多少論述能夠說出李永平那早熟的心事?重讀《婆羅洲之子》與《拉子婦》,我們見證李永平作為「婆羅洲之子」的前世今生。少年已識愁滋味,作家的「早期風格」仍然有待我們的細細體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