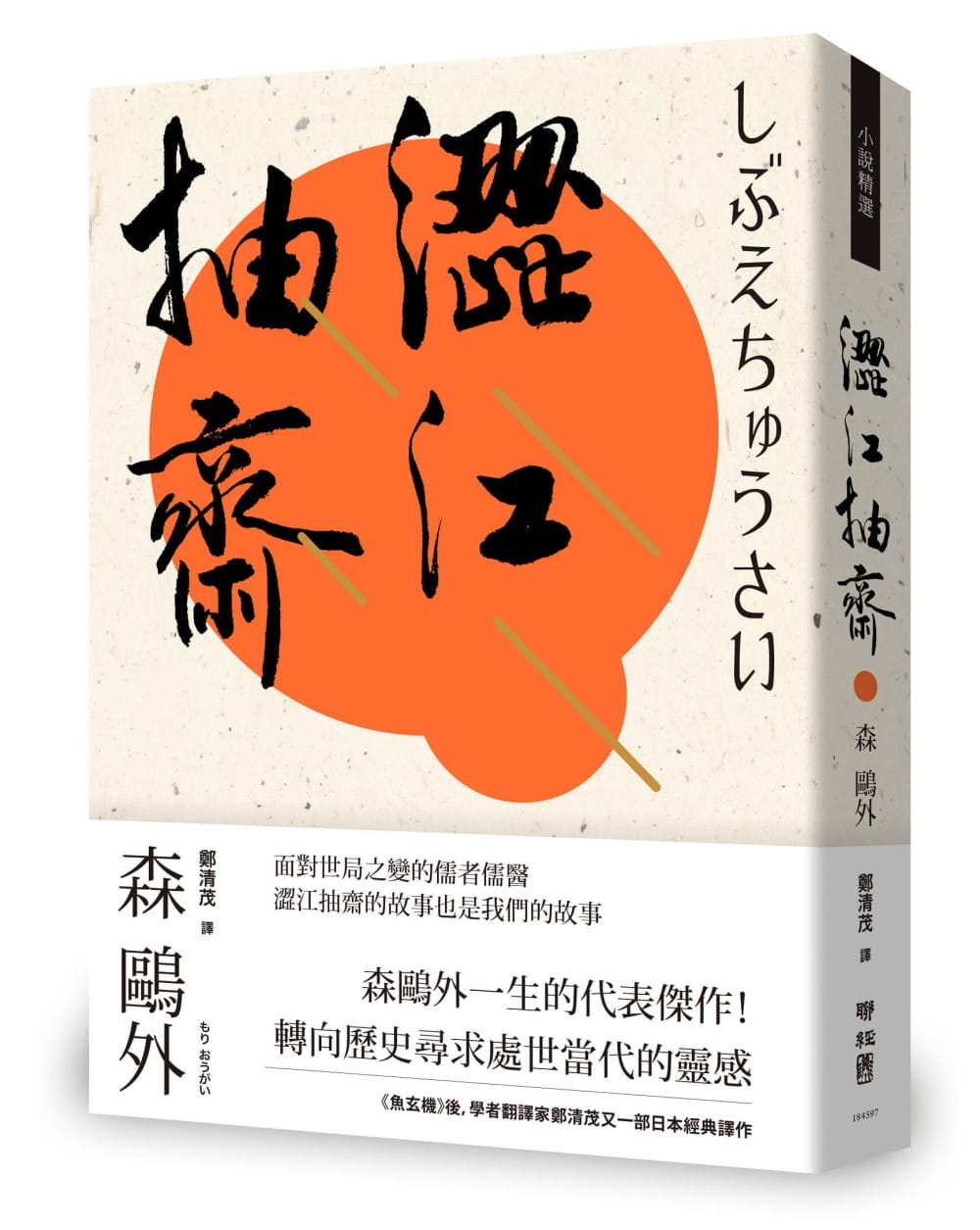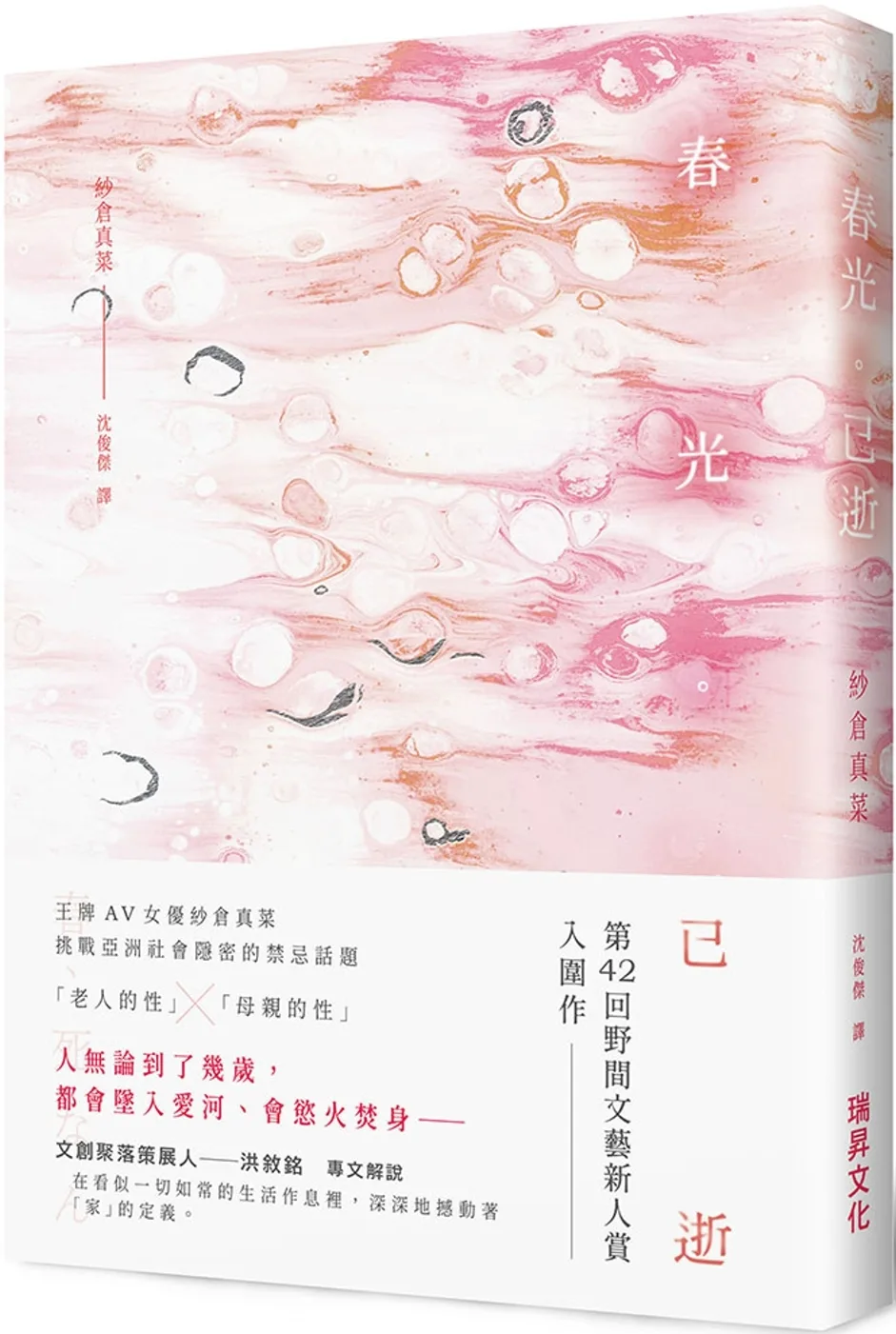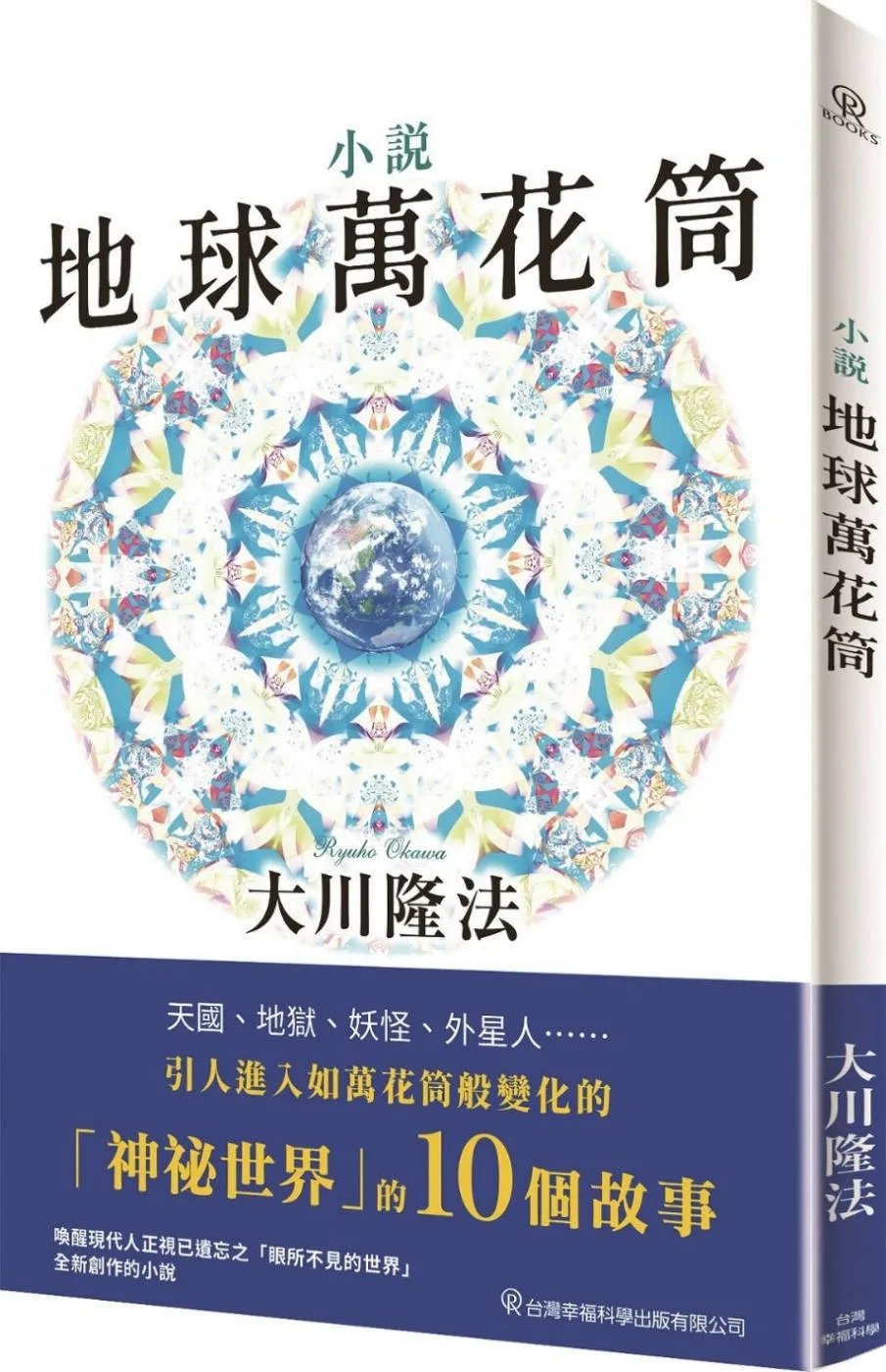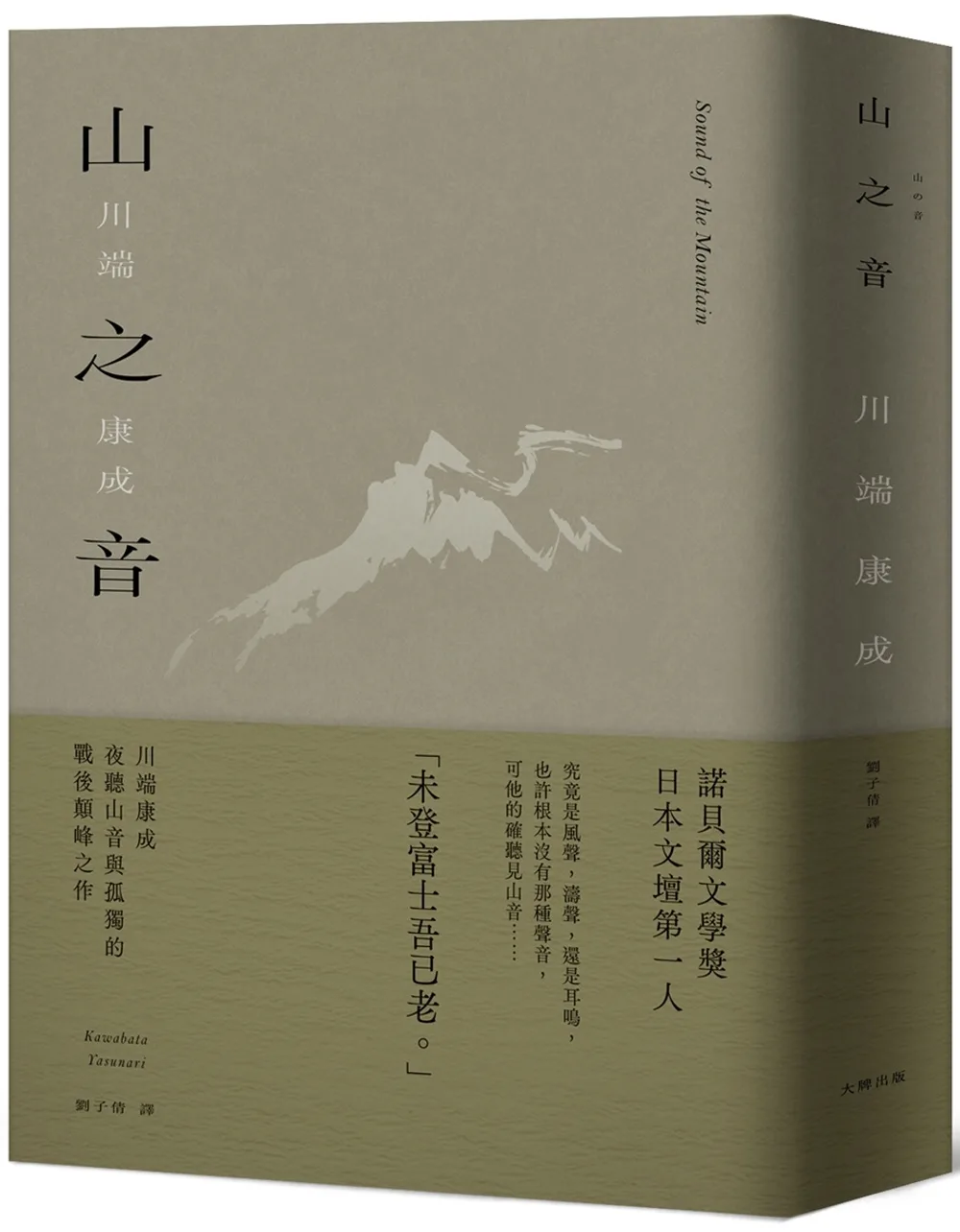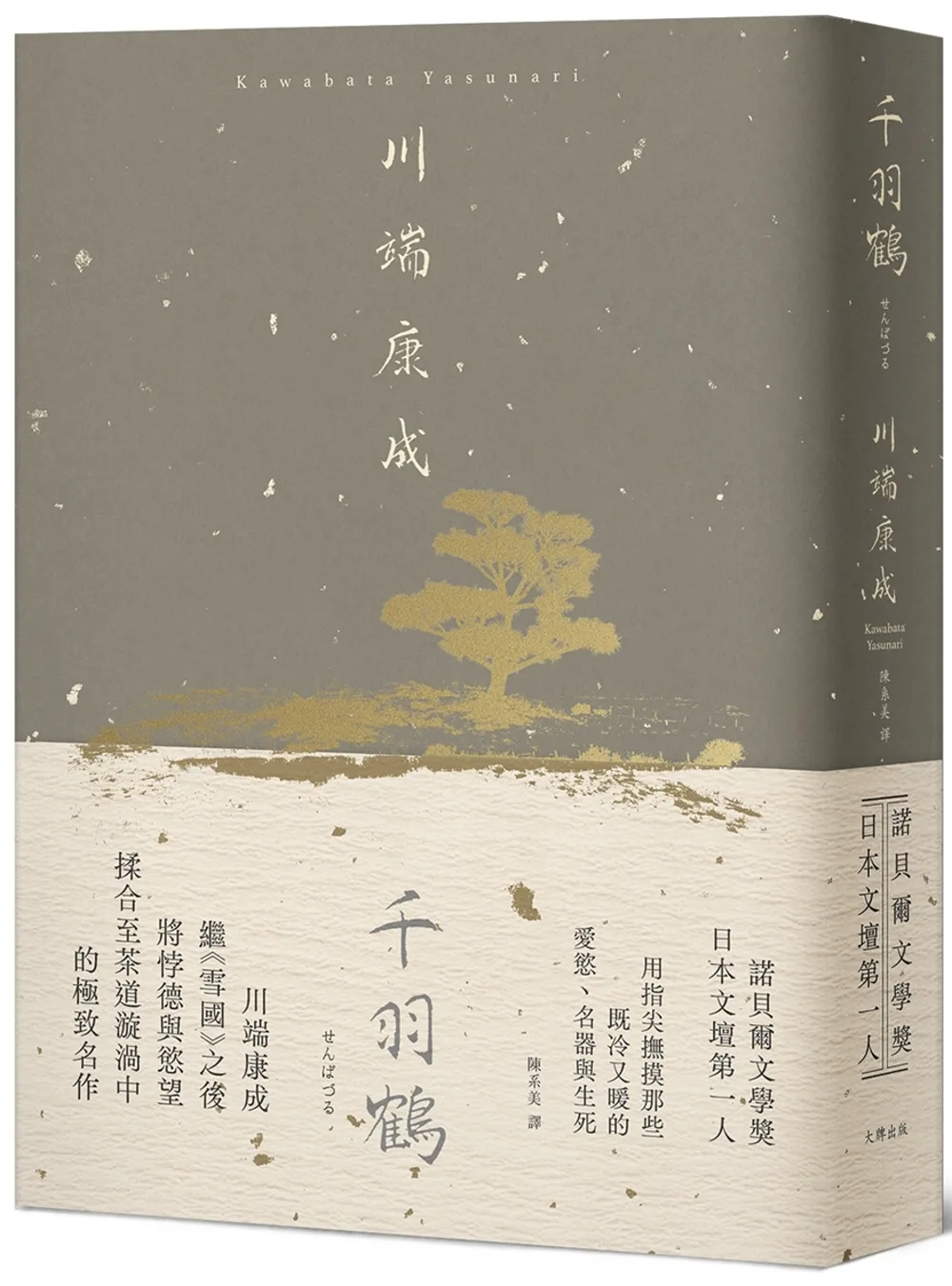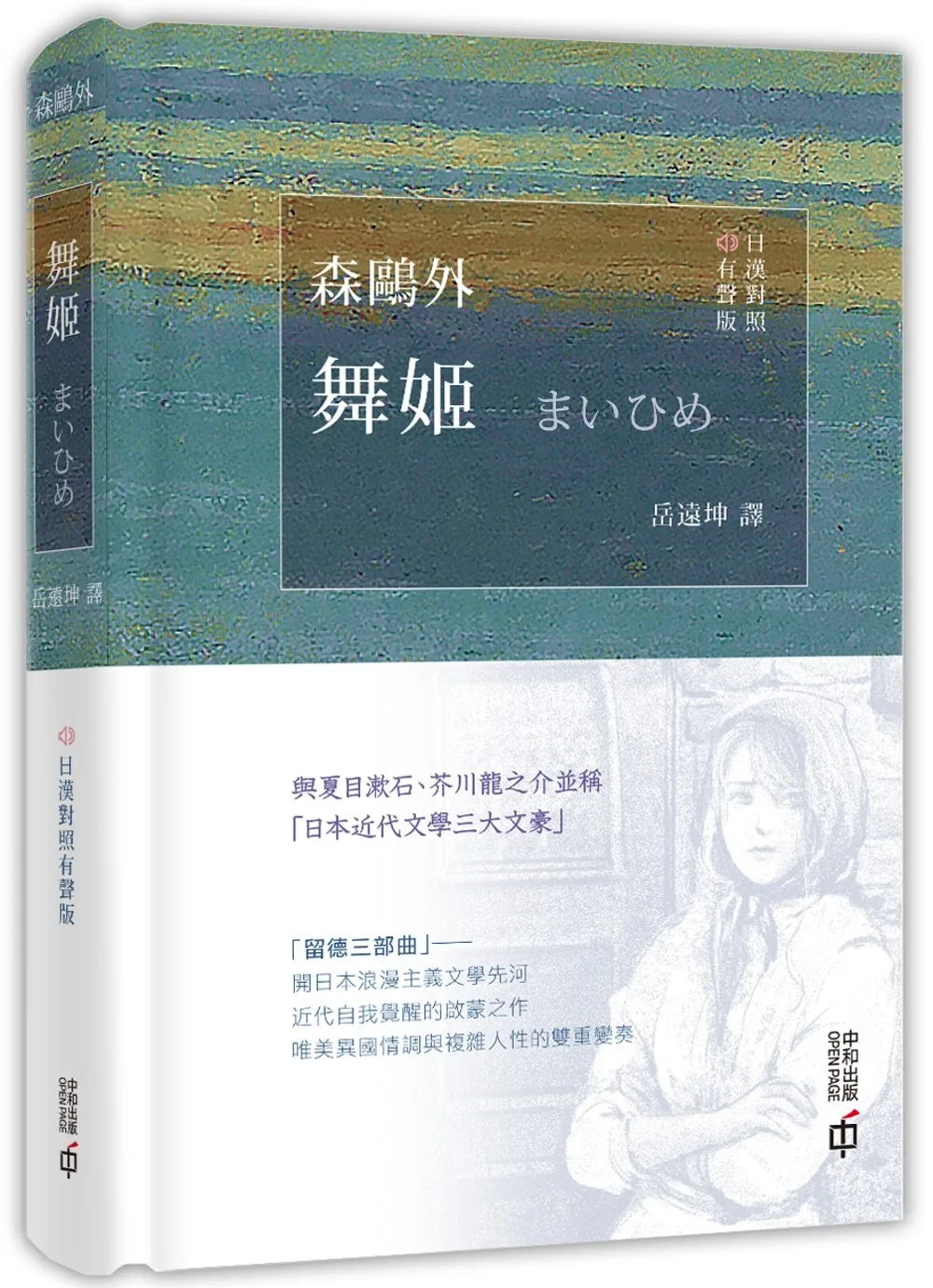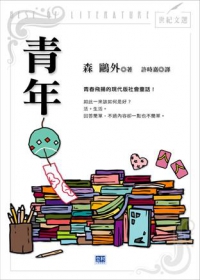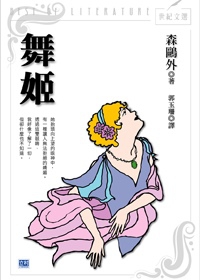緒論
大正五年(一九一六),鷗外五十四歲,辭去陸軍軍醫總監、陸軍省醫務局長等軍職,轉任文官,為帝室博物館總長兼圖書頭。此後約短短三年期間,除了照常發表雜文與短篇之外,鷗外主要完成了三部以幕府末期的儒者儒醫為題材的長篇:《澀江抽齋》、《伊澤蘭軒》、《北條霞亭》,終於把鷗外文學推上了頂峰。這時期的作品一般文學史仍然歸之於歷史小說類,但有些評家則稱之為「史傳」小說,以便與前此的中、短篇歷史小說有所區別。此外,如小西甚一則認為歷史或史傳的「史」所涉涵義過廣,所以應該另立「誌傳」一類(《日本文藝史》V,頁六一六)。其所謂誌傳之誌大概是承襲了「人物誌」之誌的用例。蓋謂僅限於誌人物而傳之之意。我在下面就採用誌傳一詞。
其實,無論用任何既有的文學術語都無法概括稱呼這些作品。說是歷史不像歷史紀錄,說是傳記不像傳記體式,說是小說更不像小說的虛構創作;可說是鷗外獨創的類型。在文學史上前所未見,其後也不見踵其武而來者。要之,在這所謂儒醫三部曲裡,作者即敘述者「我」,在敘述過程中,從頭到尾,公然直接一再出現。而以「我」的觀點,試著盡量客觀地呈現歷史人物的真實。在某種意義上,頗像新聞記者對歷史人物的「調查報導」,而不失其最重要的文藝本質。
其中的《澀江抽齋》公認是鷗外一生的代表傑作。鷗外身為明治大正年間的官僚文人,表面上為日本「文明開化」啟蒙運動的先驅;而在另一方面,卻隨著年齡的增加,反而懷念起小時候的漢學教育,不由得仰慕江戶時代武士的志節與儒者文人的風範。他在尋訪相關的歷史文獻過程中,好幾次遇到津輕藩醫官「澀江道純」與「抽齋」的名號,覺得是值得「親愛」、「敬愛」、「敬畏」的人物;經過多方多時的查證之後,才知《經籍訪古志》撰者之一的道純,就是蒐集古武鑑古江戶圖的抽齋。敘述者「我」又驚又喜,不禁這樣寫道:
我又這樣想著:抽齋是醫師,也是官吏。而且遍讀經學諸子等哲學方面的典籍,也讀歷史,也讀詩文集等文藝方面的書。他的行跡與興趣與我自己的頗為類似。不同之處只在古今異時、生不相及而已。不,不然。其實有一大差別,就是抽齋在文史哲各領域裡,寄情於考證之學,而達到了足以揚其名聲的地位;而我卻陷於駁雜淺薄的困境而不能自拔。面對著抽齋,我不得不感到慚愧。……假使抽齋是我同時代的人,我們兩人的袖子肯定會在小巷子的水溝蓋上摩碰過;他與我之間有志同道合的親近感。抽齋是能讓我感到親愛的人。(《澀江抽齋.其六》)
就是由於這種超越古今的奇緣際會、一種於我心有戚戚焉的認同親和感,鷗外為之驚喜而大為感動,或者應該說獲得了靈感與鼓勵,才開始了調查抽齋行跡的考證之旅。結果就是這本《澀江抽齋》。
這部不像傳記的所謂誌傳,雖然以《澀江抽齋》為題,所記述的對象卻不只抽齋一人。全書以抽齋為軸心,前半部敘述抽齋父祖的氏族系譜、抽齋的生前事蹟,同時旁及家族與師友多人的交往情形;後半部則完全屬於抽齋去世之後,敘述遺孀、子孫等人的境遇;直至抽齋歿後第五十七年,即大正五年,亦即《澀江抽齋》完成之年,才結束了全書。敘述者「我」的想法是:
依一般慣例,傳記大抵以其人之死而結束。然而景仰先賢的人,卻總禁不住想問其苗裔的情形如何。因此我雖已寫完了抽齋的生涯,卻猶不忍就此擱筆。我想在這下面附帶記述抽齋的子孫、親戚、師友等的境遇。(《澀江抽齋.其六十五》)
全書從一開始,「我」就帶著他的讀者,上下古今、東西南北,隨時到處,蒐集墓誌、傳記、年譜、雜記之類的書面文獻;尋訪抽齋的遺族與專家學者,徵求他們提供相關資料或意見;然後進行比對考證、去蕪存菁,以簡潔的筆法,加以書寫出來。所以有人戲稱這是一種「考證小說」。
本書所涵蓋的——或所反映的——時代,主要從幕府末期至明治年間,大約相當於整個十九世紀,在日本近代史上,可說是前所未有的動盪的大時代。無論在政治制度、文化思想、生活習慣、價值觀念等等各方面,都正在進行著東與西、新與舊、傳統與近代的衝突與磨合。《澀江抽齋》所寫的就是一群活躍於幕府末期的儒學、儒醫界——但幾乎已被歷史埋沒——的實際人物。這些人物都各具個性,尤其是主人公抽齋及其師友,如池田京水、森枳園、長島壽阿彌,還有抽齋的家族,如第四任妻室山內氏五百、次男優善(矢島優)、四女陸(杵屋勝久)、嗣子七男成善(澀江保)等腳色,在鷗外寧簡勿繁的筆端下,輪廓清晰,莫不栩栩如生、形象突出。然而,最突出的人物應該是敘述者「我」了,也就是作者鷗外本人。就是他這個「我」在書中處處出現的身影、刨根問底的認真態度,與「我猶彼也」的親和感,給人印象最為深刻。這在《伊澤蘭軒》、《北條霞亭》等誌傳小說裡,也都有同樣的傾向。
鷗外開始在報紙上連載《澀江抽齋》的大正五年(一九一六)一月,五十四歲。環顧日本文壇,自然主義運動已經衰微或變質,提倡所謂新理想主義與人道主義的白樺派,如武者小路實篤、有島武郎、志賀直哉等,繼之而起。同時另有各自為營的少壯派作家,如芥川龍之介、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佐藤春夫等,陸續嶄露頭角,成為文壇的新星。至於兩位長輩大老夏目漱石與森鷗外,則在經過東方與西洋、舊與新的對立掙扎之後,似乎也各自找到了不同的出路。
留英而討厭英國的漱石,終於設法把東與西隔開,東是東、西是西,讓東西並行不悖。換言之,一方面仍然堅持西方反映現實的小說概念與模式,再不喜歡也要繼續創作《明暗》那樣的長篇虛構小說(一九一六年六月起連載);同時在另一方面,則「擬將蝶夢誘吟魂,且隔人生在畫村」(大正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漱石詩),也寄情於漢詩與南畫的世界,藉以追慕東方傳統的詩情與禪心,而終於到了嚮往所謂「則天去私」的境界。
至於留德而愛上歐洲的鷗外,則設法超越——或不再斤斤於——東西方文明的對立,乾脆回到東方傳統裡去尋求存在的意義。雖然還是難免以西洋的眼光看待東方的問題,卻能以東方的傳統方式與態度泰然處之,而自己似乎並不覺得有任何矛盾。這種超然的態度不是無懈可擊。但是讓鷗外在其文學生命裡,總算找到了可以從容漫步的世界。
《澀江抽齋》的歷史時空與人物就是這樣的世界。在鷗外筆下「再現」的這個非今世今生的世界裡,鷗外也為日本文學創造了一個新的典型,即小西甚一所稱的「誌傳」體小說。這種體裁,在許多方面,與一般所認識或看過的近代小說幾乎背道而馳。可謂文學史上的異端。
有人推測,在完成了《澀江抽齋》等三部曲之後,鷗外還有計畫創作其他幕末儒者儒醫的誌傳,可惜天不假以年,享年六十而歿。我倒覺得,如果鷗外能多活十年二十年,他一定會突破誌傳的範疇,再創新招,另闢園地,對日本文學甚至世界文學做出更大的貢獻。
這就是森鷗外,一個日本近代文壇巨擘的文學人生歷程。
?
鄭清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