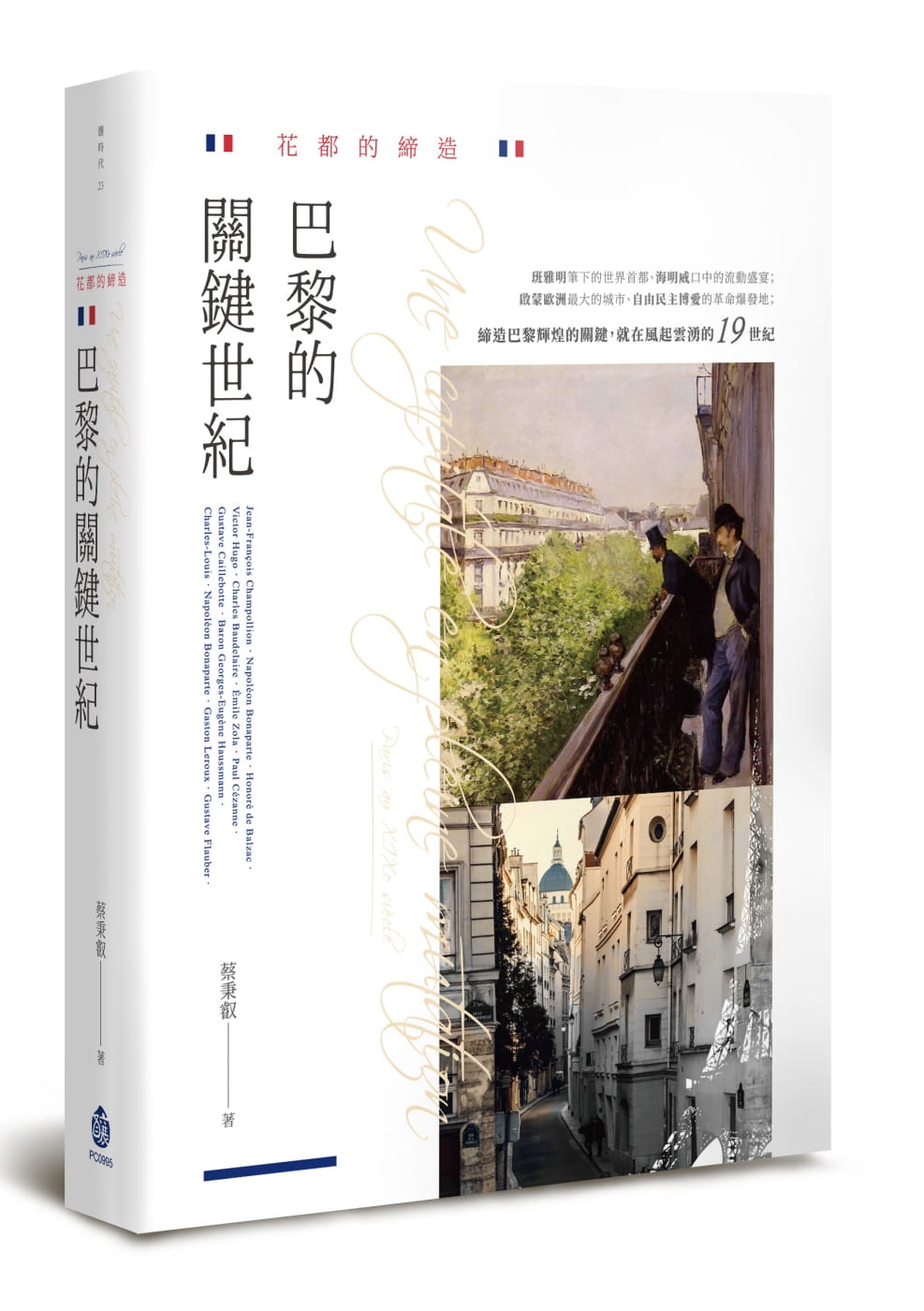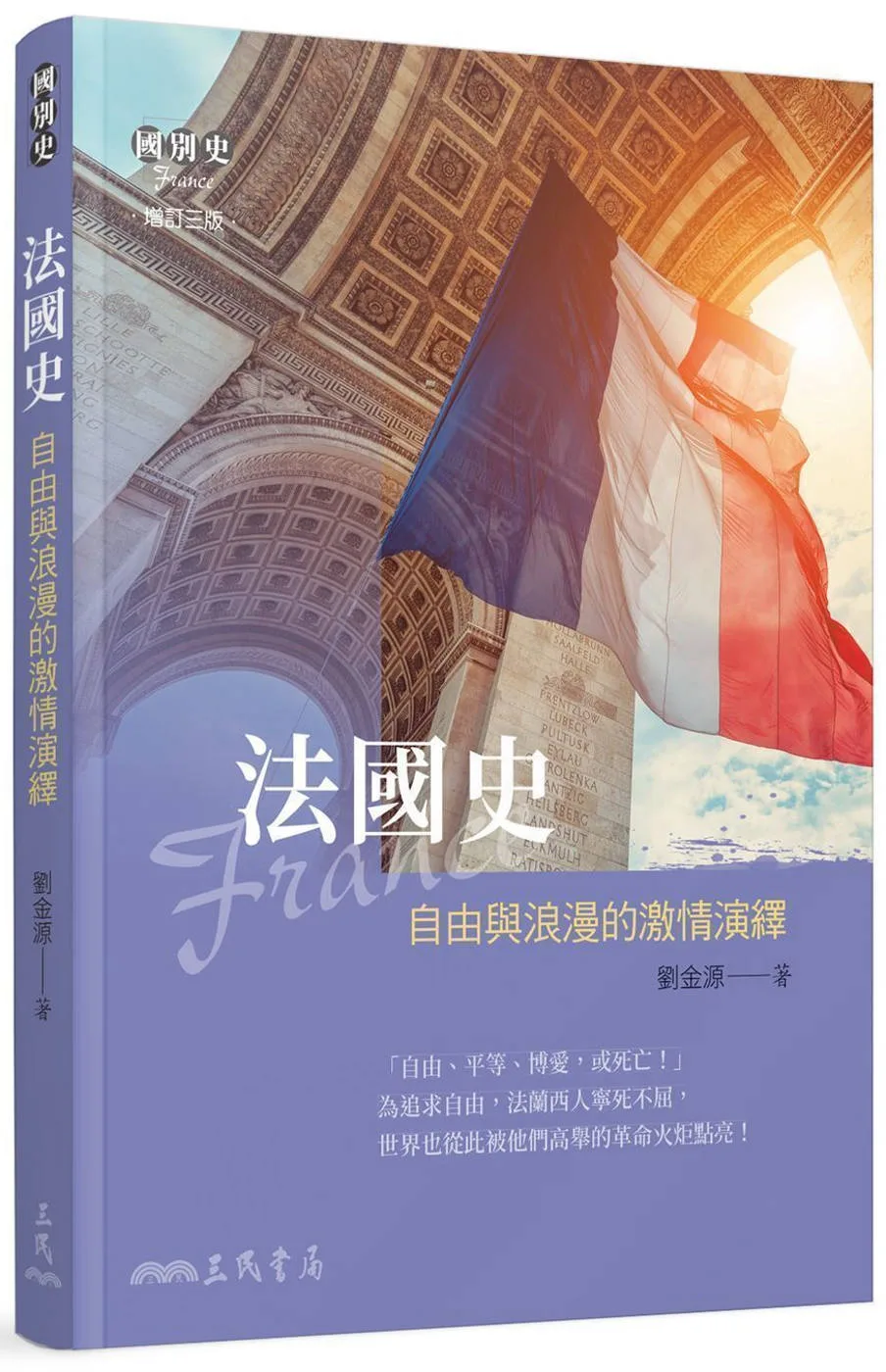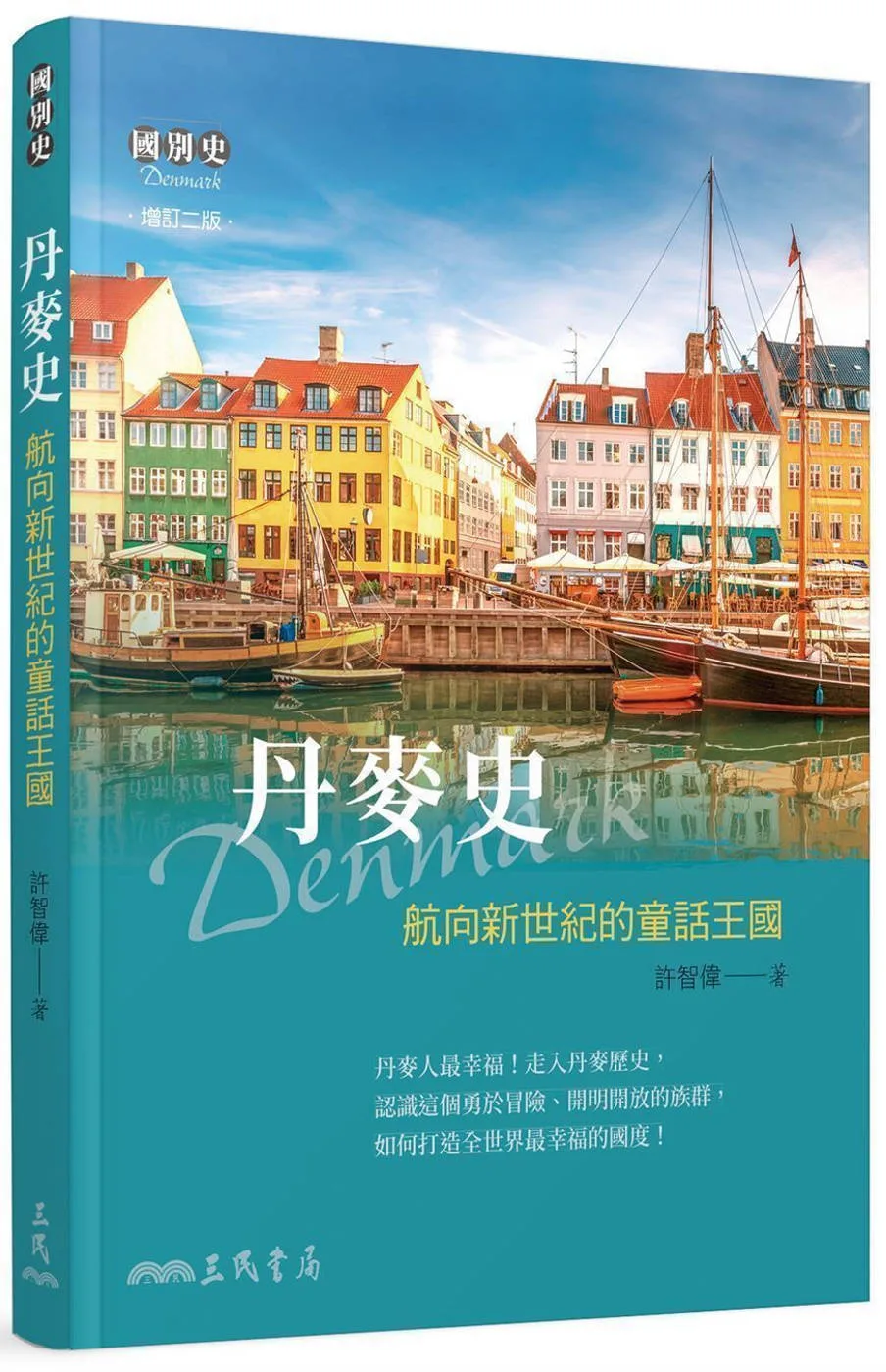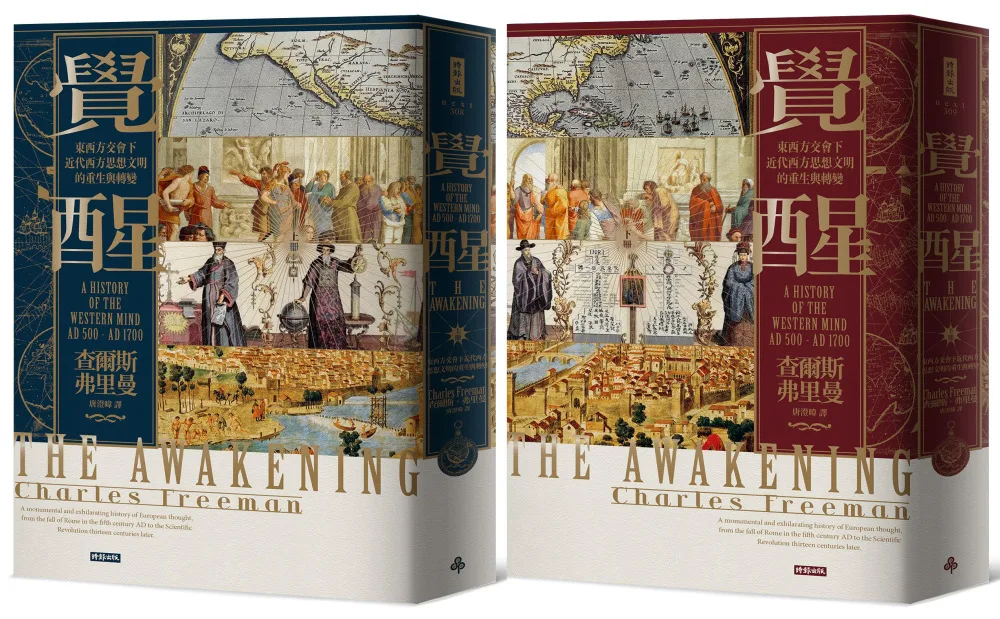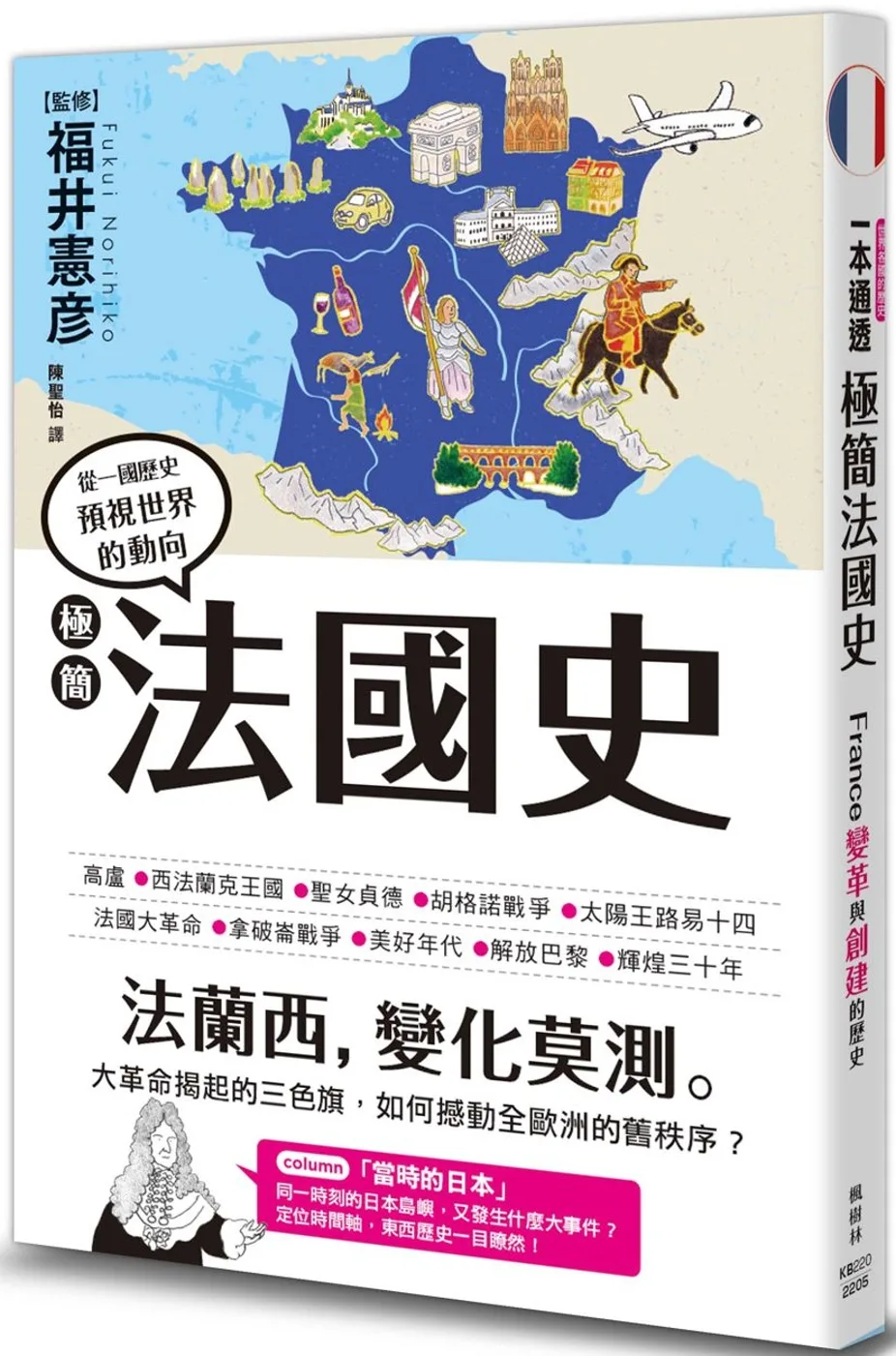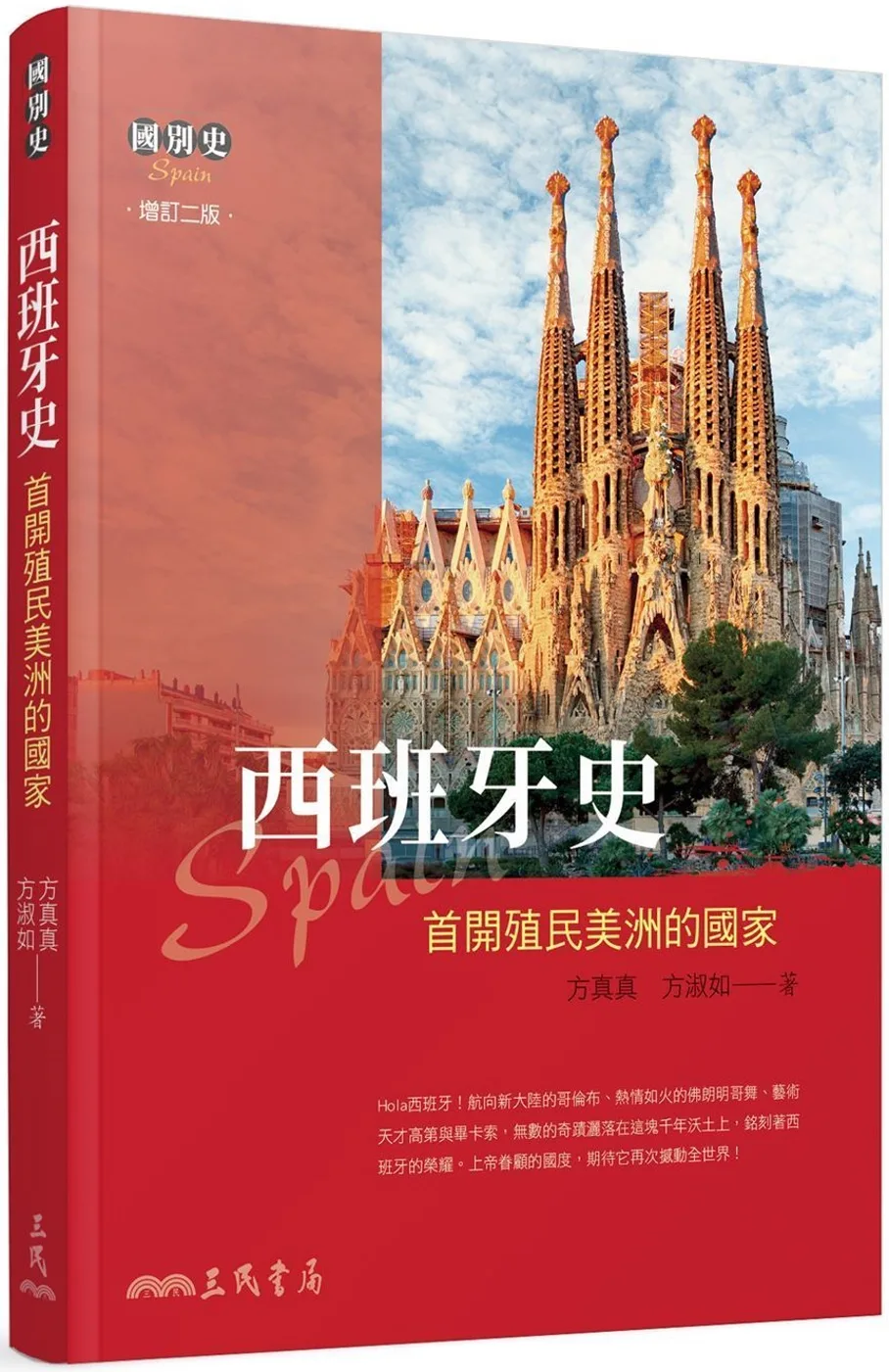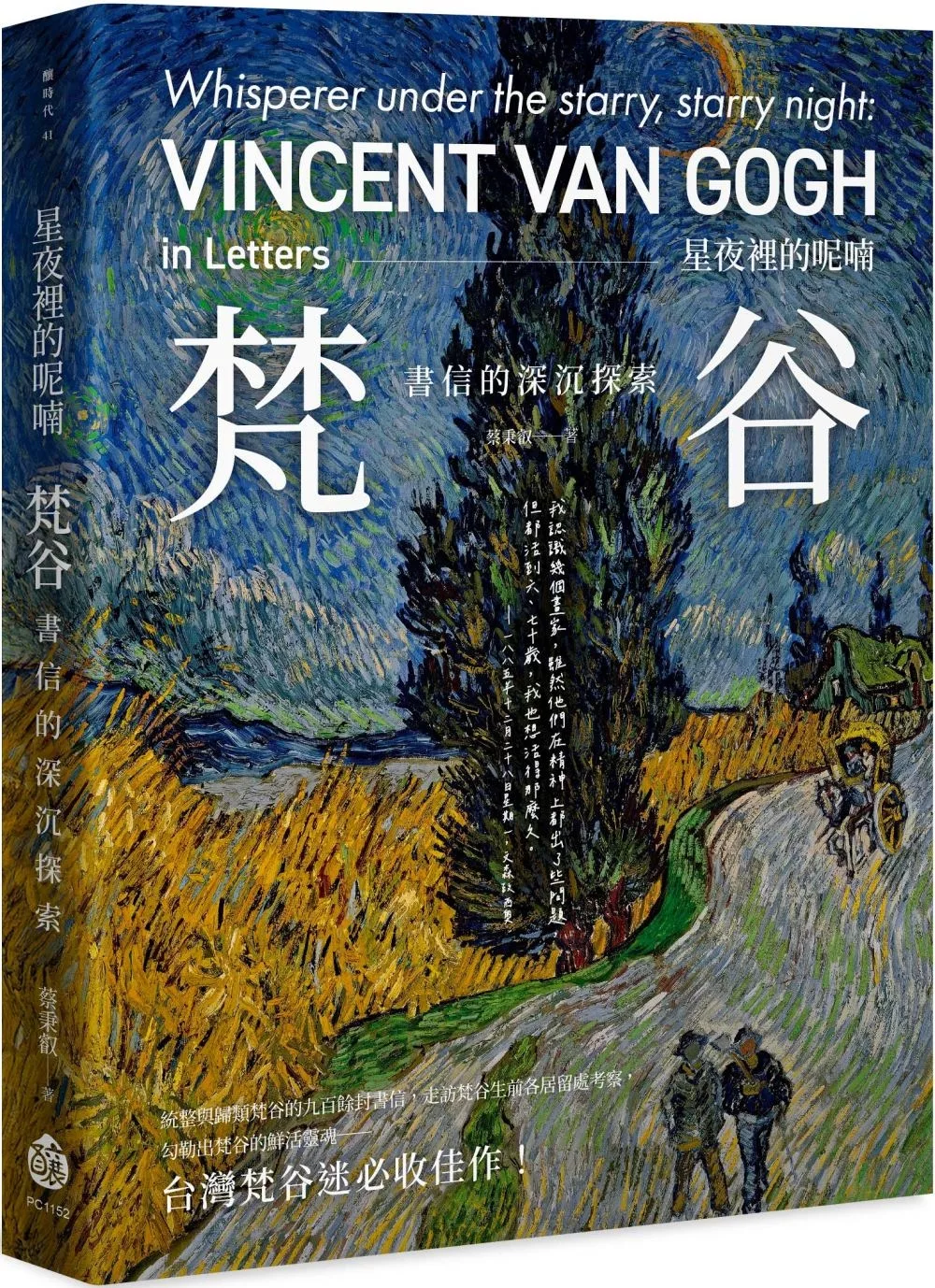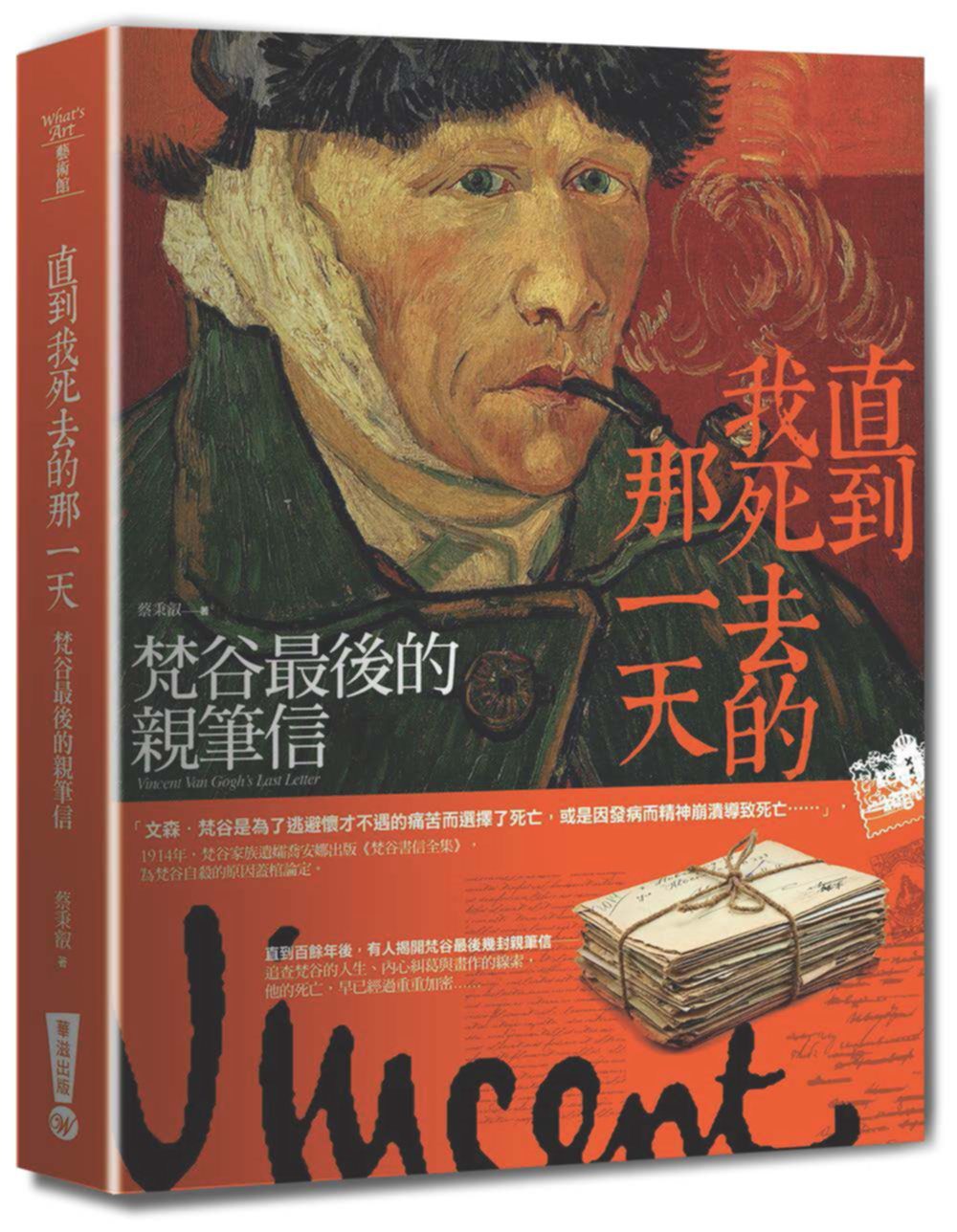推薦序
也是東亞人心靈的十九世紀世界首都
這是一個很耀眼的出版企畫,作者將十九世紀的巴黎以「立體寫作法」進行重組,當歷史人物的身影走近時,我們看到其中有政治人物、小說家、學者、畫家、建築師,這時遠景浮現了該年代文學作品的眾角色,有的振臂疾呼,有的侃侃而談,有的溫柔輕語,然後一陣腳步聲取而代之,那是二十一世紀作者疾行在十九世紀的石磚路上。這是一部大河記,一部揉合了田調、史實、記憶、再現(representation)、想像的大河記,一部值得歷史學家及人類學家拿來做研究素材的大河記:東亞這小島的知識分子在2020年時是如何遙想那十九世紀的世界首都?
不論能否用英語溝通,每個人都認識英語,講得上幾個字、幾個句子,那是最普世的語言,最具共量性的文化資本尺度,而且,這個尺度的最大值是沒有其他語言比得上。英語之於全世界語言的地位,就如同巴黎之於全世界的城市,無論造訪過與否,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巴黎,清晰或模糊,彩色或黑白;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巴黎,19世紀的世界首都》一書即揭示:在談巴黎一地的社會史同時,已經談出整體人類現代性的肇始;這個時空形成一種智性的原鄉、一個觀看現代世界的起點,許多學科肇始於此,東西兩半世界的眾多交流也與它有重大關係。全世界的文人無論操哪個語言、來自哪個角落,都可以透過閒聊它的歷史、美術、文學、哲學、社會科學……,來較量一下彼此的深淺,亦即,對它的認識形成一種最具共量性的文化資本;地球上或有其他的城市也能提供這樣的趣味,但深淺尺度的最大值,終究得將眼光飄向巴黎。希望,我這樣的說法不是一種迷信。
在巴黎的日子裡,學上了法國人講話的風格,留學荷蘭的好友Y感嘆說:「荷蘭是離天堂比較近的地方。」「對,坐Thalys高鐵才三個小時啊。」我笑回;留學西班牙的好友J說:「我住的城市有四個世界文化遺產。」「為什麼要這麼多?我住的城市,一個就夠了,就是整個城市。」轉身面向巴黎卻是甜言蜜語:「為什麼妳在天氣這麼糟的時候還是可以美成這樣?」好多次都傻傻望著流下淚來。如果迷信帶來偏見,那愛情是更巨大的偏見,巨大到卡住我的人生十二年。
去年搬回臺灣,我與藝術家太太把家當款一款,居然款出兩個貨櫃來。Emile Guimet數月的日本行帶回來的物件都可以作為吉美博物館(Musee Guimet)的起家底,那我們長居十二年的「後送行李」──其中大都是百年以上的布爾喬亞家具……,好像可以在打狗做些什麼?或許是「復刻」出一個十九世紀藝文沙龍(salon litteraire)?在巴黎的公寓裡,因著一種生活情趣,我們原本即經常更換內部裝飾,為此還得租用倉庫來堆放季節不對的「過季品」,這些古物或骨董有的是世居那裡的朋友因搬家相贈,有的是我們從事古畫買賣所順道購藏。在整理這些家具之際、在復刻工作籌畫之際,出版界的朋友忽然寄來這本書的稿子,啊,好巧,在同一個城市,有一個人跟我們一樣在時時遠眺著十九世紀的巴黎。
儘管久居巴黎,熟到土生土長巴黎朋友也會驚豔於我的導覽,但作者對於十九世紀巴黎的飽讀詩書仍令我自嘆不如;原來,塞納省省長奧斯曼(Georges Eugene Haussmann)的政界人生是從我語言學校所在的普瓦捷(Poitiers)起步;原來,政治生命一夜起落的Georges Boulanger,勝選之夜時人所在的餐廳就是九年後左拉(Emile Zola)振筆寫下〈我控訴……!〉的那間,目前由來自美國的高級時尚名牌所占據著;原來,我們去過很多次的一家米其林星級餐廳,再走幾步就是巴爾札克(Honore de Balzac)辭世的地方,他在那裡「全身水腫使皮膚變得像豬皮,動脈炎還引起了壞疽,腐爛處的繃帶發出陣陣惡臭」;最後,造訪住在聖丹尼門附近的好友K總會和好幾位性工作者在街上擦身而過,原來,1848年民變(insurrection)時這裡被堆了街壘(barricade),當時一位性工作者站到前面去,向政府軍大喊:「膽小鬼們,開槍吧,如果你們有膽量向一個女人的肚皮開槍!」隨即迎來一陣無情的槍響,而另一位性工作者卻無畏地挺身而上……
史家一般把法國的十九世紀界定在1814到1914年之間:拿破崙退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或者廣義地往前推至法國大革命。但為何是十九世紀?站在巴黎街頭舉目望去,沒有一個時代比起這段期間對於今日城市容顏更有決定性,不論是一排又一排很雷同的奧斯曼式建築(immeuble haussmannien),或是醒目的觀光景點,多是誕生於此:如拉雪茲神父公墓、兩個凱旋門、旺多姆圓柱(La colonne Vendome)、聖米歇爾噴泉、瑪德蓮教堂、七月柱、協和廣場的噴泉、聖拉札車站、加尼葉歌劇院、聖心堂、市政廳、大小皇宮、亞歷山大三世橋、艾菲爾鐵塔、春天百貨、拉法葉百貨公司、地鐵新藝術(art nouveau)入口、奧塞美術館建築等等。從2010年開始,英文的Palace被借用來標示那些無上尊貴的法國旅館,巴黎歷來的十四家即有八家可溯自這年代:Le Meurice、Le Ritz、Hotel Regina、Le Shangri-La、La Reserve、The Peninsula、Hotel Lutetia、Hotel Plaza Athenee;至於一戰之前拜訪巴黎的國王們,大致上會在Le Meurice、Le Ritz、Hotel de Crillon(源自十八世紀)之一落腳。
十九世紀對於今日法國之重要,又可如歷史學家Jacques Revel所描繪:「法國記憶安穩住進了國族空間(la memoire francaise se loge aisement dans l’espace national)。」這是有其國族與政治上的意義;就國族上,那六角形的國土以國族定義出現,即地理法國與由記憶形成的國族法國在邊界上重疊起來,其實是在這期間形成的集體意識,1887年Ferdinand Buisson所出版的《小學教學與教導字典》(Dictionnaire de pedagogie et d’instruction primaire)可視為一個時代結晶,用以向孩童們灌輸而去。在政治上,被認為啟發了1980年代法國政治史新研究取徑的《法國的右派們》(Les Droites en France)一書(第一版在1954年),Rene Remond指出今日法國政治結構是延續了那源自法國大革命、而於十九世紀不斷打造出來的summa divisio(深層分裂):左派與右派,二十世紀的右派可細究為反革命右派(如維琪政權)、自由主義右派(如季斯卡派)、凱薩式右派(如戴高樂派),這三系意識形態皆可在十九世紀找到很直接的根源,依序見於波旁正統黨、奧爾良黨、波拿巴黨;意識形態的分裂無法分割這個國族,因為大家擁有同一個十九世紀,各黨各派都是從這個共享的記憶資源庫去發展敵友互動。
法國在廣義的十九世紀被擠入了十幾個體制,短有數月的巴黎公社、百日王朝,長有數十年的第三共和;法國人在帝國制、王朝制、共和制之間來來回回數次,直到第三次王朝復辟在1879年流產才確定了共和制的鞏固。這不只是法國史中最為縝密的一段年輪,放在歐洲尺度也是如此:十九世紀的法國無疑成了人類政治體制的實驗室。
體制如此多變,不少人主張是因為首都街道紋理易生民變;在1830年七月革命、1832年六月暴動、1848二月革命、1848年六月蜂起、1871年巴黎公社、1968年的五月學工運,石頭與家具往路上一丟,堆出街壘就成為戰鬥舞臺,雙方對峙二邊;後來,塞納省省長奧斯曼重整此紋理,將巴黎多處開腸破肚,以便讓政府軍得以直奔任何動亂處所;1866年流亡比利時的革命家Auguste Blanqui寫下了《武裝奪取的指示》(Instructions pour une prise d’armes),詳細闡述了巴黎街壘的設置技藝;十九世紀全球大概只有這一都會擁有著一本教導如何民變的「使用手冊」,儘管它的到來已經快要趕不上巴黎的空間變化了。
在巴黎藝術家及作家的手下,每一場民變都孕育出一道道藝文風景,德拉克洛瓦(Eugene Delacroix)的畫作《自由領導人民》講的是1830年那場,雨果(Victor Hugo)的《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採用了1832年那場做背景,馬內(Edouard Manet)留下了巴黎公社街壘的石版畫……,這些才子們在這本書被談論與稱頌,然而,他們在當年並非站在一個主流品味的位子上。
這些人可以被視為十八世紀啟蒙時代文人(homme de lettres)──以百科全書派為代表──的繼承者,但和這些前輩不同,十九世紀的他們不依賴權力中心作為「藝術保護者」,創作也不受到王室訂購與否的影響;事實上,前輩並沒有在十九世紀重現而成為他們的競爭對手,因為在狹義的十九世紀裡,並沒有一位君王或其身邊的人對文化品味的演進產生足夠的影響:Alexis de Tocqueville稱Louis-Philippe國王沒有什麼藝術概念,就算Mathilde Bonaparte及Napoleon-Jerome Bonaparte積極介入文化圈,也很難描繪出他們的偏好主導了什麼。舊的藝術機制──法蘭西學院、官方沙龍、法蘭西喜劇院等等─並沒有失去其在品味控制的重要性,只是和政治權力者的個人偏好脫鉤了。十九世紀的主流品味不再是官方藝術(art officiel),而是布爾喬亞品味(gout bourgeois);這是一種墨守常規主義(conformisme),保守且拘泥於道德框架,支持偏好古典題材的學院派,不過,也懂得擁抱現代化帶來的技術新事物。
就此品味可見:法蘭西喜劇院不停地重複上演古典作品,建築形式不停地搜尋古典元素並湊合起來:即後來傳到臺灣的折衷樣式;在文學世界裡,當年最受肯定的也不是大小仲馬、雨果或左拉,而是像Eugene Scribe這樣的劇作家,當年威爾第(Giuseppe Verdi)為了能在巴黎歌劇院演出,還得接受他丟來的劇本,但今日人們幾乎忘卻了他所有的作品;至於畫市裡最為被推崇的大師:Theodore Chasseriau、Eugene Deveria、Horace Vernet、William Bouguereau、Ernest Meissonnier、Franz Xavier Winterhalter、Rosa Bonheur、Alexandre Cabanel、Jean-Leon Gerome,全是服務於布爾喬亞品味的學院派,他們中間也沒有一個能將當年的名望延續到今日;更糟的是,當訂購者過於介入時,還會擦槍走火出art pompier(消防員藝術),這個負面標籤是源自歷史題材畫作經常出現戴著金屬頭盔的人物,這讓人想到消防員。
打頭陣挑戰學院派的是1820及1830年代的浪漫主義,這首先是對古典作品的否定,指那是祖先們才會有感覺的過時作品,其次是強調作品要能表現出新時代的深層感情,主角人物要能召喚激情而不是理性;雨果、德拉克洛瓦、大仲馬皆屬浪漫主義的創作者;歷史學界也受到影響,Jules Michelet在其《法國大革命歷史》(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francaise, 1847)一書裡,即以抒情筆調寫下對巴黎人的歌頌。浪漫主義之後是寫實主義及自然主義,從1840年代中葉開始,庫爾貝、杜米埃、左拉、米勒這些創作者陸續挺身挑釁布爾喬亞品味:世界是怎樣就畫出怎樣、寫出怎樣,不用考慮什麼藝術固有的美學標準。最後,一群被官方沙龍拒絕的畫家們集結起來,從1874年第一次辦展就確定了他們的印象派名號,群眾湧入不是來欣賞叛逆,而是因為畫作內容難以理解到好笑;但不過幾年之後,學院派就要被迫將市場一步步地讓出來了。
從浪漫主義到印象派,這些十九世紀的巴黎叛逆才子集體創造出一個被社會所肯認的新身分,他們的創作不受「藝術保護者」擺布,也不去迎合布爾喬亞的主流品味,他們積極透過作品再現「現下的巴黎社會」而間接地表達了公共意見,不少還直接介入時事議論;同時,儘管無法如同其挑戰對象在經濟上如此成功,他們已經可以靠著版稅過上舒適生活;那是一個可以靠著才氣化身為公共知識分子,並同時取得階級翻身的時空;今年剛辭世的Pierre Benichou稱這現象為「一種非宗教的精神權力的降臨(l’avenement d’un pouvoir spiritual laique)」。這是一個不曾出現在臺灣的現象,一方面是這裡菁英文化消費市場體弱,一方面是因為島上的創作者較為自離於土地,比如,美麗島事件沒有辦法如那一個個巴黎民變刺激出大量文學或視覺創作,而這兩方面或許有因果關係。
十九世紀時,革命法國(La France revolutionnaire)與藝文法國(La France litteraire)都形成一個歐洲尺度的霸權,以巴黎為震央,射向歐陸各大都市。同時,殖民法國(La France coloniale)身為亞洲強權,透過傳教、外交、戰爭、萬國博覽會、移民、貿易、文化與知識交流等方式,也與東亞各邦密切連結;法帝是印度支那最大的帝國、印度支那則是法帝裡人口最多的殖民地,並且,最迷惑十九世紀巴黎藝文圈的異國情調是和風主義(japonisme),因此下述狀況是很例外的:介於印度支那與日本之間,福爾摩沙與巴黎互動稀薄,僅僅出現在張聰明(Tiunn, Tshong-bing)、孤拔將軍(Amedee Courbet)、1900年萬國博覽會……幾個例子上。
在臺灣的清領時代,可能只有一個旅行讓土生土長的臺灣人踏上巴黎,那是馬偕夫人張聰明,她在隨丈夫回鄉省親時於1880年1月24日過路此地,同行的還有他們不滿一歲的長女偕瑪連(Mary Ellen Mackay)。
1884年至1885年法軍侵略越南、中國與臺澎海域,為北臺灣帶來了「西仔反」;領軍的孤拔戰績斐然,於1885年三月底拿下澎湖時被巴黎媒體封為「民族英雄」,但數週旋不幸病逝;遺體於八月時在大量群眾圍觀下抵達巴黎,國葬在傷兵院舉行;法國境內今日有七十條左右的公共道路以孤拔命名,其中一條在巴黎。
在1900年巴黎的萬國博覽會中,日本館展出臺灣地圖,文宣冊子提到臺灣,臺灣總督府派了代表前去,而臺北茶商公會則由吳文秀(Ngoo, Bun-siu)代表前去宣傳,他被莊永明稱為「第一個看到巴黎鐵塔的臺灣人」;日本館旁設有一喫茶店,吳帶去的烏龍茶在裡面供應。今日,臺灣人喜愛的奢侈品牌瑪黑兄弟(Mariage Frere)──唉啊,真巧,臺、法兩地的「兄弟茶」都很貴──是一間開設於1854年的茶貿易行與茶沙龍,其仿古風格的logo寫著「中國、錫蘭、印度、福爾摩沙」四國度,說明臺灣茶在此歷史名店的份量;或許,吳當年曾與他們接觸過。
以十九世紀的巴黎為寫作對象,沒有一位臺灣知識分子曾完成過一本如此紮實且主題多元的著作,但我相信,這只是頭一本,之後會有其他人接棒,因為它明顯還騰出許多空間給後人努力:產業革命與工人運動、大眾文化的萌生、帝國與殖民、國家認同與移民、科學、政教衝突與分離、布爾喬亞、保皇黨與共和黨、博覽會、社會主義……,事實上,就連布爾喬亞藝術也是有部分該平反,這也值得寫,都可延續「立體寫作法」來下筆。在此同時,也請容我鼓吹以同樣的寫作法應用在臺灣上,比如以上世紀末高雄柴山作為寫作標的,讓田野調查的自己、自然主義時期胡長松筆下的杜天勇,與當年柴山自然公園促進運動人物錯身而過。
除了耀眼,這本書還是一個很佛心的出版企畫:跟作者要個google map連結、粉絲專頁連結,它立刻變身為巴黎觀光導覽書;出版於1856年的《十九世紀的巴黎與巴黎人:風俗、藝術與紀念建築》(Paris et les Parisiens au XIXe siecle: moeurs, arts et monument)一書開頭寫著:「在今日,只要有著巴黎這曼妙的標題,該劇碼、雜誌或書就一定會成功。巴黎是永不止息地引人好奇,什麼也不能滿足,不管它是嚴肅的大部著作、輕鬆的出版物、歷史、年表、研究、記述、圖表、小說,統統都不能。」最引人好奇的事物需要請教最好的導覽,我們手上這本書就是全臺最有深度的巴黎導覽書:不論是心靈、智性或是觀光,作者所下的考據功夫很驚人,所展現的文字能力令人折服,他揉合了嚴肅與輕鬆、歷史研究與文藝作品的想像、過去與現下,這樣的努力與才氣,理應換來這本書的市場成功。
勸敗:「一種非宗教精神權力的降臨」是如何發生在十九世紀巴黎?讓這美好的事也發生在二十一世紀臺灣,要請您先來支持這本書。
文�魏聰洲(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CRH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