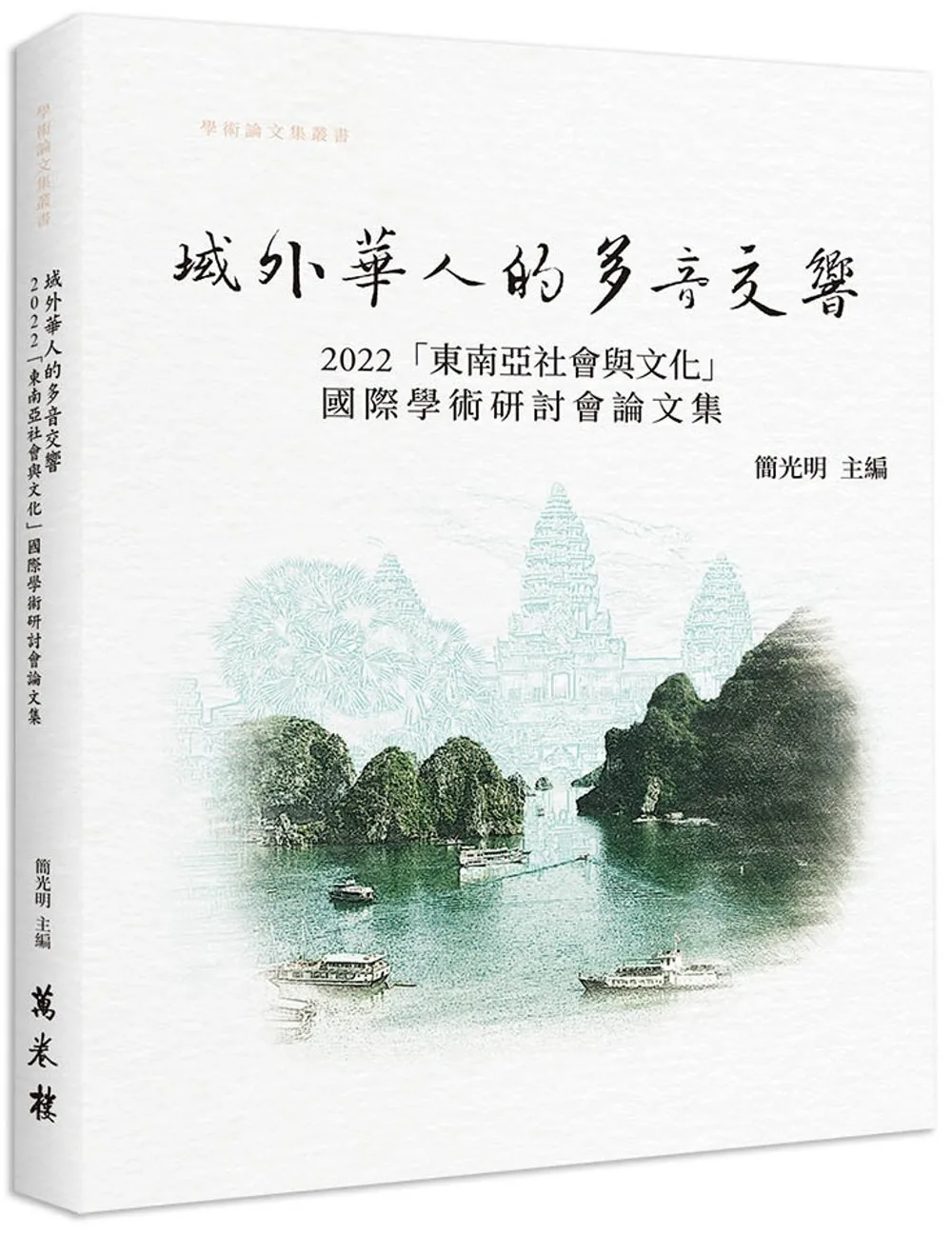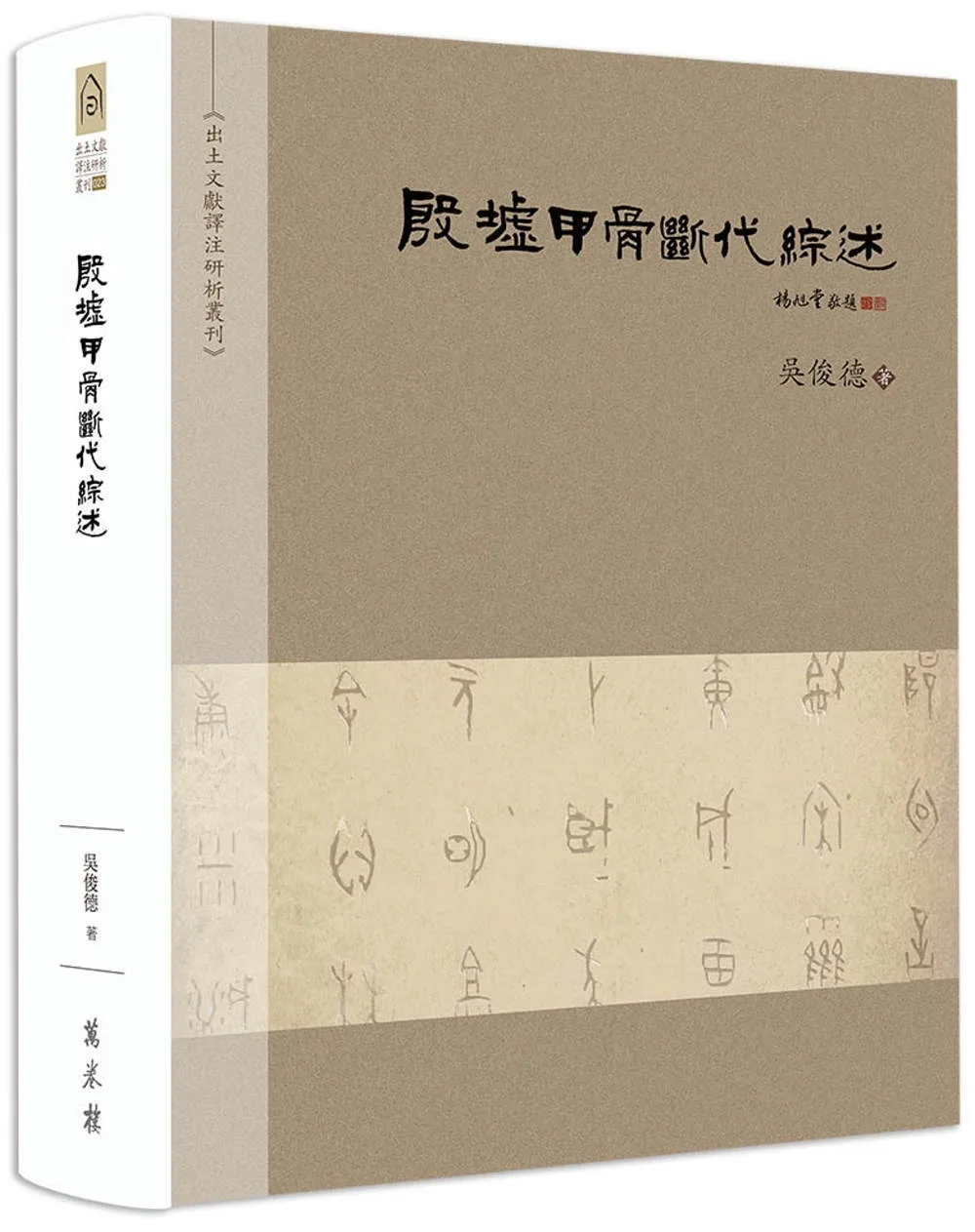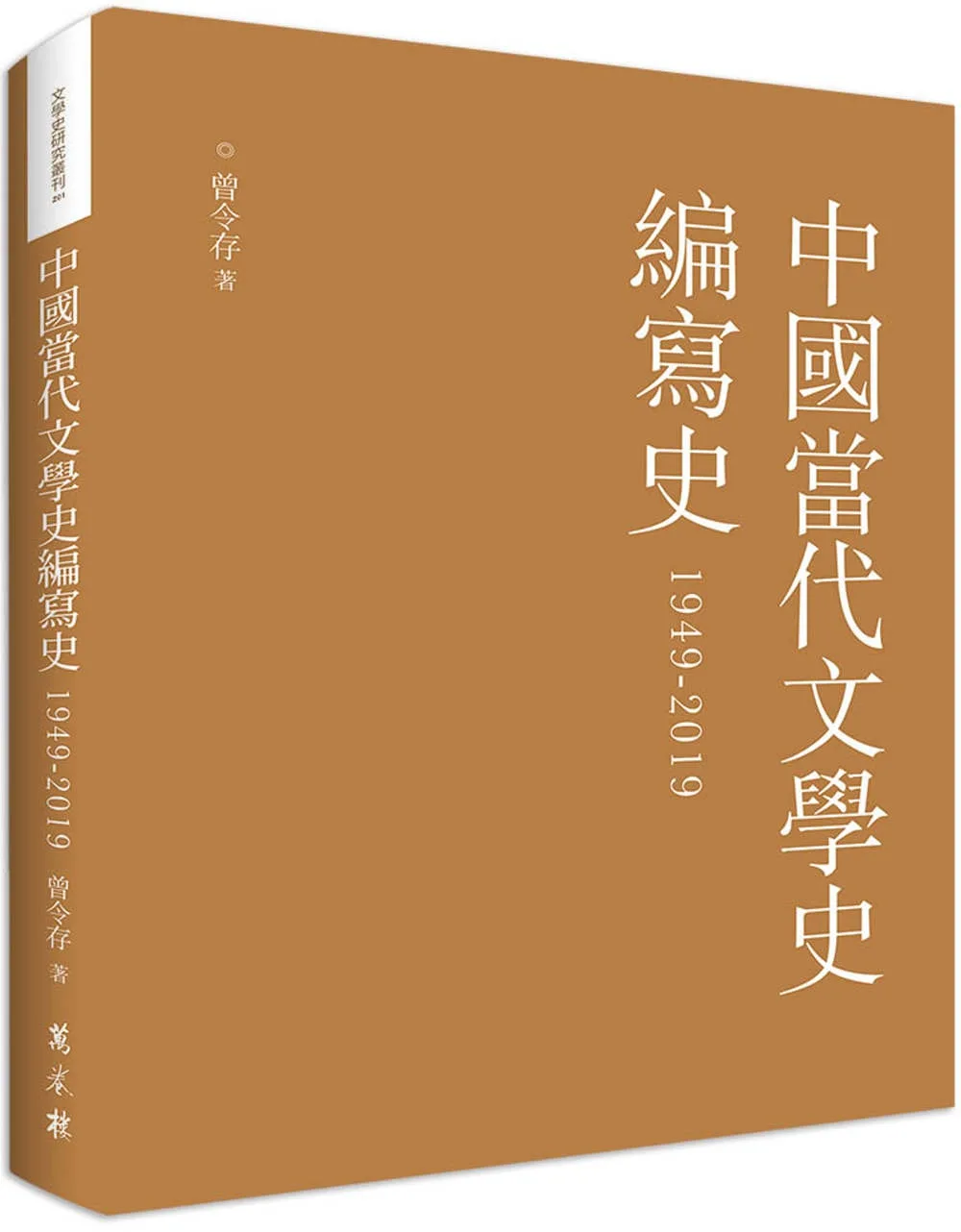序
從夢境說起
《列子•周穆王》記載了一個老役夫的故事,說他白天為主人勤勞治產,從不怨嗟,別人都覺得不可思議,想要勸他留點體力,但他卻說:「我白天為人奴僕,固然辛苦,但晚上夢到自己做了國君,快樂無比,有什麼好嘆恨的?」這種一半為奴僕、一半為國君的人生,聽起來很玄妙,我自然無緣親歷,但回首生平,卻為日夜經歷的幾乎為截然兩個不同的世界所困惑。
從有記憶以來,凡是入夢,就進到一個異於現實的時空,經常沒有明顯的座標,也少有醒著所接觸的事物,更別說夢境裏的那些人多半是陌生的!有時也想試著採用佛洛伊德(A. Freud)或容格(C. Jung)的精神分析理論來解那些夢境的緣由,只是在追溯自己繁複不已的做夢實務後,卻很難相信那些都是性欲的變種或原型的體現,倒是一種靈異學的觀點常浮出我的腦海。也就是說,那些夢境可能是累世記憶的?現,或是靈魂出體到了別的空間,或是有其他靈體來相會。因此,除了少數綺夢,其餘都在醒後備覺疲倦,也許夢中自己的靈體已經出入或跟其他靈體交接無數回了。
曾經想過,趁醒來記憶還鮮明的時候,趕快把夢中經歷的紀錄下來,那鐵定是另一個人生;但線索常在瞬間被雜事打斷,以至因為費於拼湊而放棄,迄今一直沒能有翔實一點的追記。不過,回顧從年少到現今所做的夢,卻有某些「階段差異」的跡象。如小時候常夢到懷抱巨石從吊橋滾落;稍長外出求學反多夢見徒手在空中飛翔;後來進入學術界所夢的一改變成跟他人搏鬥或被仇人追殺,即使還能騰空,也是倉皇躲避,過程都極為驚險緊張;如今從教職退下來,以為可以閒逸一陣子了,但沒想到夢境更加零碎紛亂,全然不是白晝所能複製想像。偶爾聽見有朋友長年夜夜罕夢,實在羨煞!我這輩子,大概無緣不跟另一個莫名其妙的世界發生關係。
雖然夢中情境多非我所能預料,但某些經歷卻也讓我覺得有宿緣的可能。好比幾年前,跟一位宗教師常在夢裏相遇,有一次我們隨許多人在山路行走,他說徒弟都不理他,沒人扈從,我看他病得很重,爬不上去,就揹了他一段;又有一次,我邀他去夜市,他欣然允諾,但需要戴一頂帽子掩飾身分,沒想到才出門不久,就被他的徒弟攔住,對方以好像逮到小偷的口吻說:「別以為化妝,我就認不出你來了!」這讓我醒後笑到差一點岔了氣!以我對他的了解,這種事上輩子很可能有過。後來我以一首詩希望他「來世別再輕許收徒╱給愛也是」。
還有一位曾經過從甚密的師長,我夢見他帶著我們幾個弟子,去偷館藏的一幅畫,得手後搭計程車離開,但他沒說要給我們這些幫手什麼報酬,反而把畫捲一捲放進了他的背包。我醒後,甚為悵然!對照他平常的作風,類似體恤不到別人的情況是有的,只是很難想像累世中有可能配合他去幹這種勾當。其實,我依稀記得,我們是去參觀畫展,怎麼中途變了調?至今我還在納悶這件事。
有時候,我沒有興趣交接的政治人物也會入夢來。像馬英九,2000年總統大選時,他在當臺北市長,很多人要拱他出來競選,他大概覺得時機還不成熟,所以忍住了。當時我看情勢,早晚那總統大位是他的,於是那種感覺就延續到夢中,在一次「他致信於我」的盛意後,依例為他寫了一副嵌字聯:「英雄先譽聽喝彩,九五至尊看加身」。聯語有部分是醒後續成,只不過它沒有機會送出罷了,畢竟先前我們僅在一場研討會中照過面而已。
上述這些比較有劇情的夢,還鮮活的留在記憶底層,必要時都會喚起再讓它們迴轉一遍;此外就都屬於蕪雜斷片,經常像泡沫一樣,風一吹就消失得無影無?。當然,也有些讓人感到麻渣不快的夢會如影隨形,甩都甩不掉。正如過去有位同事,擔任主管,把整個單位搞得烏煙瘴氣,我跟他鬧翻後,就在夢裏發現他把我送他的一本書,狠狠的摔在地上,至今我一想起都還感覺得到那重重的落地聲;又如我退休前所面臨的學校系所整併案,被某研發長擺了幾道,申訴無門,等一切定調後,竟在夢中跟他打了一架。我們研究生知道後,問我:「打贏了嗎?」我說:「當然,他那麼瘦小,根本禁不起一捶!」似乎這樣該氣平了,其實並沒有!只要憶起那段被欺凌的過程,就覺得那一拳還在尋找回敬的快意!
比起太多倏興忽滅且細碎不堪的夢境,這些偶現略帶「完整性」的遭遇,似乎有要暗示或象徵什麼,但又不知確切的指向,到頭來還是要「放它過去」,否則就得陷入精神分析學家那種強為解會的焦灼裏。然而,話說回來,分佔人生一半的夢中世界,不可能完全沒有意義。在我的經驗中,夢境除了異常奇詭,它的豐富變化性還遠超過現實生活,可以說場域要多寬廣就有多寬廣;在那裏面縱使會有「補償」或「慰藉」,但更多的是「失去」、「驚恐」和「疑惑」,只是都難以理解它的來龍去脈。因此,倘若要說我們能夠掌握人生,那也不過是被無數不確定的因素所制約,當中最大宗的就是做夢,那是無論如何也無從規畫、執行和評估的,但遇到時卻又真實得很。
史蒂芬斯(A. Stevens)的《大夢兩千天》裏提到,所有的釋夢人都像是在黑暗中摸象的半盲人,以為摸到了整隻象,「其實只摸到了象鼻、象腿、象尾。而佛洛伊德摸到的顯然是象的生殖器官」。這比喻的還算傳神,但他本人僅遵循容格的集體潛意識路數,不免又落入他所嘲諷的摸象行列,終究沒有顯現出新意。我會用現象學家的方式,把那無法理尋的夢境加上括號,讓它繼續主宰一半的人生,然後留意存在於罅隙中可能的「微雕」的信息。
所謂可能的「微雕」的信息,是說在我們所經歷的人文化成的世界裏,有特別纖細的一面,那是進入夢裏才感受得到的。不就有兩個現成的例子:一個是數學家卡登(J. Cardan)寫下他著名的《論微細之物》,每當他疏於寫作,夢就會以強大的力量催促他;一個是發明現代小提琴弓的作曲家塔爾蒂尼(G. Tartini),曾經困折於完成一首奏鳴曲,有一天晚上夢見海灘有支瓶子,裏面有個魔鬼懇求放他出來,雙方約定魔鬼要幫塔爾蒂尼完成這首曲子,事後塔爾蒂尼醒覺,立刻儘可能的回想而抄下寫出〈魔鬼奏鳴曲〉,這是他最受人稱頌的樂曲,但他仍感嘆道:「這首曲子是我寫過最好的,但跟夢中的曲調比起來,還是差太多了。」類似受到夢感而成就非凡的例子,應當不少,像完成鉅著《野性的思維》的李維史陀(C. Levi-Strauss)和發明相對論的愛因斯坦(A. Einstein)等人,也都有受過夢境啟發的追憶。顯然做夢跟人心靈的成長有著極為密切的關係;而我們有許多偶發的智慮,可能都源自夢境的啟示,以至一個皇皇然的人文世界早已經過迷夢精微雕琢而成形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實在不敢說每一次第的寫作都是「獨力完成」的,因為有太多的變數隱藏在夢中那個不可測度的晦暗國度,我無從細為指證,也難以虛構描摩,卻又常覺得別有力量促成。因此,集子內各作品不論是在暢敘道理,還是在跟人互動,或是在留言寄思,都摻雜了兩個世界的感悟成果。而所以用「微雕人文」命名,是為了喻示寫作在很多時候是「深致有自」的,而那細微的感觸則緣於夢境的多方含攝;出了那個世界,我們可能都無以啟動靈敏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