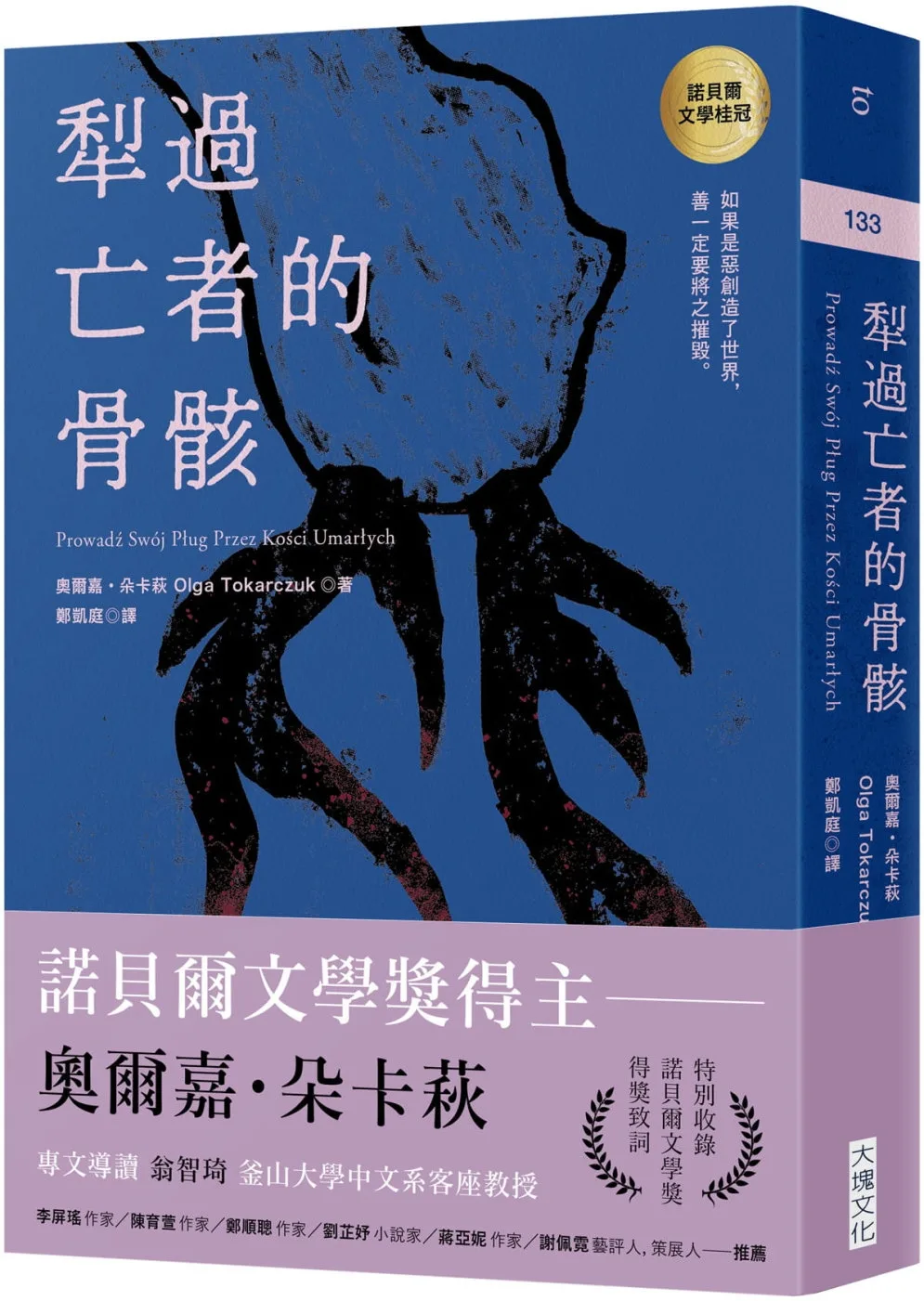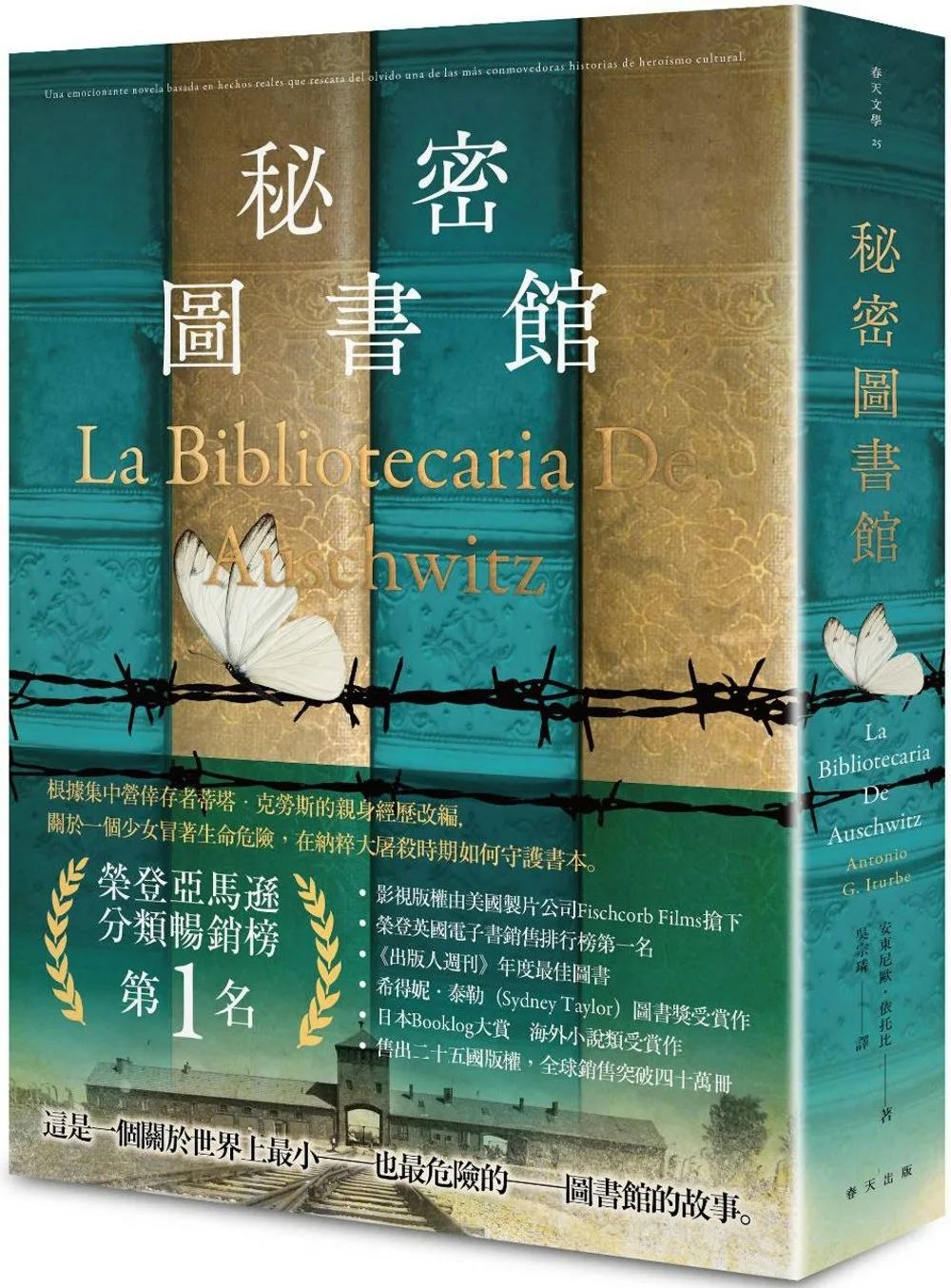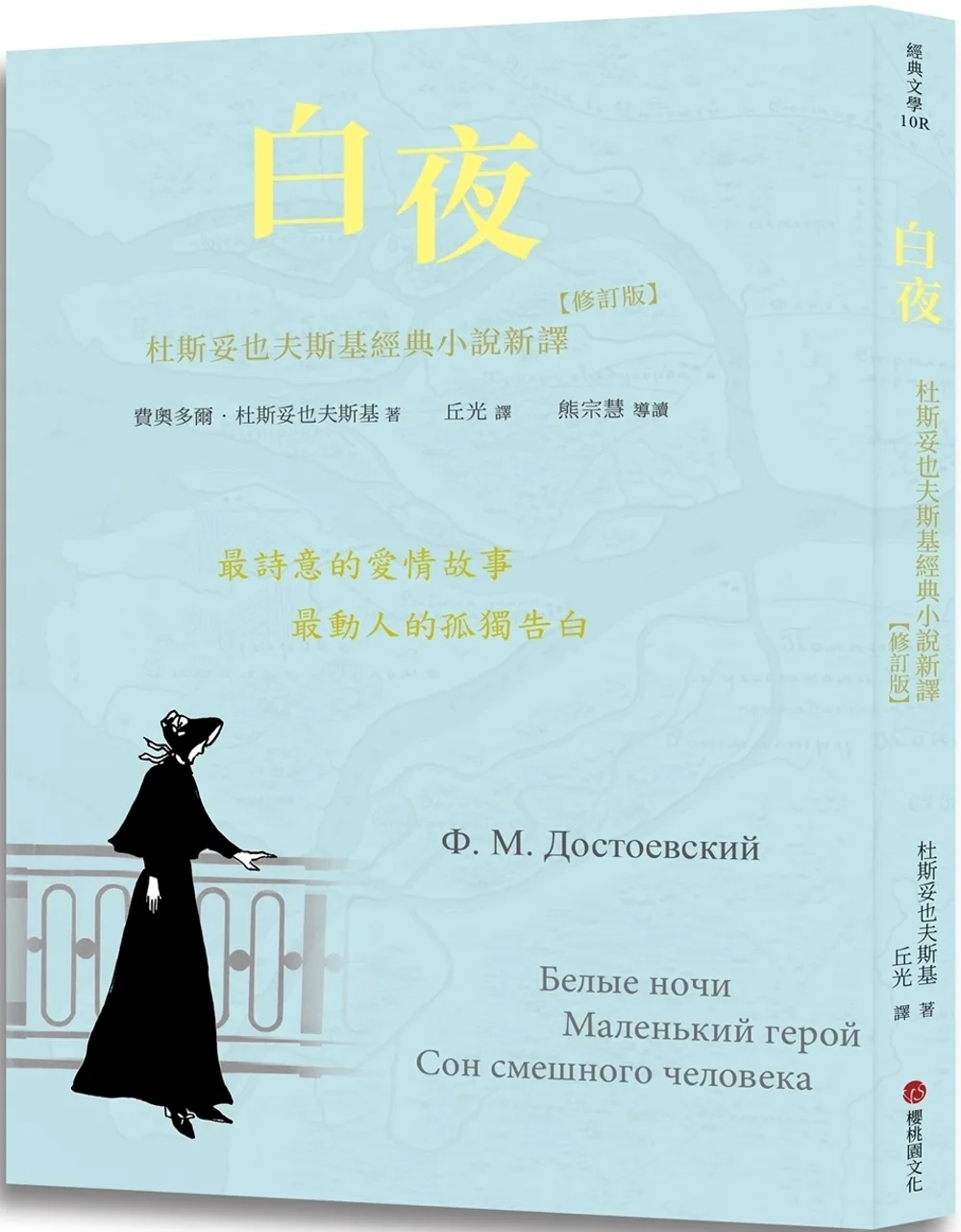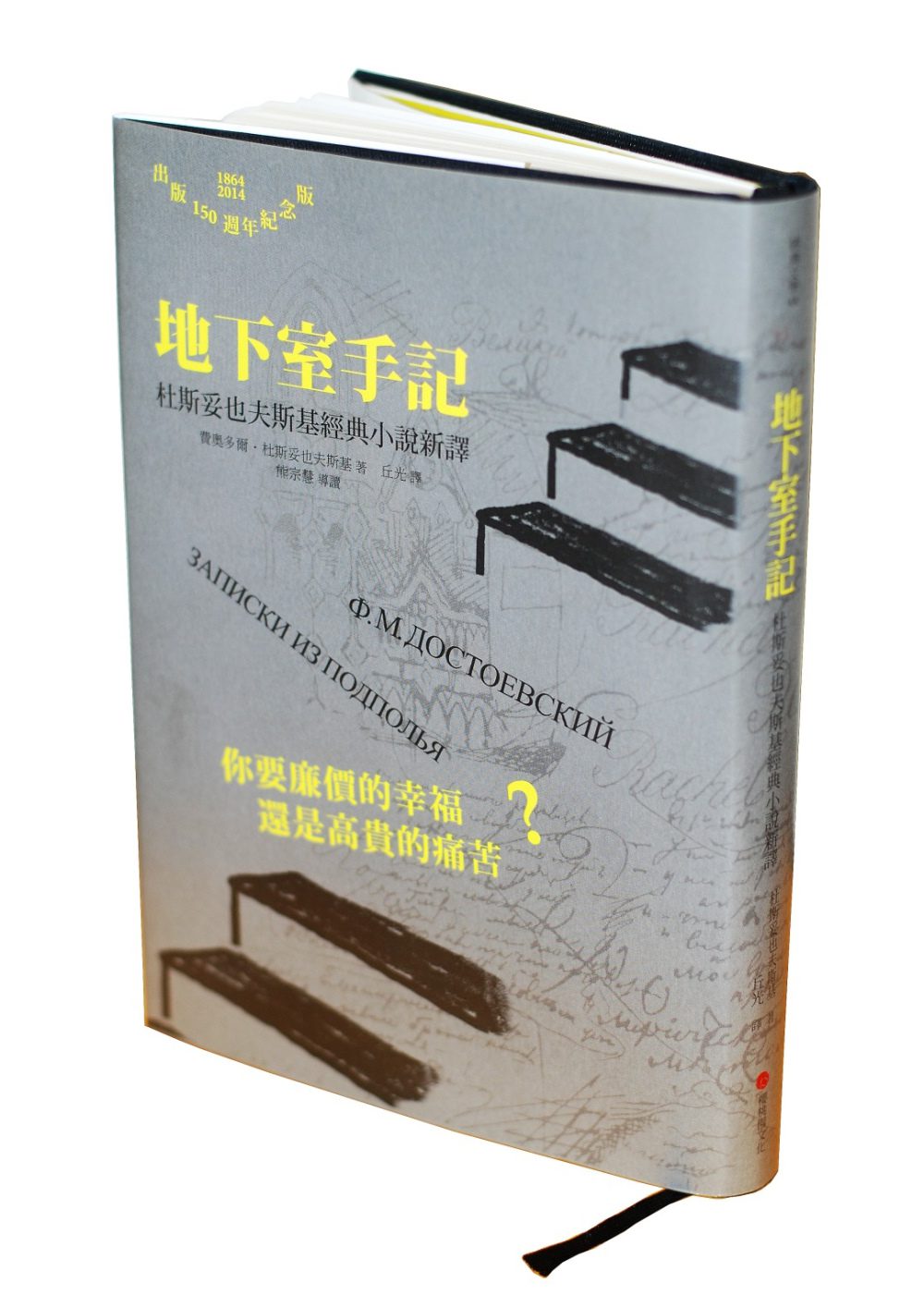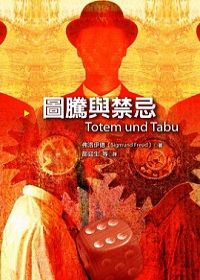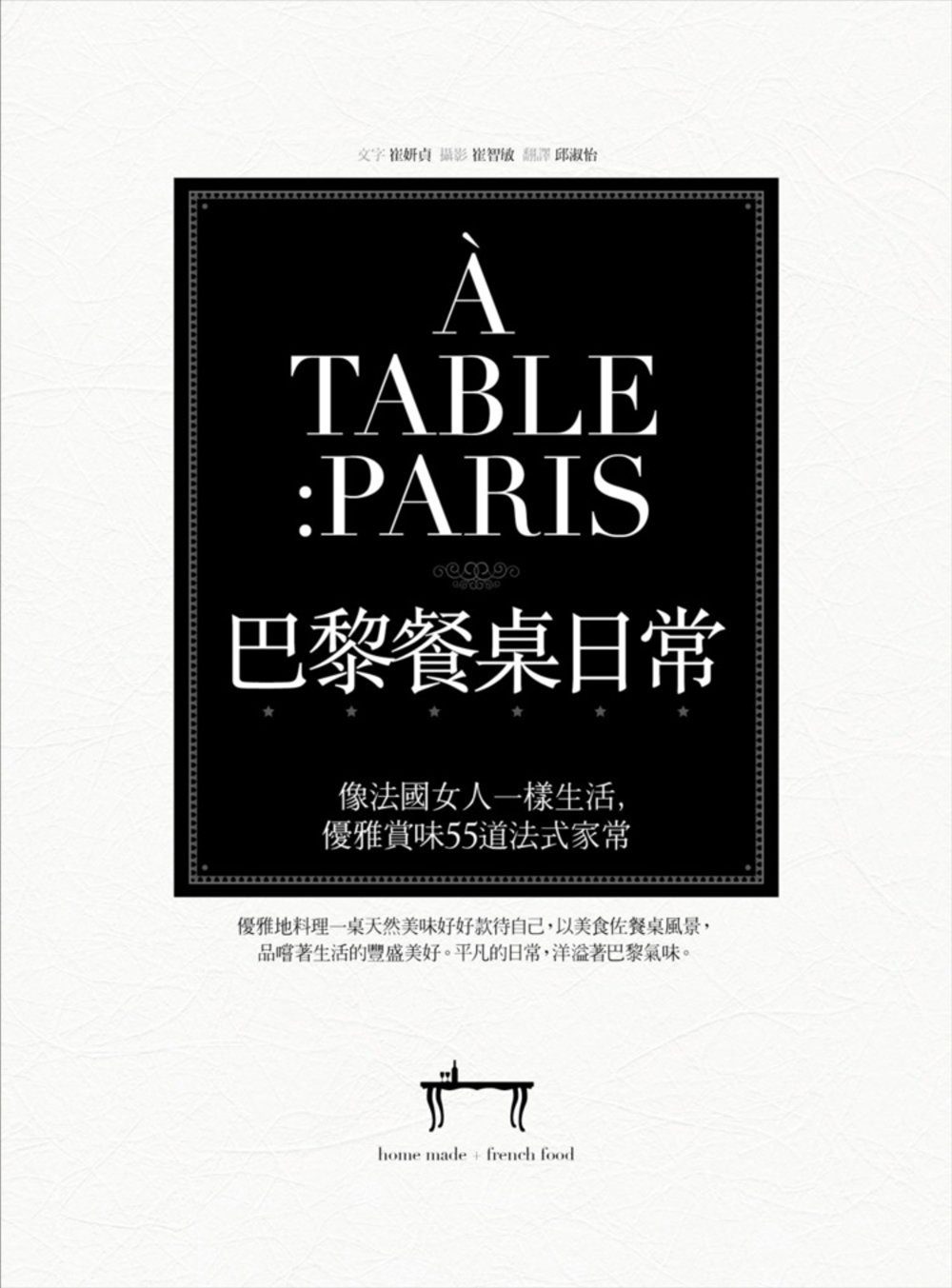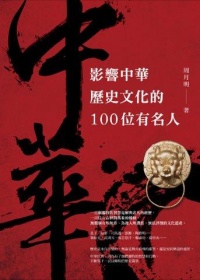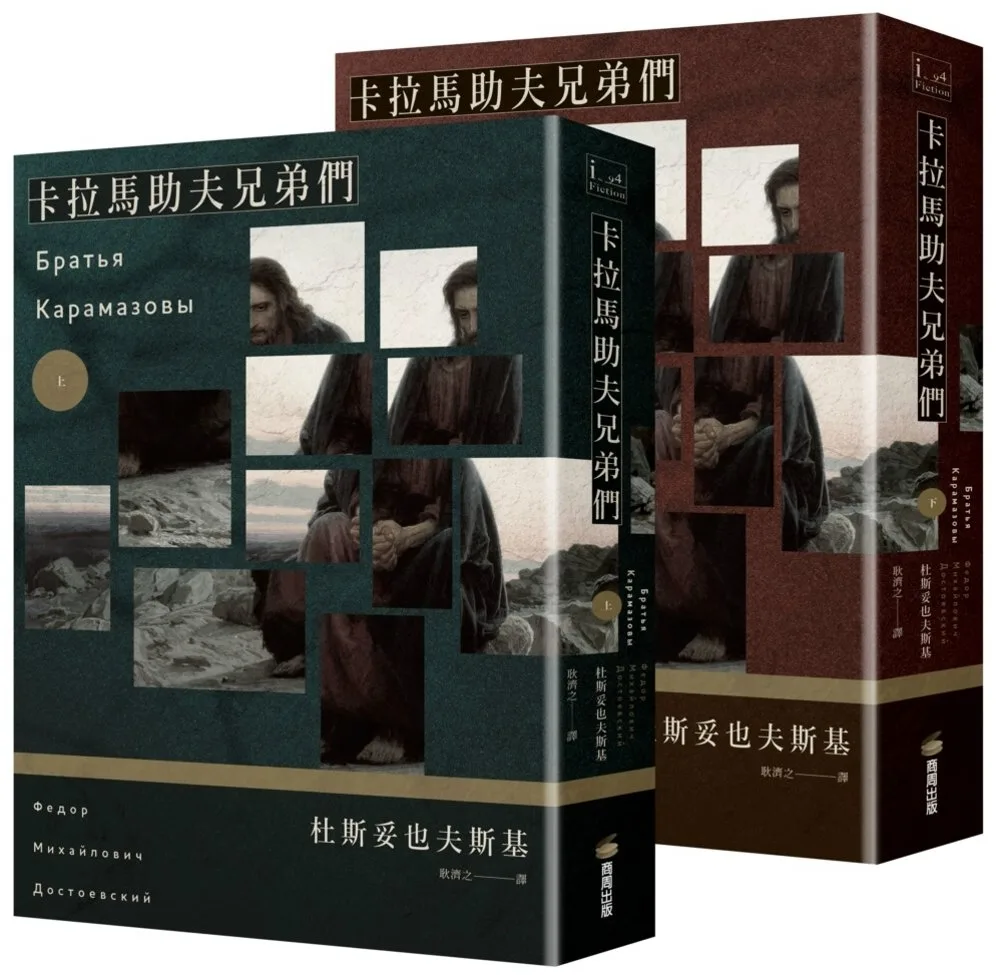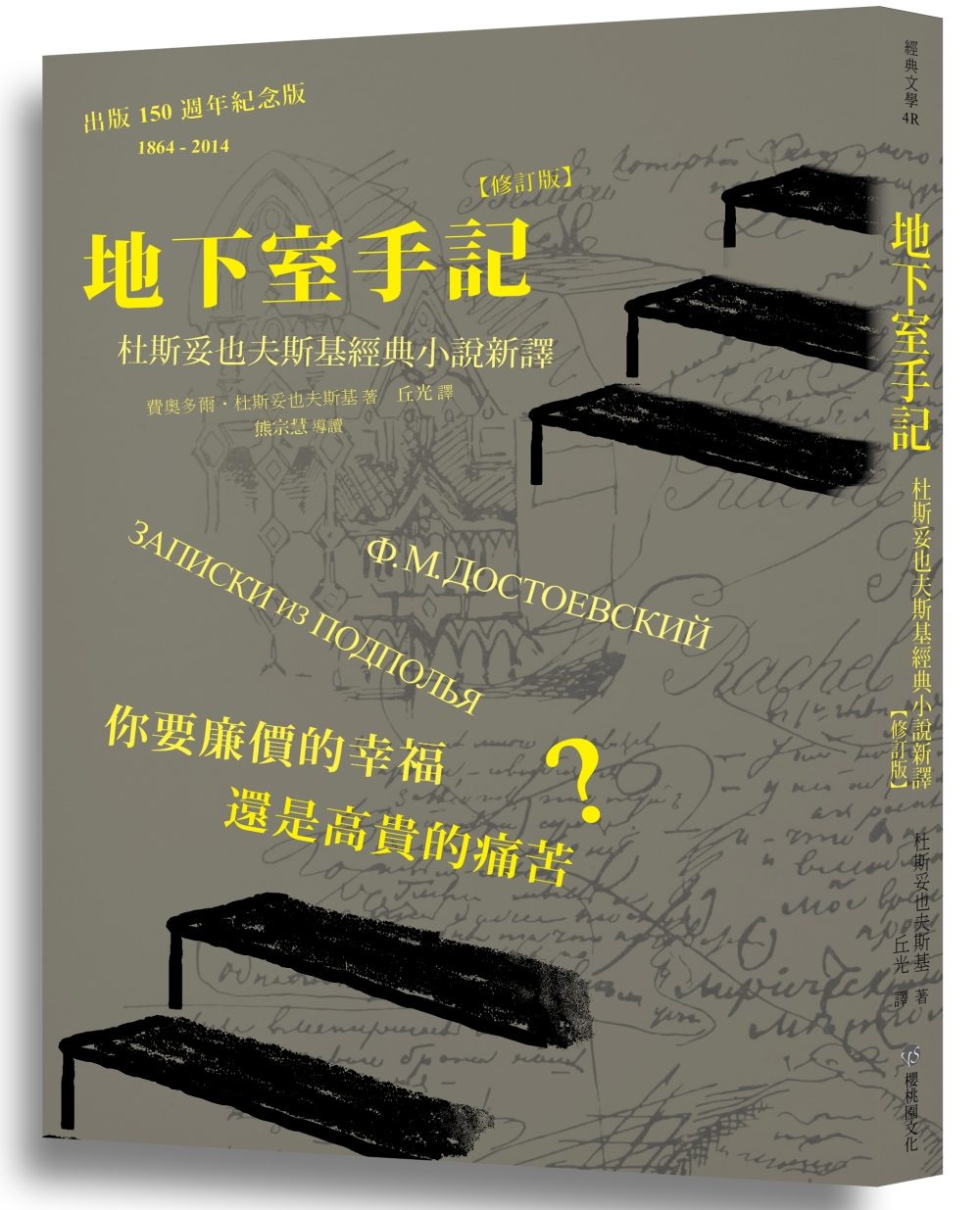譯本序
偶爾看到一篇帶有宗教色彩的淒美感人的神話故事,上帝和天使對人間苦難的冷漠使主人公感到莫名的恐怖。當大地還充滿「贖罪」的人類的哀號、呻吟和垂死的歎息的時候,他拒絕進入上帝的天國:
某天,一位天使或六翼天使把我放在他的翅膀上,要帶我進入福音書中的天國,去見「創世主」,我覺得自己正在大地的上空飛翔,我越飛越高,我聽見從大地上向我飄來悠長而悲哀的聲音,仿佛山間溪流單調的吟唱響徹寂靜的群峰,不過這時我聽出了人類的聲音:那是夾雜著求告聲的哀號,間以讚美聲的呻吟,那是絕望的祈禱、與讚美一起從垂死的胸膛發出的歎息;這一切匯成一片洪亮的音響,一曲那樣撕心裂肺的交響樂,使我心裡充滿了憐憫之情。我覺得天暗了下來,我已經看不見太陽,看不見宇宙的歡樂。我轉頭望著與我同行的天使。我對他說:「難道你沒有聽見嗎?」天使平靜開朗的臉看了我一眼。他說:「這是從大地上向上帝飄來的人們的祈禱。」當他這樣說的時候,他潔白的翅膀在陽光下閃爍;我覺得那翅膀是黑色的,而且充滿恐怖。「如果我是那個上帝,我會哭幹了眼淚,」我叫道,真的覺得我正像孩子一樣在哭泣。我鬆開天使的手,掉在了地上,我覺得我還有太多的仁慈,無法在天國裡生活。
有一位偉大的俄羅斯作家永遠在傾聽大地的呻吟,他就是杜斯妥也夫斯基,他關注「窮人」的卑微處境和可怕的命運,對「被傷害與侮辱的」小人物滿懷憐憫之情;前面故事中的「我」不禁令人想起杜斯妥也夫斯基筆下的一個那麼相似的形象——伊萬•卡拉馬佐夫,他懷著痛苦和悲憤的心情傾訴人類罄竹難書的苦難,以及婦女兒童所遭受的慘不忍睹的折磨和摧殘。他認為,如果包括無辜的孩子在內,人人都必須「贖罪」,以這樣的苦難換取未來的和諧,那麼,「和諧的要價也太昂貴了,我們根本付不起進入那種狀態的代價。所以我急於退還我的入場券。」他解釋道:「我不要和諧,這是出於對人類的愛,」不錯,他也是「還有太多的仁慈」,因而不能接受上帝的世界,無法在天國裡生活。因為他所追求的不是百分之十,也不是百分之九十,而是所有人的幸福,是沒有弱者的眼淚和呻吟的和諧世界。奧地利作家茨韋格就曾敏銳地注意到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這一創作特點,並在《三位大師》一書中給予了熱情的肯定。心理學家佛洛德曾致函茨韋格感謝他贈閱《三位大師》,在信中對茨韋格作了應有的評價,稱他為藝術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闡釋者。
《三位大師》(1820)是茨韋格為歐洲三位文學大師巴爾扎克、狄更斯和杜斯妥也夫斯基作傳的一部著名的傳記文學作品。他在書中寫道:「讓我們環顧一下周圍吧,街道上,小店裡,低矮的房子和明亮的大廳裡,——那兒的人們在想些什麼呢?要做幸福的、滿意的、富裕的、有權勢的人。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主人公之中,有誰追求這些呢?一個也沒有。他們不想停留在任何地方,甚至也不想停留在幸福之中。他們永遠向前奔走……」他們自己「對這個世界一無所求」!
《罪與罰》是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一部最深刻最富於現實意義的作品。他以犀利的筆觸無情地剖析那個時代俄國的社會現實,深入地觸及社會底層的各個角落,令人窒息地感到,走投無路就是小說的主旋律。種種社會原因把窮苦無告的人們逼到左右為難、進退維谷的困境。馬爾美拉陀夫在酒店裡向萍水相逢的青年訴說生活的殘酷,哀歎:「您可知道,先生,您可知道,一個人走投無路的時候,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境遇啊?」他不禁發出絕望的哀鳴:「得讓每個人有條路可走啊」!除了這位九等文官,卡傑琳娜•伊凡諾夫娜、索尼雅、杜尼雅,還有拉斯柯爾尼科夫也都無路可走。
被「貧困逼得透不過氣來的」大學生拉斯柯爾尼科夫,因為付不起學費而輟學。他的摯愛兄長的妹妹杜尼雅,為了哥哥的學業和前途接受了她所不愛的有錢的律師盧仁的求婚。拉斯柯爾尼科夫是從母親的來信得知這個消息的,母親的信使他極為痛苦。「差不多從開始讀信起,他的臉就被淚水浸濕了;可是等到看完信,他臉色慘白,抽搐得臉也扭歪了,嘴唇上掠過一陣痛苦、惱怒、兇惡的微笑」,他「沉思起來,想了好久」。他不曾有過片刻的猶豫,他決不能接受妹妹這樣的犧牲。
此時他早就在心裡醞釀著一個計畫。經過長久的猶豫、等待,也由於機緣巧合,他終於實現了自己的圖謀——殺死了放高利貸的老太婆阿廖娜•伊凡諾夫娜,又意外地殃及無辜,被害人的異母妹妹,經常受她虐待的善良的麗紮韋塔•伊凡諾夫娜意外地闖入犯罪現場,也同時遇害。就在發生此案的前一天,拉斯柯爾尼科夫在一家小酒店無意中聽到一個大學生和一年青年軍官在議論阿廖娜•伊凡諾夫娜:「從大眾利益的觀點看來,這個害肺病的、愚蠢而兇惡的老太婆活在世界上有什麼意義呢?」另一方面,「年輕的新生力量因為得不到幫助而枯萎了,這樣的人成千上萬,到處皆是!」那麼,「把她殺死,拿走她的錢,為的是往後利用她的錢來為全人類服務,為大眾謀福利……一樁輕微的罪行不是辦成了幾千件好事嗎?」拉斯柯爾尼科夫不禁感到驚訝,因為他的「頭腦裡剛才也有過這樣的……完全一樣的想法」。
拉斯柯爾尼科夫並不認為他犯了罪。不錯,他殺了人。可是「大家都殺人,現在世界上正在流血,從前也常常血流成河」,那些人因為殺人如麻而加冕為王,還被稱為人類的恩人。在他看來,人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平凡的」和「不平凡的」。前者必須遵守現存法律和道德法則,循規蹈矩。後者在為實踐自己的理想而有必要時,有權利逾越某些障礙,不受現存法律和道德的約束。小說中的這位主人公是在不同的心境、不同的情況下抒發自己的見解的。他對索尼雅說:「我告訴你吧:我想做拿破崙,所以我才殺了……現在你懂了嗎?」他在索尼雅面前最願意直抒胸臆:「索尼雅……現在我知道,誰聰明、強硬,誰就是他們的統治者。誰膽大妄為,誰就被認為是對的。誰對許多事情抱蔑視態度,誰就是立法者。誰比所有的人更膽大妄為,誰就比所有的人更正確!……只有瞎子才看不清!」索尼雅明白了,「這個可怕的信念就是他的信仰和法則」。
總之,杜斯妥也夫斯基塑造了一個超人的形象,對這個人物給予了強有力的批判,拉斯柯爾尼科夫這個形象和「為所欲為」、超然於善惡之外的超人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十餘年之後,德國哲學家尼采的《查拉圖什特拉如是說》出版,他在其中系統地闡述了他的超人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