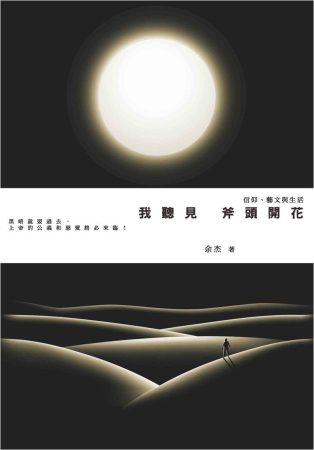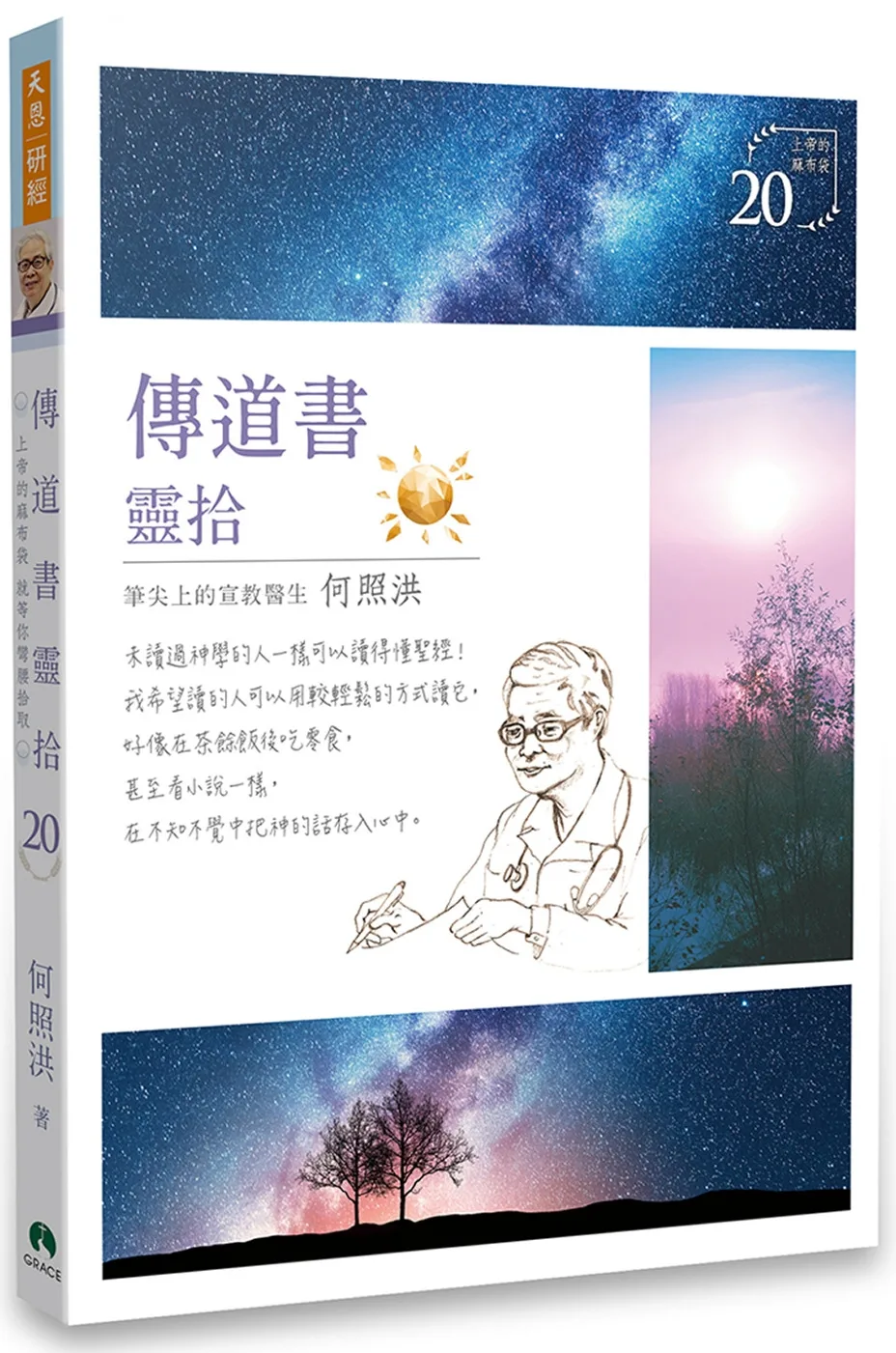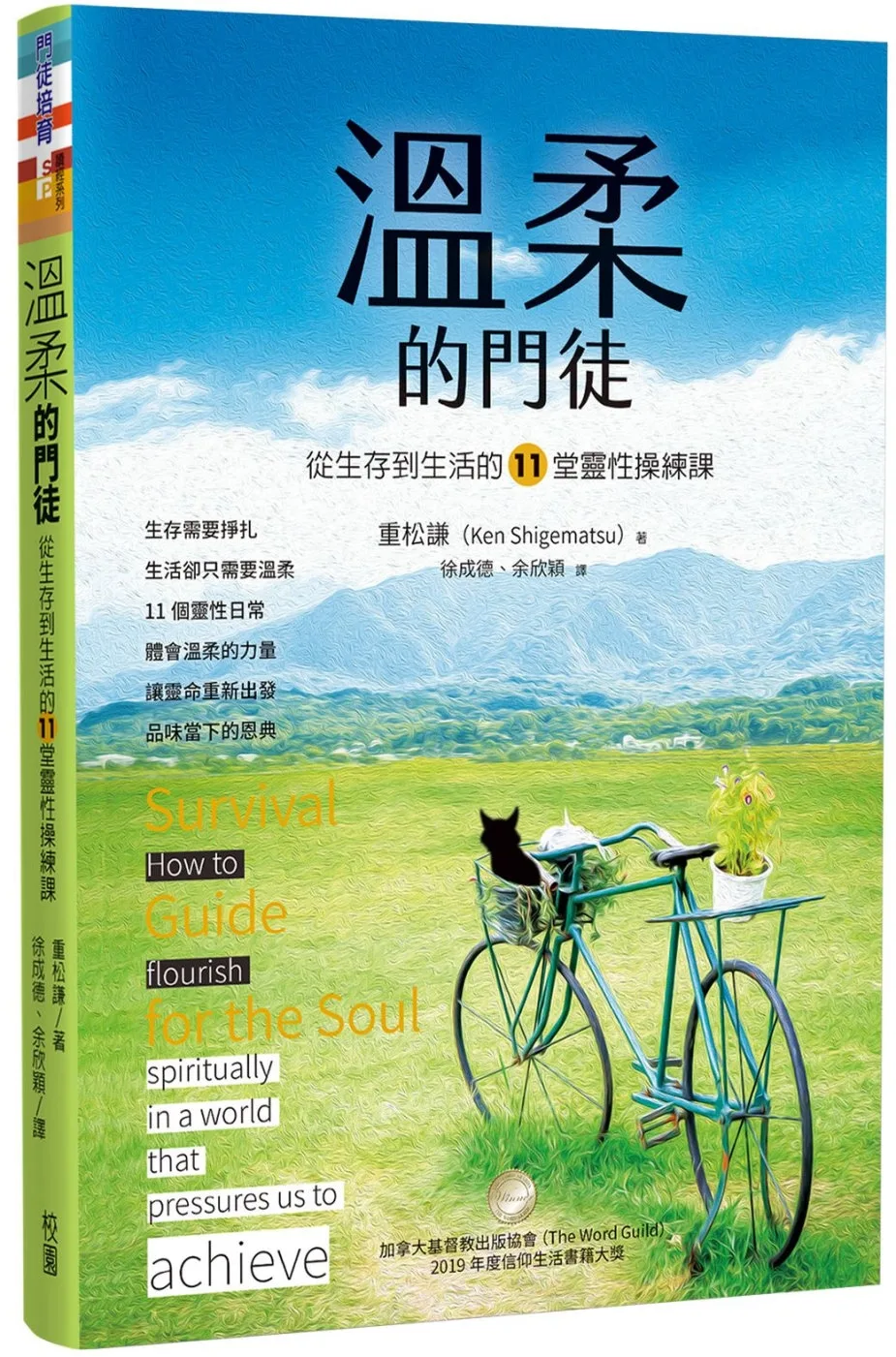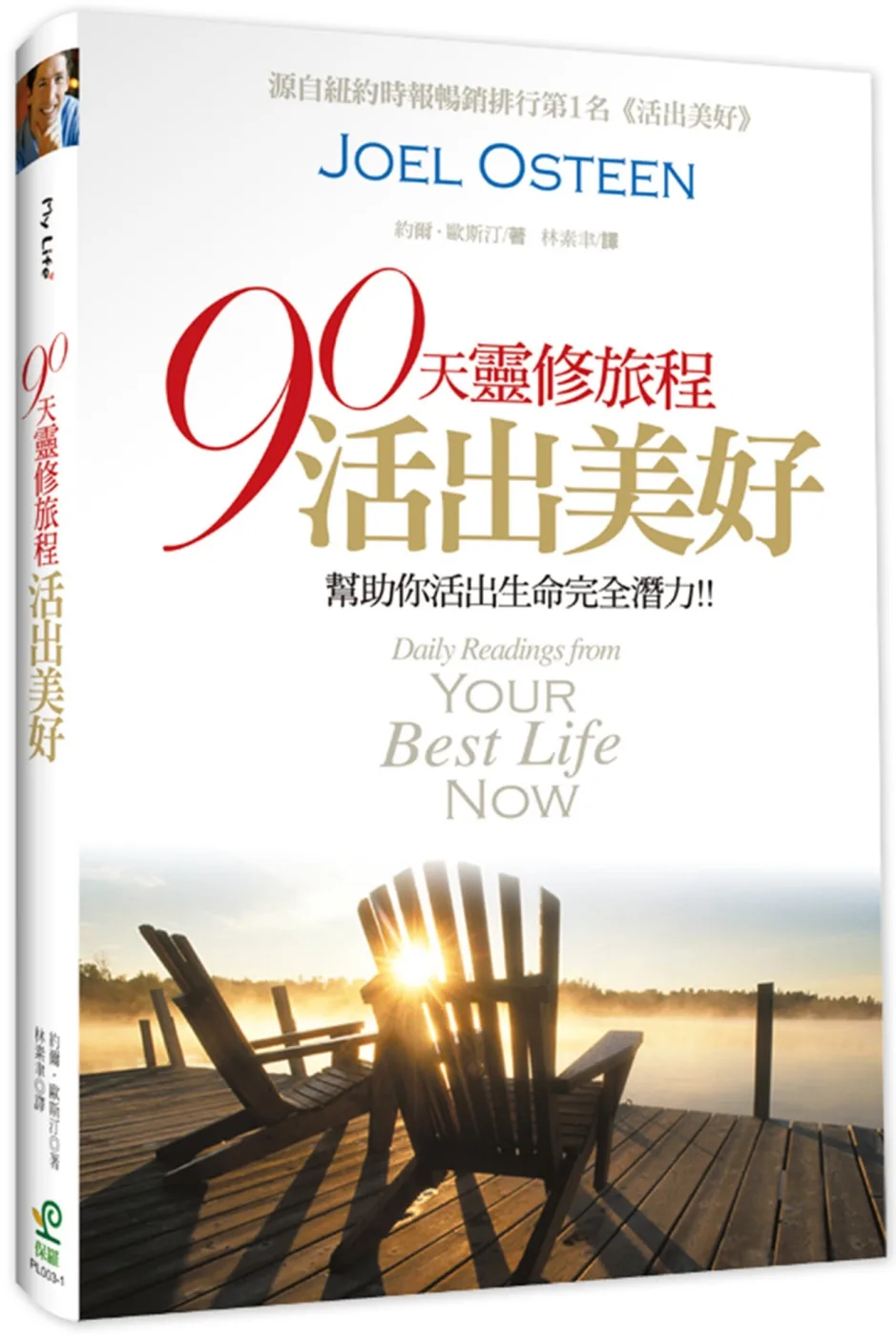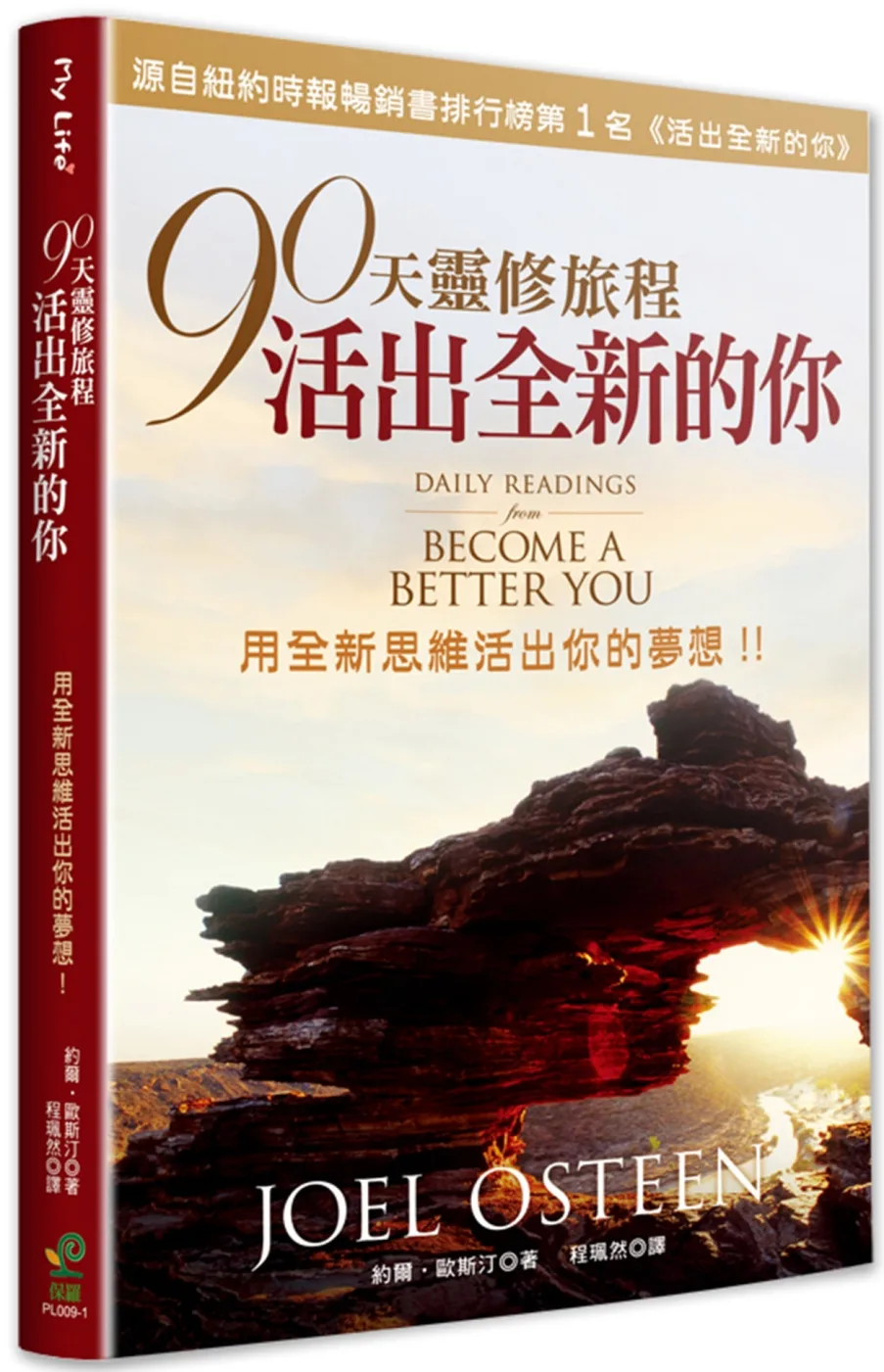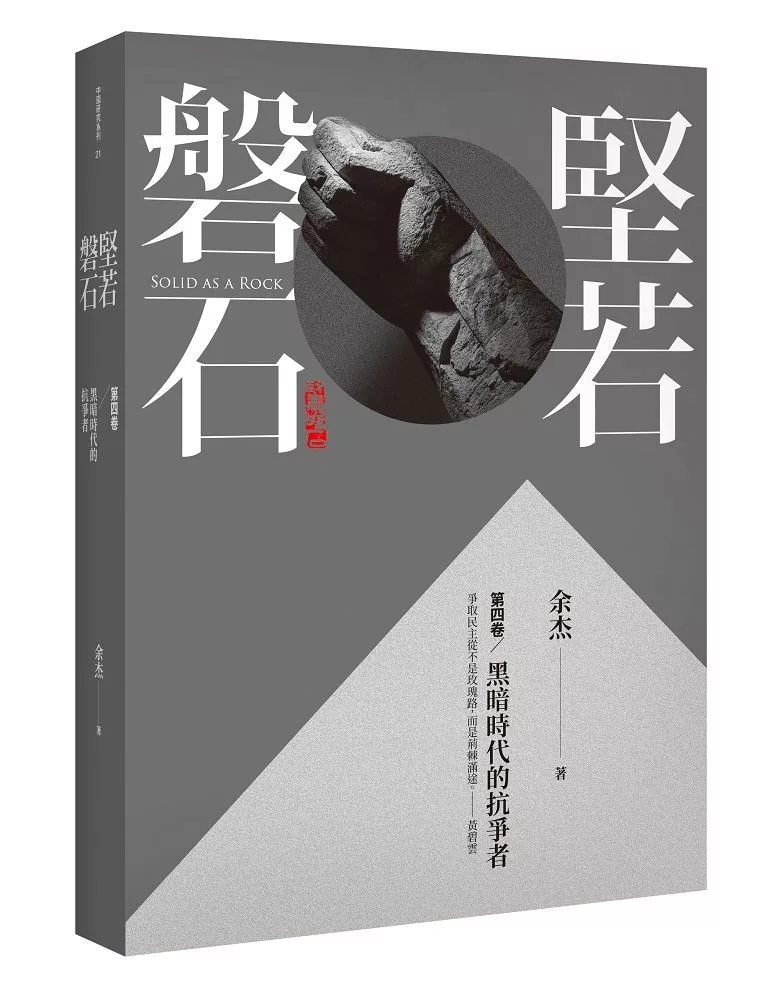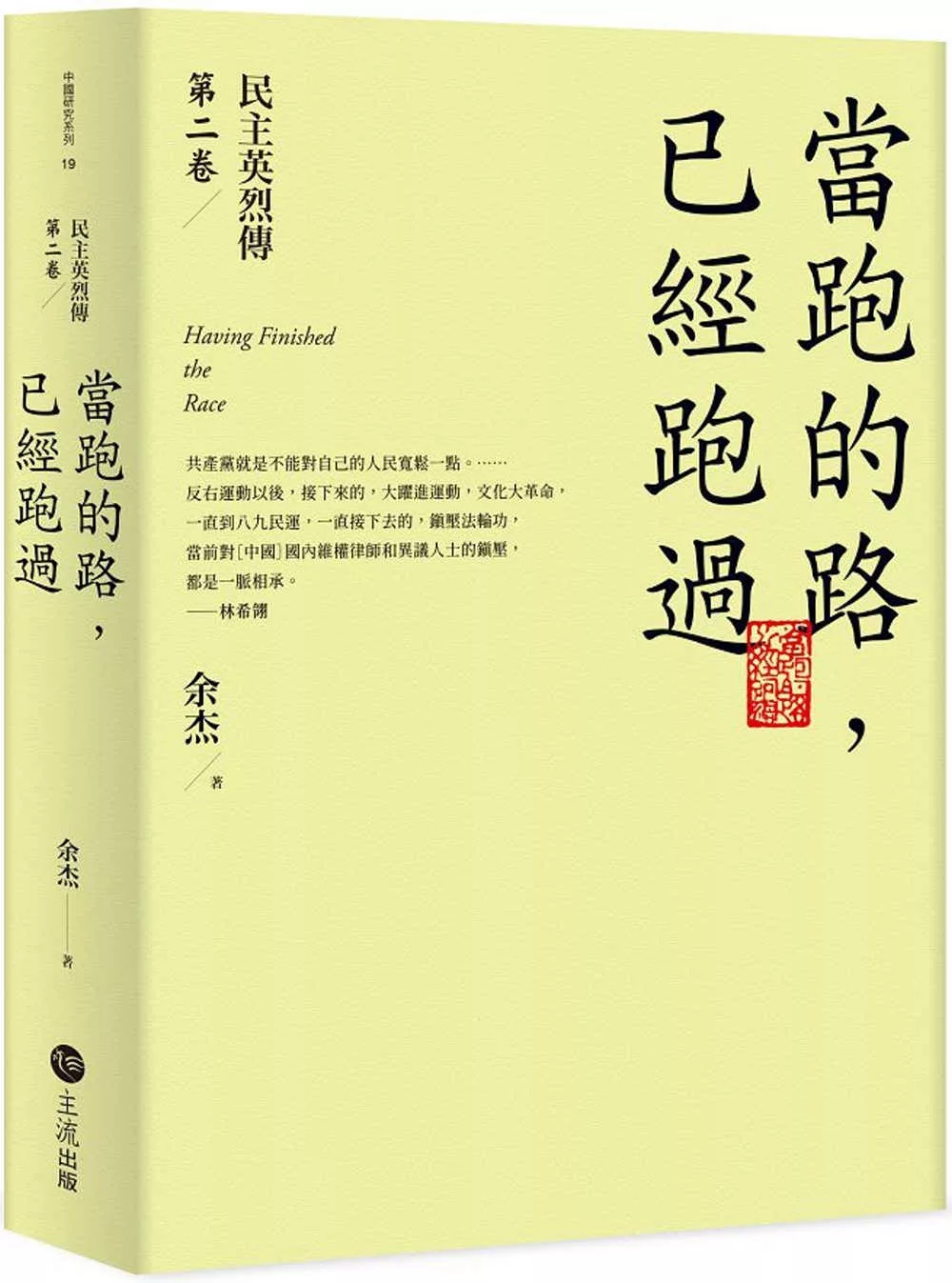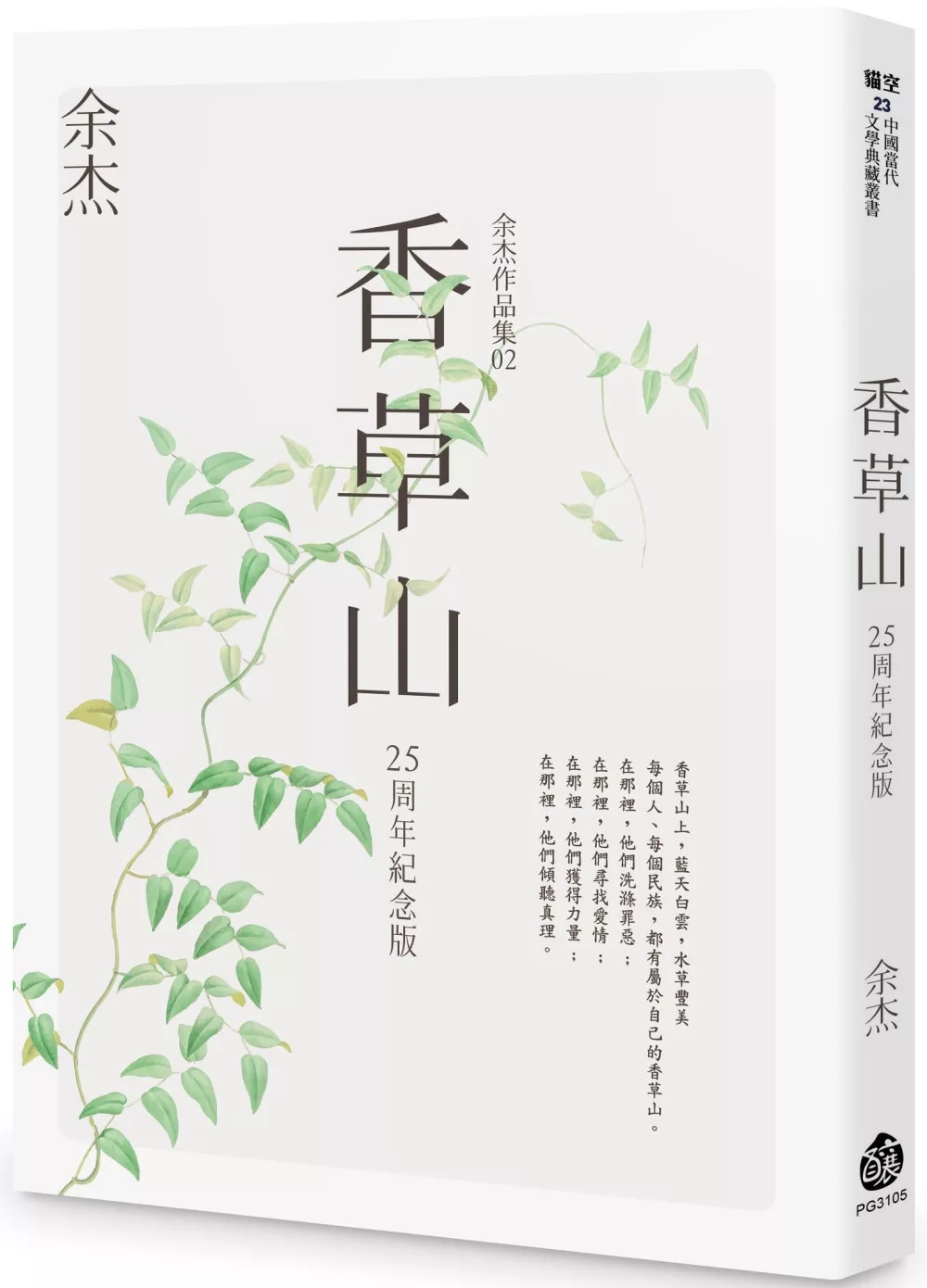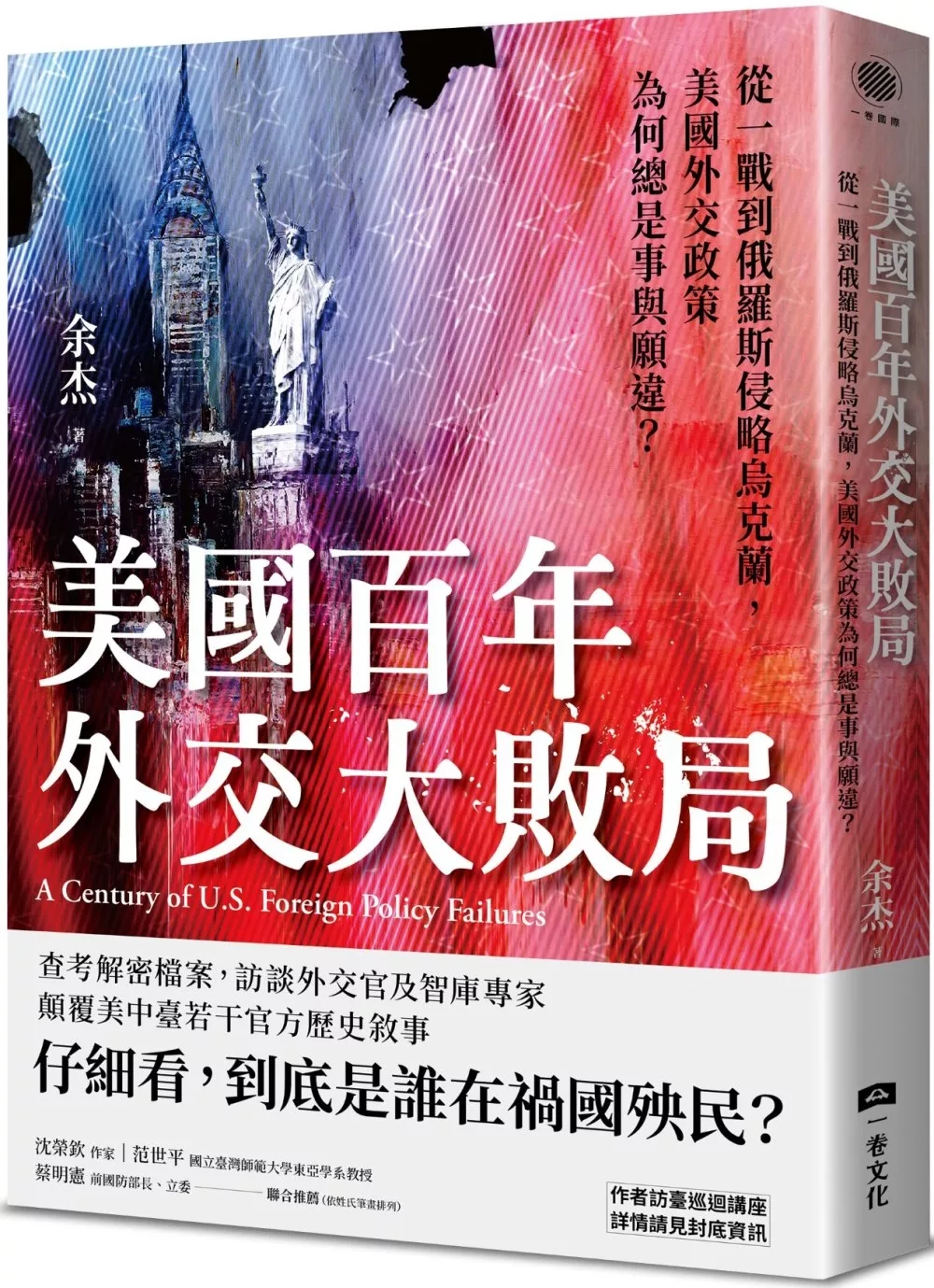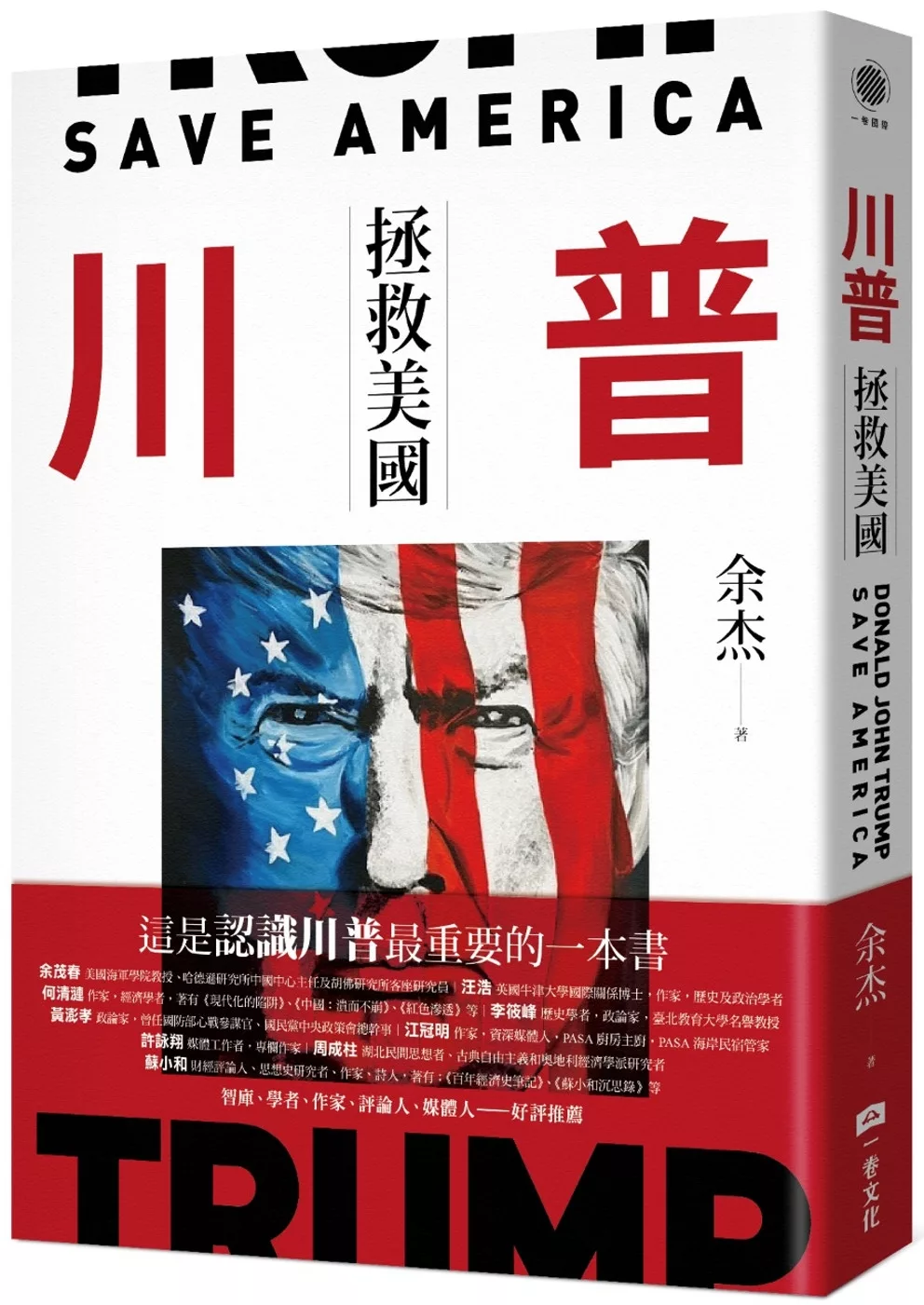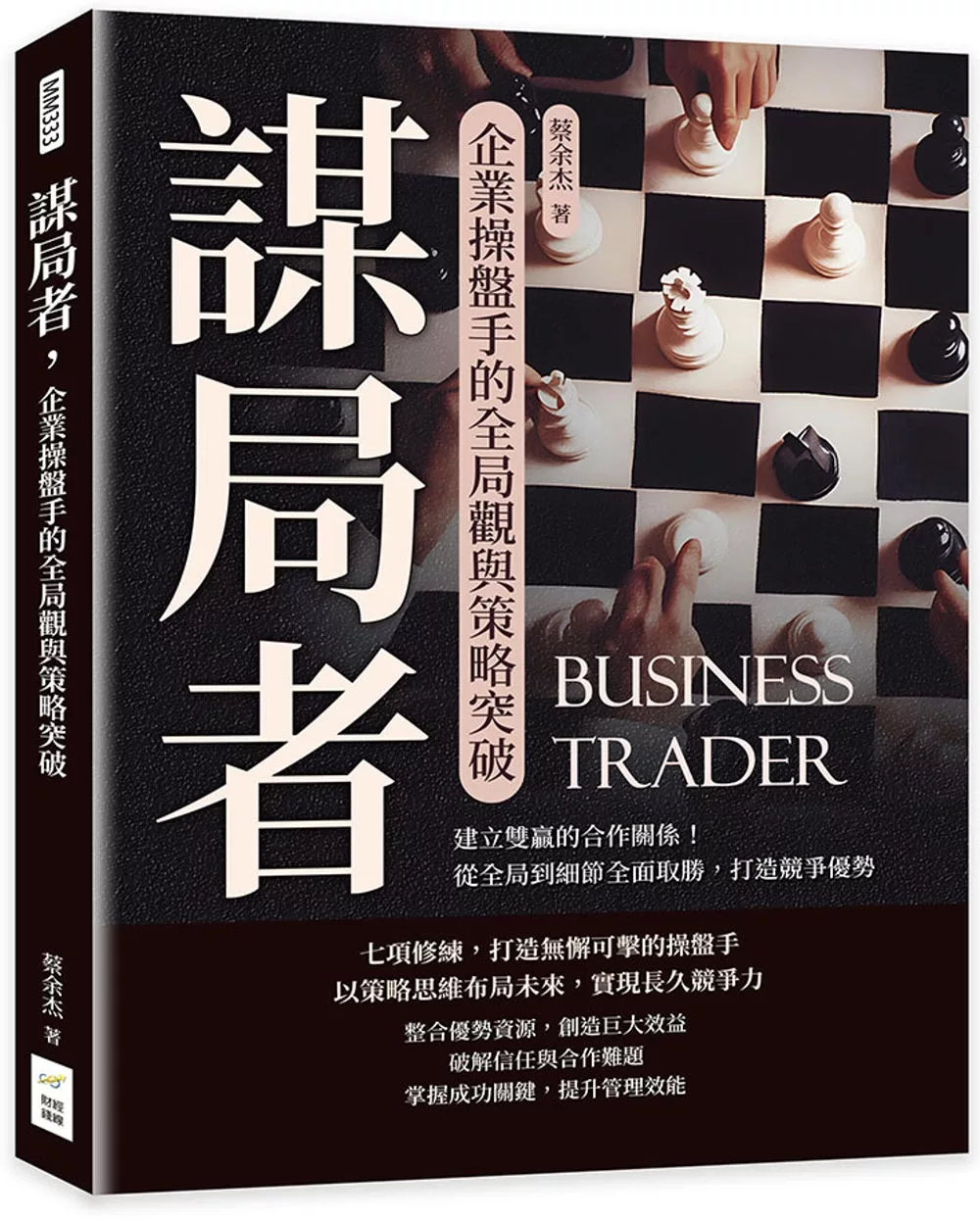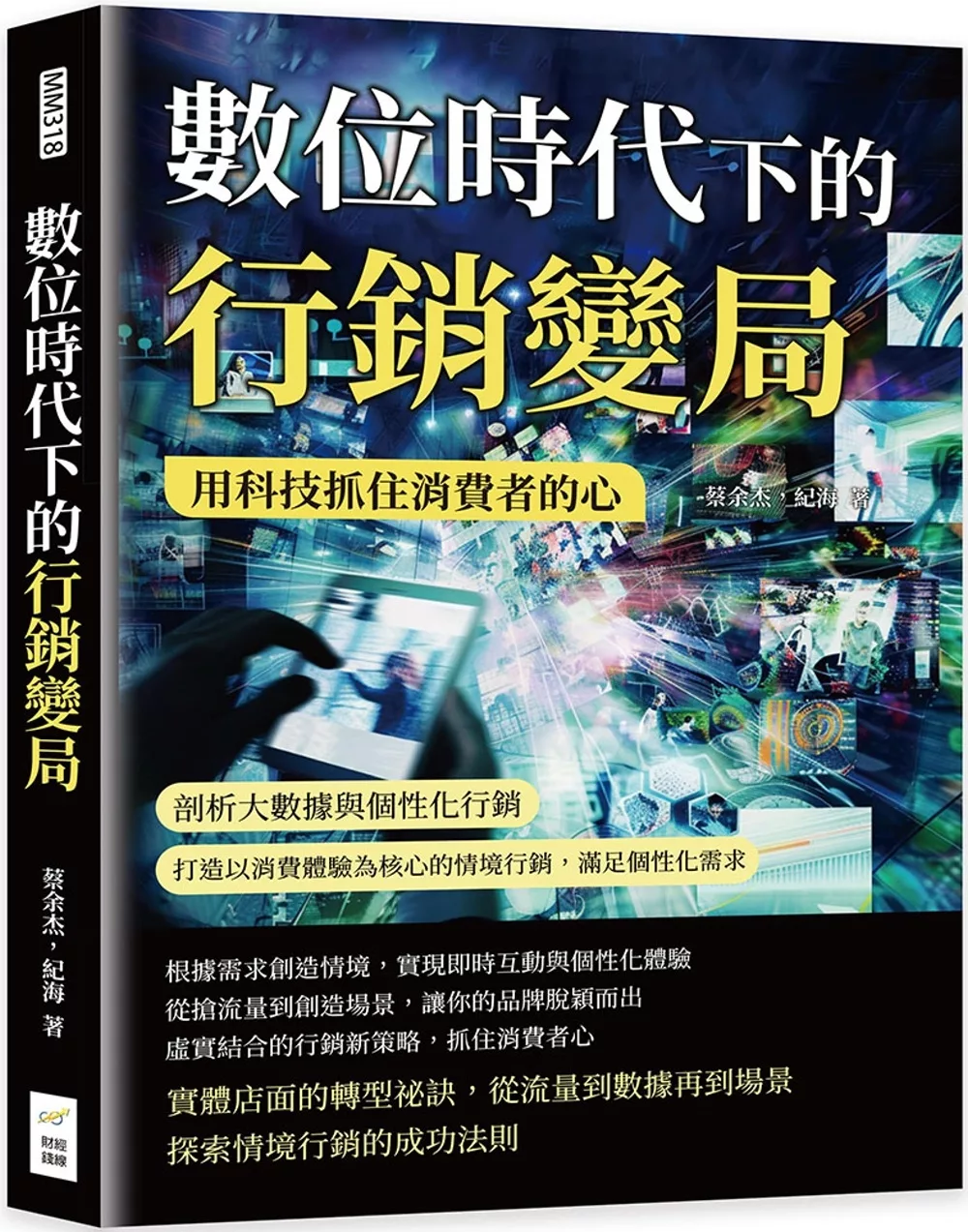推薦序
寧作獨排眾議的天路客--雅歌出版社社長 蘇南洲
魯迅有句名言:「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余杰,一位北京大學中文所畢業的才子,因《香草山》一書而成為百萬作家,卻不得上班,未曾領過薪水,因為他的國家領導讓他找不到工作,只有一輩子或逐水草而生,或在曠野中靠烏鴉銜食過活。他今年四十歲,也勤奮筆耕了四十本書,近千萬言,每日執筆十小時,十數年如一日,古今中外少有出其右者,令人不得不佩服。
余杰常常以「六四之子」自命,「六四」這個符號一直是許多知曉內情的人,避而不談、不願碰觸的議題(近似二十多年前的台灣「二二八」)。六四那年,余杰尚是一個不到十六歲的成都高中生,客觀地說,似乎沾不上邊,但當我在「天安門母親」群體丁子霖老師家中,看著余杰與蔣、丁兩位老師伉儷的互動,在起坐、餐飲流動中的空氣裡,彷彿聞到近似母子般的親情,溢漾著比親人更親的彼此認同與接納,我無言了。
余杰的文字很兇,特別是對有位有權的人,頗有「說大人,則藐之」的古風,也不屑作識時務之俊傑,每每哪壺不開提哪壺,簡直是專與位權者對著幹,朝著總司令部開砲。當他人在北京時,卻連著寫書批判溫家寶、胡錦濤等國家當權者,敢於如此犯顏抗上,更敢於替坐大牢的劉曉波出傳,如今被流放異邦,還繼續寫書批判習近平,簡直是提著人頭在寫、寫、寫,即便有人好意提醒他小心被「江南」掉,也不能稍改其志,因為他已經有過「陳文成」的前半經歷,難怪二○一二年十月紐約特雷恩基金會要將「公民勇氣獎」頒給他。
余杰的文字也很柔,不僅是早期二○○二年《香草山》裡的愛情故事,如優美靈動的生命交響詩般,既富哲思亦撫慰心靈;還有本書中寫到他在被軟禁時,與妻子一邊看《矛尾》電影、一邊流淚的情景,那種對愛與和平無限憧憬的心願,實在扣人心弦。
結識余杰,起於二○○八年秋,旅美多年的好友力揚,邀我赴美與一些民運基督徒分享如何以基督徒角色推動台灣二二八平安運動,為受難家屬及台灣社會止痛療傷與「收驚」的工作。翌夏,余杰循著旅美民運基督徒的引介,來台找到我訪談「二二八」、《曠野》、《雅歌》等課題,而後以「社會心靈重建的建築師」一文,編入他與王怡合著的《我有翅膀如鴿子》。
余杰的處境一年比一年緊張,二○一○年原本計畫為他出版一系列「以神為本」叢書的香港某單位藉詞拖延,可是他講演已經排定,急得直如熱鍋上的螞蟻,他問了別人,也來問我,素性向來無法見危不救的我,也就不多說地挽起袖子,用十四個工作天,完成「以神為本」系列叢書的前三本書(合計約六十萬字),從簡體電子檔經過三次以上轉檔、編校到印刷、裝釘、入庫到位,還趕運至香港書展會場及時供應了余杰講演所需,期間吃了不少苦頭,不過也甘願自嚐。
基於多年陪伴二二八受難家屬的經驗,我也用同樣心情陪伴余杰及一些師友走過艱難之地,無論他是如何「被招待」或「被旅行」,能夠擔任陪伴者,是我的榮幸,也是我的界限,我的「二二八」經驗教會我只能盡心陪伴,任何多言都是在別人的苦難與血跡上的妄行,而貼近苦難則是我作為基督徒的天職。
余杰在二○○三年受妻子劉敏的影響成為基督徒,二○○六年以大陸家庭教會成員與異議作家身分,到白宮與布希總統深入交談中國宗教自由議題,碰觸到中國官方的敏感神經,也遭到太平洋兩岸想和北京方面建立良好關係的許多教會、福音機構與神學院疏遠,所幸除了他的「以神為本」叢書已出版九本外,如今繼《生命書》之後,這本充滿信仰蘊涵的《我聽見斧頭開花》能夠順利面世,也印證了聖經上說「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熄滅」的聖言。
作為獨排眾議的異議分子必然是孤單的,作為行走天路的基督徒也必然是孤單的,在這雙重孤單之下,余杰仍堅持走向千山萬水,只要有主恩相隨,妻兒相伴,縱使面對紅海,相信他也會義無反顧地走向水深之處。
自序
我願做一個憤怒的基督徒
當我完成這本書稿的時候,我心裡知道,這不會是一本超級暢銷書,它的內容並不涉及大部分基督徒關切的婚姻輔導、兒女教育等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議題,它所討論的是華人基督徒甚少關心的異象、公義、社會責任、文化使命等問題。從某種意義上?,這本書的讀者肯定是「小眾中的小眾」──但是,為這部分有異象的基督徒寫作,就是我的異象。
基督徒為什麼必須有異象?
荷蘭傳教士甘治士一六二七年進入臺灣,英國傳教士馬禮遜一八○七年進入中國大陸,若以此兩個時間節點而論,基督新教進入華人社會已有數百年的歷史。然而,基督信仰之於華人社會,仍然如同油浮在水面,而非鹽溶入水中。
為何如此?在我看來,乃是因為華人教會長期以來形成了兩個多少偏離聖經真理的傳統。其一,認為既然世界和人全然敗壞,世界末日即將來臨,便安心地坐等耶穌再來的那一天。在此神學框架之下,形成了一種聖俗絕對二分的反智主義、孤立主義和私人化的信仰模式。其二,受到近代以來的社會福音運動及第三世界的解放神學影響,以及儒家和佛教等中國傳統信仰的侵蝕,偏離了「因信稱義」的新教精神核心,強調善行,認同社會主義的制度框架。這兩個極端都不符合聖經之教導。
華人教會需要神學的歸正與生命的更新。基督信仰是一整套的、獨一無二的世界觀。所謂「新造的人」,就是指人在成為基督徒之後,世界觀發生徹底的翻轉。進而,上帝賜予那些世界觀已然翻轉的基督徒以異象和願景。若無異象,民就放肆。有了異象,信仰與生命就能合二為一。布利克理如此描寫那些具有異象的人:「這些人有一種預感,覺得另有一種方式,認為可以建成更好的世界。」他稱這些人為「找路者」,「他們熱愛這個星球,覺得對神所造的世界有責任,想要使所有神的百姓活得有意義。」
沒有異象的基督徒,期盼的是那種桃花源中與世隔絕、自得其樂的生活;而有異象的基督徒,是有智慧和勇氣的基督徒,是有信念和信心的基督徒,也必然是有影響力的基督徒。他們不是隨波逐流,而是逆流而上;他們不是遺世獨立,而是風雨兼程。他們以能與上帝同工而信心滿滿。英國神學家斯托得在《當代基督教與社會》一書中追問?:那二十億沒有聽過耶穌的人,和另外二十億聽過,但沒有恰當回應機會的人;那些窮人、饑餓的人、受到傷害的人;被政治、經濟或種族逼迫的人;千百萬被墮胎、焚化的嬰孩;以及所謂「平衡核武」的威脅……我們看見這些事,難道無動於衷?我們看到現況,難道看不見可以改變的情況?改變是可能的。那些未聽聞福音的人,可以將耶穌的好消息傳給他們;飢餓的人可以餵飽,受壓迫的人可以得釋放,流離失所的人可以有家。我們需要有異象,看見神的旨意與能力。
在基督新教的歷史上,最具異象的前輩就是清教徒群體。發掘清教徒的精神資源,是我近年來思考和寫作的重心所在。
因著對公義的堅持,我們憤怒
在清教徒時代,很多牧師和平信徒都是頗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雖然「公共知識分子」這個概念是最近半個世紀以來才開始流行的,但在宗教改革之後,長期在社會上承擔此種角色的,恰恰就是一批牧師與平信徒。對於他們來說,教會與社會之間並沒有一道高牆,基督信仰不是一種被束縛在教會之中的僵化教條,而是貫通於基督徒生活各個領域的真理與倫理。清教徒不是社會上的弱勢群體,他們用美好的見證顯明了上帝的大能,他們敢於對抗這個世界的不公不義。用美國清教徒史家利蘭•賴肯的話來說就是:「清教徒是事奉上帝的偉大人物,在他們裡面,清醒的激情與熱烈的同情心有著很好的結合。他們有異象而又實幹,將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結合,追求目標並講求方法,是偉大的信徒,有著偉大的盼望和偉大的作為,也是偉大的受難者。」
今天的華人教會為什麼失去了光與鹽的特質?我觀察到,很多基督徒反倒比他們不信主的時候還要膽小,無論是面對人性的邪惡,還是面對制度性的邪惡,他們大多默不作聲、忍氣吞聲,甚至自欺欺人地禱告說,統統交給上帝來解決吧。然而,上帝並沒有讓我們做守株待兔的基督徒、如履薄冰的基督徒,上帝讓我們剛強壯膽,跑那當跑的路,打那美好的仗。基督徒不是沒有是非判斷的好好先生,基督徒不是沒有稜角的犬儒主義者,基督徒理應像大衛那樣挺身迎戰巨人哥利亞,基督徒應當像但以理那樣無畏地面對獅子。這樣的勇氣,是如何從我們身上喪失的呢?
真基督徒是一群會憤怒的人,而不是心靜如水的假冒為善者。出於對那些將聖殿當作市場的買賣人的憤怒,耶穌親自出手掀翻了他們的攤位;出於對羅馬教廷販賣贖罪券的憤怒,馬丁路德不畏死亡的威脅,宣布「這就是我的立場」;出於對販賣奴隸的「國際貿易」的憤怒,威伯福斯和同伴們推動了廢奴運動;出於對納粹的暴政和種族屠殺的憤怒,潘霍華參與地下抵抗運動並以身殉道;出於對美國社會種族歧視現象的憤怒,馬丁•路德•金率領眾人進軍華盛頓並發表了《我有一個夢想》的演講……他們,就是行道者。憤怒出詩人,憤怒也出聖徒,憤怒帶來了起而行公義的勇氣,憤怒帶來了實踐真理的決心,憤怒更帶來了個人和教會的復興。
基督信仰是滾燙的,如溫水一樣不冷不熱的基督徒,會被上帝從口中吐出去。基督信仰又是具有顛覆性的,它不會與敵基督的、不公義的社會秩序「和平共處」。從英國革命到美國獨立戰爭,從美國南北戰爭到南非黑人的抗爭,憤怒的基督徒們是在前線浴血奮戰的主力軍。所以,我願意做一個憤怒的基督徒,願意自己的文字充滿憤怒和激情。詩人 T. S. 艾略特說過:「年輕的時候,我們看問題稜角分明;隨著年齡漸長,我們喜歡說話留有餘地,即便明確的觀點,也要多加限定,喜歡插入更多的括弧。我們能預見自己的觀點可能受到怎樣的反駁,我們對論敵更為寬容,有時甚至是同情。而年輕的時候,我們說起自己的觀點來底氣十足,要麼激情澎湃,要麼義憤填膺。」對我來說,真理讓我得享自由,真理讓我永遠年輕,成為基督徒之後,我沒有變得鄉愿、世故、中庸、冷漠,我的文字反倒更加銳利、更加鋒芒畢露。
我要迎接的屬靈的「不列顛空戰」
二○一○年,上帝讓我經歷了中共的蓋世太保的酷刑之後死裡逃生,上帝沒有讓我成為殉道者。二○一二年,上帝更為我排除了一道道的攔阻,帶領我們全家奇蹟般地離開中國,來到美國,來到這塊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的地方,開始新一階段的生活。
臨行前,王怡弟兄在微博上留言祝福我說:「主啊,我知道不是地上的君王;乃是天上的君王使他們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主所指示的地方去。」這是讓我最感動的一句臨別贈言。二戰期間,文學大師 C. S. 路易斯到牛津大學的學生團契分享。當時,很多年輕人都去參軍了,有一些在前線戰死。那些沒有參軍的同學追問說,我們在這個時候讀書有意義嗎? C. S. 路易斯對他們說,這場仗早晚會過去,希特勒注定會失敗,但當倫敦上空納粹的飛機消失後,另一場屬靈的大戰即將來到──馬克思的聲音、佛洛依德的聲音,各種世俗的思想和價值都將蜂擁而至。那時,誰可以升空,去參與這場屬靈的「不列顛空戰」呢?他說,這就是上帝讓你們活下來的原因。這段話深深激勵了我,這也許就是上帝讓我活下來的原因。
成為基督徒之後,我寫作的目標,不再是自我的功成名就,而是榮神益人。《我聽見斧頭開花》這本文集,就是我「不列顛空戰」的「備忘錄」。無論是對清教徒傳統的追慕,還是對華人教會史的梳理;無論是對教會內外黑暗面的揭示,還是對流行的政治、經濟、文化觀念的剖析,我都竭力做到「憑愛心,說誠實話」,拒絕謊言,不迎合大眾,講述讓人感到「扎心」的真理。我在很多文章中得出的結論,在這個善惡與對錯的標準已然混淆甚至倒錯的時代,幾乎都是嚴重的「政治不正確」。但是,基督徒應當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憤怒與激情,因為,最終的判斷標準,就是回歸聖經──經上如是?,為什麼還要欲言又止呢?
數百年來,基督信仰在華人社會中生根發芽,但趙天恩牧師所宣導的「文化基督化」遠未實現,華人文化仍被敵基督的專制、暴力、謊言和迷信所充滿。然而,我欣喜地看到,上帝在這個時代興起了一批信仰純正、異象明確、委身教會又面向社會的作家、學者、藝術家以及各個領域的專業人士,上帝要將「文化鬆土」的使命放在這群人的身上。無比榮幸的是,我亦是其中之一員。我祈求,上帝繼續使用我這卑微的器皿,讓我有分於將福音傳遍地極的偉大使命;我也祈求,與更多的弟兄姊妹共用在主裡豐盛的生命,一起走在「與神同行」的道路上。這一路,有死蔭幽谷,更有花香滿徑;這一路,有公義,有憐憫,有恩慈,有信,有望,有愛。
二○一三年九月
美國維吉尼亞州